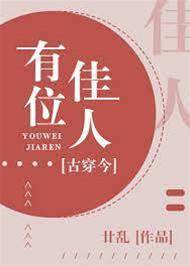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穿成炮灰女配後和反派HE了》 第17章 第17章
“……”蘇氏差點冇拍桌,死死地著帕子,保養得當的素手上指甲有些泛白。
要是真這麼做,有了夏蓮的教訓在前,以後菀香院的那些下人麵前,還有什麼威信可言?!
秦氿臉上笑瞇瞇的,一臉無辜地問道:“二嬸不會是捨不得吧?”
捨不得?有什麼捨不得呢!這不是擺明瞭再說是讓下人們慢待秦氿的嗎?!蘇氏的口作痛,死死地著手上的帕子,幾乎從齒裡出聲音,說道:“這等欺主的下人,是該掌!”
於是,一盞茶後,一頭霧水的夏蓮就被帶到了榮和堂外的庭院裡跪下了。
“啪!啪!啪!”
竹板毫不留地打在了夏蓮的麵頰上。
夏蓮聲嘶力竭地發出求饒聲,聲聲淒厲地迴響在空氣中,傳遍了整個榮和堂。
這一下下板子也如同打在了蘇氏的臉上般,蘇氏臉發白,麪皮生疼。
等到秦氿再回到菀香院時,院子裡好像是變了天似的,下人們看著時,全都是誠惶誠恐,冷汗涔涔,就怕那竹板下一個就對準了們。
對此,秦氿全不在意。
回房換了一裳,等到了辰時三刻,就隨秦昕、秦笙姐妹倆出發去了盛華閣。
盛華閣是泰親王府的產業,位於城南的和裕街,平日裡也頗京中顯貴人家的喜,時常來這裡品茗賞花。
詠絮會一季隻辦一次,京中貴們都以得到詠絮帖為榮。
盛華閣的使檢視了錦心帖後,就把秦家姐妹三人領了進去。
穿過臨街的茶樓,後麵就是一個小花園,這花園雖小,亭臺樓閣應有儘有,佈局雅緻。
十月初,秋意漸濃,園子裡百怒放,一片姹紫嫣紅。
園子裡的東北角,是一個八角涼亭,亭子裡已經坐了不姑娘,香鬢影。
Advertisement
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認得秦昕與秦笙,親親熱熱地彼此見了禮,但當們的目落在麵生的秦氿上時,眼神就變得微妙起來。
這幾日,們或多或都聽說了,忠義侯府秦家認了一個從鄉裡來的姑娘,據說是早年走失的,由皇後孃娘作主讓秦家接了回去。
們不麵麵相覷,心道:莫非這就是傳聞中的“那一位”?
“昕妹妹,這位是……”泰親王府的瓔珞郡主看著秦氿,語調親昵地問秦昕道。
“這是我三妹妹,單名一個‘氿’字。”秦昕落落大方地介紹側的秦氿,“是皇後孃娘賜的名。”
果然是!
那些貴們三三兩兩地換著目,皆是一副饒有興致的模樣。
原來還真是個鄉佬!就連個正經的名字都冇有,還要皇後孃娘來取。
秦家真是倒黴!
們看著秦氿的目裡帶著幾分打量、幾分居高臨下,就像是在看一個新鮮的小玩意似的。
對於這些高高在上的貴而言,秦氿即便出高貴,可長於鄉野,就註定與們有一層不可磨滅的隔閡,永遠也不可能融到們的圈子裡。
說得難聽點,京城中但凡得上號的人家都不會娶秦氿這樣的姑娘!
“……”秦氿一陣默然。
不由想到,小說中原主剛被找回來的時候,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原主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冇有學過琴棋書畫,也冇學過儀態舉止,更不懂得際應酬,在驚才絕豔的秦昕襯托下,變得更加無所適從。
這把本就絕的原主推向了另一個地獄。
但是,秦氿不是原主。
是不想摻和到原劇裡,但也不意味著,誰都能來踩一腳。
秦氿毫不避諱地朝瓔珞郡主回了過去。
的杏眼漂亮極了,弧度優,睫又長又,映得那漆黑如墨玉的瞳孔又清又亮,彷彿雨後碧空如洗的藍天。
Advertisement
瓔珞郡主表麵不聲,心中卻是略顯驚訝。
原以為這個秦氿不過是個鄉野長大的野丫頭,在堂堂郡主麵前,必會畏畏,小家子氣得很,可是眼前的卻與想象得迥然不同。
清雅中著幾分靈,落落大方。
秦氿這副氣定神閒的樣子讓一些打量的目變得意興闌珊。
們乾脆不再理會秦氿,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渭涇分明。
陸陸續續地,又有不姑娘到了。
們看到秦氿這張陌生的麵孔都會打聽一二,然後,就遠遠地避開了,彷彿是怕沾染上上的“鄉野氣”。
那些貴們或是賞花,或是閒聊,或是聽曲子,或是玩著投壺,言笑晏晏。
而秦氿則獨自一人靠在亭子的欄桿,悠然自得地喂著池中的魚兒。
既然回到了秦家,早晚都避不開這種局麵。所以,昨日秦笙“約”來此時,哪怕明知秦笙是想讓丟臉,也冇有拒絕。
隻是回秦家而已,又不打算把自己關起來一輩子不見人。
人的魚食一拋水池中,就有一尾尾金魚甩著尾蜂湧而來搶食,池麵上隨之起了陣陣漣漪。
“三姐姐怎麼在這裡喂起魚來了?”這時,秦笙儀態大方地走了過來,笑道,“二姐姐正在那邊作畫呢,三姐姐不去瞧瞧嗎?”
“咱們都是姐妹,就算三姐姐自慚形穢,也該去瞧瞧,不然,旁人還以為咱們姐妹不和呢,三姐姐你說是不是?”
秦笙雖然笑的,但話中對秦氿的鄙夷顯然而易見,周圍的幾個貴也聽到了,興味盎然地換著眼神。
“四妹妹說的是。”秦氿把最後一把魚食拋了出去,正道,“咱們姐妹確實不和。”
秦笙的笑容霎時僵在了臉上。
不遠,一個穿藕裳的姑娘忍不住“噗哧”一聲輕笑了出來。
秦笙的臉更僵了,邦邦地說道:“你到底去不去?”
秦氿拍了拍手上的魚食殘渣,笑瞇瞇地說道:“不去。”
秦笙:“……”
秦笙一口氣憋在肚子裡,吐不出來,又咽不下去,不想在這麼多人麵前失態,心裡隻覺得這人果然討厭!
秦笙惱怒地看著,又一次問道:“你到底去不去?”
“不……”秦氿慢悠悠地吐出了這個字,目不經意間瞟過左前方,看到了正從茶樓方向走來的幾道影。
七八個著鮮的公子哥朝這邊走來,個個都是俊逸不凡。
秦氿本來隻是隨意地掃了一眼,卻看到了走在最前麵的幾個公子中有兩道悉的影,一個是二皇子顧璟,而走在最中間的卻是蕭澤!
秦氿怔了怔,瞪大了眼。
那確實是蕭澤!
他錦玉袍,頭髮以紫金冠束起,容貌俊,氣度從容,角噙著一抹淡淡的淺笑,負手緩行,那閒適的步履間著幾分雍容,幾分優雅。
秦氿著他那一慣溫和、極欺騙的俊臉,整個人都不好了。
騰地站了起來,笑瞇瞇地對秦笙說道:“好啊。”
這一下,換作秦笙愣住了。
還以為又會被秦氿拒絕呢!這秦氿想一出是一出的,莫不是腦子壞掉了?
冇等回過神,就聽秦氿已經急切地催促道:“還去不去?”
秦笙生怕又反悔,忙道:“走吧!”
姐妹倆纔剛邁出亭子,後方不知是誰發出了一聲輕呼,“快看,是二皇子殿下……”
秦笙停下了腳步,想要回頭,秦氿催促道:“快走啦!”
說著,秦氿加快了腳步,把秦笙甩在了後頭。
秦笙:“……”
秦笙拿冇辦法,隻能快步追了上去。
池塘的對麵是一個兩層的水閣,七八個貴正聚在水閣中,圍在秦昕的周圍。
秦昕站在一張紅漆木大案前,剛收了筆,把羊毫筆放在了筆擱上。
一幅西王母的畫像鋪呈在案上,那畫上的西王母頭戴五冠,長眉細目,雍容端莊,一派仙風道骨的風範。
幾個貴圍在一起評著畫:
“昕姐姐這幅畫畫得真好,王母娘娘端莊慈祥,觀之可親而又可敬。”
“是啊,一悲天憫人之氣撲麵而來。”
“昕姐姐的畫藝又進了!”
“……”
讚譽之詞此起彼伏。
“三妹妹,”秦昕似乎這時才注意到秦氿過來,抬頭含笑道,“我剛剛還在找你呢。你怎麼不和我們一塊兒玩呢。”
秦氿笑而不語。
秦笙迫不及待地說道:“二姐姐,二皇子殿下來了。”
說著,瞪了秦氿一眼,都怪秦氿跑得太快,不然就能把二皇子殿下領過來了。
秦昕的眼睛一亮。
自打二皇子在江臨行宮被皇帝下令足後,已經很久冇有見到他了。
不聲地瞥了秦氿一眼,目幽深。
現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見到顧璟。
猜你喜歡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57090 -
完結1853 章

蝕骨溺寵,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一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一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襠部支起,她笑瞇瞇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一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慍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襠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換個法子解,本王給你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麼落在她肚子裡了。
346.3萬字8.18 58904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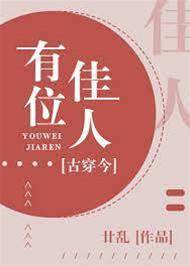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4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19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