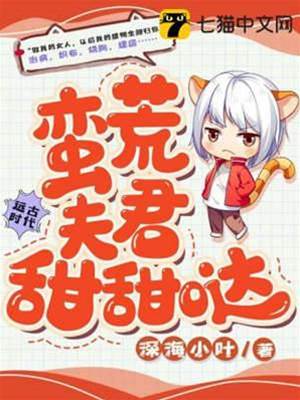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我家賢妻太薄情》 第13章 第 13 章
薛宜寧難地重新躺下來,想了想,開口道:“把晚秋進來。”
玉溪出門去,很快就帶了晚秋進來。
晚秋是管院中灑掃的二等丫鬟,平時并不在邊侍候,但也是從薛家帶過來的陪嫁,自然也是聰明伶俐的。
“夫人。”晚秋在床邊站定。
薛宜寧半躺靠著問:“是芬兒來向長生傳話的?”
晚秋回答:“是。”
“當時神怎樣?”
晚秋回道:“有些著急,又好像……”
仔細想了想,說道:“有些擔心和……猶豫,對,就是這樣,我看看我一眼,很快就撇開了,又看了眼屋子這邊,好像怕被看見聽見什麼似的,隨后就和長生說話,待長生進來,就回院外去了。”
“然后長生就立刻進來了?”薛宜寧問。
晚秋點頭:“是。”
“好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薛宜寧說。頭疼,難,說這些話,已是傷神。
玉溪還不明白薛宜寧問這些做什麼,一旁子清卻琢磨過來,問薛宜寧:“夏姑娘說什麼心口疼,是裝的?要不然邊侍候的人怎麼會不敢被咱們這邊看到呢,芬兒是知道從這邊走將軍太過分,所以怕夫人怪罪吧?”
薛宜寧喃喃道:“芬兒如此,是人之常,只是長生……他的心,大概是向著那位夏姑娘的。”
經主子點明,這時子清才完全明白過來。
心口疼,說不出是什麼病,有可能是很疼,也有可能只是偶爾疼那麼一下。
要怎樣才能功把將軍走?那一定得表現得很著急,疼得很嚴重,而長生急步走進來的樣子、稟報時的神態,分明就是很嚴重的樣子。
所以駱晉云才會二話不說就扔下這邊的夫人,張地去看夏柳兒。
Advertisement
可若按規矩,長生不該那麼闖進來,而該讓院里的晚秋來通傳,但他沒有,他就是怕晚秋是這邊的人,會輕描淡寫說一句,駱晉云又被這邊絆住,不會馬上去探。
所以主子才說,長生是向著那位夏姑娘的。
夏柳兒是他送回來的,當初從杭州到京城,軍中也沒有丫鬟,想必一路也是長生照顧,所以更有主仆之誼,這才幫著夏柳兒爭寵。
想到此,子清不忿道:“可夫人才是這駱家的主母,他這樣向著一個姨娘,將主母置于何地?”
薛宜寧有氣無力,緩聲道:“他不是向著姨娘,是向著他自己的主子。”
子清頓時無言。
長生的主子,自然就是將軍。
作為邊人,他怎會不知將軍心思?他向著夏柳兒,是因為,將軍向著夏柳兒……
夏柳兒的心口疼,也不知究竟是怎樣的病,反正最后并沒有大夫進府,倒是駱晉云,一直在萬福園待到了傍晚。
子清惡狠狠地想,照兩人這黏糊勁兒,說不定早就無茍合,有了首尾。
幾日之后,平陵公主府給長孫做周歲,薛宜寧大病初愈,不敢出門,所以沒有陪同,只有老夫人自己過去。
回來后,老夫人喜不自勝,帶回來好消息:平陵公主選定了駱晉雪做兒媳婦,明說要挑日子找人上門提親。
事如此順利,薛宜寧功不可沒,加上平陵公主還問起了薛宜寧,老夫人回來后也就對薛宜寧格外重了些,當著駱晉云的面,讓他對媳婦兒好些。
老夫人沒提夏柳兒,但大概老人家也覺得駱晉云對夏柳兒太好了,多讓薛宜寧這個正室夫人面無。
駱晉云沒接話,只是到晚上,他來了金福院。
Advertisement
薛宜寧正點著燭臺給他那件寢,見他來,放下針線,起侍候他解帶沐浴。
駱晉云看著,平靜待道:“母親說平陵公主喜歡你,以后那些納采納吉的事,都由你來接應安排,這樣不易生事端。”
薛宜寧溫聲回答:“好。”
除此之外,再無多的話。沐浴完,一番云雨,他披上服下床離開,好像是夏天的碳火,冬天的涼席,紆解,再不值得看一眼。
靜靜躺在床上,神依舊溫順,什麼話也沒說。
其實,再習慣,也還是有一些在意的。
這樣毫不掩飾的鄙夷和輕慢,但凡是個人,都會難以承。
但在不在意,似乎也沒什麼用。
夏柳兒……他沒提起,也忘了過問,也不知夏柳兒的心口疼最后怎樣了。
這晚并沒想到,第二天夏柳兒那里就出了事。
正是忙完一整個早上剛得空歇一會兒時,玉溪急匆匆過來,告訴萬福園那邊鬧了起來,說是小珍忌恨夏柳兒,有意打翻了香爐,將燒紅的香灰灑到了夏柳兒臉上,險些讓毀容。
雖是有驚無險,但夏柳兒坐在床邊哭了半天,下人去來了駱晉云,駱晉云一早連衙署都沒去就去安夏柳兒,最后當即命人打發小珍,在萬福園訓誡,讓所有奴婢用心辦事,若再有懈怠,必嚴懲。
聽見小珍的名字,薛宜寧便知這事自己是摘不掉了,因為小珍就是自己派去照顧夏柳的丫鬟。
若這錯是芬兒犯的還罷了,總歸芬兒是老夫人派過去的人,可偏偏是自己安排去的,旁人會不會想,這是暗中待給小珍的差使,故意要將得寵的夏柳兒毀容?
但這事,完全無從辯解,沒有任何反駁的余地。
子清端來了藥,讓趁熱趕服下,大概是怕因這事煩心,又勸道:“咱們是當家夫人,任跳到天上去又能怎樣?夫人趕生個嫡子,才是要的。”
薛宜寧看著那藥,神微微恍惚。
就在這時,院中傳來靜,幾人抬頭,只見駱晉云自院外進來,緩步走到桌邊,一不看向,臉上帶著微怒。
薛宜寧心知他為什麼事而來,心中不由“咯噔”一下,溫聲道:“夫君。”
駱晉云看一眼面前的藥,將之前的微怒略收斂了下,問:“喝的什麼藥?”
薛宜寧還沒說話,子清連忙回道:“是調理之藥,補子的。”
說調理,駱晉云便大概猜到是什麼藥,進門已有兩年,確實該著急孕育之事了。
沒再多問藥的事,他開口道:“小珍今日一時不慎,將香爐打翻,險些讓柳兒毀容,但好在柳兒幸運,并無大礙。”
說完,他就靜靜看著薛宜寧,似乎在等的回應。
薛宜寧起認錯道:“小珍是我挑選的,當初覺得聰明伶俐,行事穩妥,卻沒想到竟這麼莽撞。這事讓夏姑娘了驚,小珍就由來發落吧。”
駱晉云沉聲道:“倒不忍責罰,我替作主,將小珍發賣出去了。”
薛宜寧想問發賣到哪兒,擔心會送小珍去青樓館那種活地獄,卻又不敢多說,怕更加害了小珍。
最后,勉強說道:“夏姑娘……倒是宅心仁厚。”
也許是演技太差,被駱晉云看出言不由衷,他盯著看了半晌,略帶了一嚴厲道:“薛宜寧,不是每個人,都有你這樣的出。”
薛宜寧怔怔看向他。
隨后便聽他繼續道:“柳兒只是個姨娘,見不了外客,進不了族譜,的出,注定妨礙不了你。”
“夫君,小珍的事……”
沒讓辯解,他打斷了,直接吩咐道:“你盡快給那邊安排新人吧,安排好后給我過目。”
薛宜寧咬咬,將心里的委屈悉數咽下,終究是順道:“好,我盡快去安排。”
駱晉云走了,連背影都帶著幾分余怒。
明白,他生氣了,生氣在他眼皮子底下使這種招,差點害夏柳兒毀容。
可是,哪怕他給一個辯解的機會……的確出好,的確從小就學著怎樣做一個主母,所以知道怎樣毫無聲息磨一個妾室,卻為什麼要用這樣愚蠢的招數?
更爽直一些的玉溪不悅道:“照這樣說,那夫人干脆什麼也別做了,小珍犯錯就是小珍犯錯,那可是駱家自己采買的丫鬟,怎麼還要扯到夫人上!”
薛宜寧沒說話,頹然在桌邊坐了一會兒,想起什麼來,緩緩抬頭道:“子清,你去看看小珍出府了沒,若沒有,找機會去見見。”
子清聽了令,趕出去了,過了兩刻之后回來,進屋就關了門,朝薛宜寧稟報道:“夫人,我見到了小珍,你猜小珍說什麼,說當時替夏姑娘拿枕頭,不知道怎麼地,夏姑娘就撞了一下胳膊,然后那桌邊的香爐就掉下來了,香料掉到了床上,落了些在夏姑娘肩頭,可沒等反應過來,夏姑娘就驚一聲,然后捂著臉大哭起來,問做什麼,一慌,就馬上跪下來認錯。
“后來等將軍過去,被發落,收拾了東西才突然想起來,那香爐明明沒放在桌邊的,很注意,都放里面些,不會太靠外。而且還說,其實夏姑娘一直就不喜歡,更喜歡芬兒,本就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犯錯,沒想到最后還是這樣……”
薛宜寧聽了,半晌沒回話。
子清忍不住問:“夫人,你說這事,是夏姑娘故意設計的嗎?就是要弄走小珍?”
“弄走小珍,順便給我安一個蛇蝎毒婦的罪名,這府上若有人要毀容貌,自然只有我。”薛宜寧嘆聲道:“小珍,是被我連累了。”
一旁玉溪氣憤道:“怎麼這麼能折騰,以為扳倒了夫人,就能扶正?”
薛宜寧抬頭看向,喃喃道:“其實,也不是不可能,是良妾,又得夫君寵,離正室就差一步之遙。”
玉溪頓時啞口無言。
不錯,夏柳兒的確是可能被扶為正室的,特別是在駱晉云喜歡的況下,就算老夫人不太滿意也沒辦法,因為這家里明顯駱晉云能全全作主。
所以,夫人還是要趕懷上孩子,生下嫡長子,這樣才能暫且穩固地位。
子清似乎也想到了這一層,連忙看向旁邊桌上放著的藥碗,著急道:“藥差點忘了喝,怕是冷了,我再去溫一下。”說著就端了藥離開。
薛宜寧看著的背影,沉默無言。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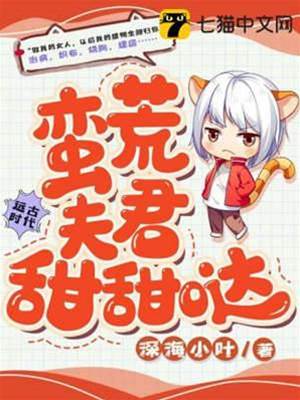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306 -
完結154 章

二小姐進京了
沐羨之穿成了沈相爺家多病,從小養在山上道觀里的二小姐。彼時沈相夫妻剛去世,面對龐大的產業,親戚們虎視眈眈。性格軟弱的長姐被欺負得臥病在床,半死不活。要面子好強的三妹被退了婚…
52.8萬字8 23736 -
完結571 章

滿門炮灰讀我心后,全家造反了
喬嬌嬌上輩子功德太滿,老閻王許她帶著記憶投胎,還附加一個功德商城金手指。喬嬌嬌喜滋滋準備迎接新的人生,結果發現她不是投胎而是穿書了!穿成了古早言情里三歲早夭,戲份少到只有一句話的路人甲。而她全家滿門忠臣皆是炮灰,全部不得好死!喬家全家:“.......”喬家全家:“什麼!這不能忍,誰也不能動他們的嬌嬌!圣上任由次子把持朝綱,殘害忠良,那他們就輔佐仁德太子,反了!”最后,喬嬌嬌看著爹娘恩愛,看著大哥 ...
105.3萬字8.18 17760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