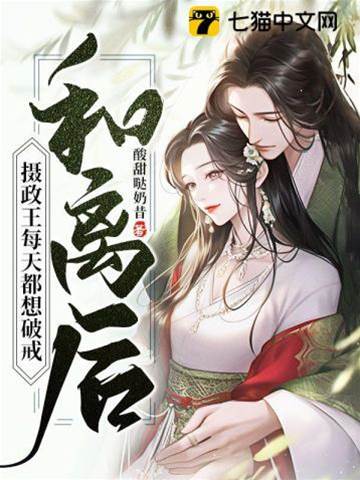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逐鸞》 第2章 第2章
“快走!”
長解鄭恭兇神惡煞地催促著落后的流人。面慘白,疲憊不堪的流人踉蹌著加快步伐。
荔知走在隊伍中后段,為了節約力氣咬牙關,一字不發地迫自己往前走。
汗珠從通紅的面頰流下,匯漉漉的領,后背的汗水早已打里,冷風一吹,像井里撈出的汗巾在上,荔知不由打了個冷噤。
卷著雪片的風呼嘯在開闊的山谷中,穿過禿禿的枝椏時發出鬼哭狼嘯的聲音。
謝蘭胥的馬車落在隊伍最末,一名衙役坐在車頭駕車,揮舞著馬鞭驅趕落后的流人,車上四鑾搖搖晃晃,鈴聲不斷。
鈴聲帶著荔知回到昨夜。
風聲沙沙,樹影婆娑。
無邊蒼穹下,謝蘭胥散著烏黑長發,如玉耀的面龐上著淡漠的彩。慵懶半披的螺鈿紫大袖衫在細雪中涌,一條紅灰的帶垂在邊,皎潔的月讓他一塵不染,像是云頂淌下的銀河。
踩碎枯葉的聲音讓馬車前的謝蘭胥抬起了頭。
四目相對,他若無其事地笑了。
役人的怒罵和催促讓荔知回過神來,一地月影隨風而去。/的痛苦重新被喚醒,相比起長途跋涉的折磨,腸轆轆本不算什麼。
紙一般單薄的鞋底清晰到腳下的每一塊砂礫石塊,為了減輕痛苦,荔知拿出失而復得的手帕,想要將其墊進鞋底。
剛剛彎下腰,一聲尖利的破空之聲打破了平靜。
“啊!”
一名短解捂著脖子上鮮淋漓的箭矢,瞪著驚恐的雙眼倒了下去。
嗖嗖又是幾支箭矢進人群,流人隊伍霎時大。
“山賊來了!快跑啊!”
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所有人都往前奪命狂奔。
Advertisement
荔知被驚慌失措的流人撞倒在地,還沒來得及爬起來,一只裹在草鞋里的大腳就向手腕落下。
幾乎是下意識的反應,荔知出另一只手,握住自己戴著貝殼手鏈的手腕。
流人的大腳落在的手背,一陣劇痛。
荔知變了,咬的牙關卻沒有傳出一聲痛哼。
待踩踏的流人奔向前方,抓住機會爬了起來,站穩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鏈,雖然手背被踩破了皮,但好在護住的手鏈安然無恙。
第二件事,就是看向隊伍末端的馬車。
山林中沖出的山匪騎著瘦的馬匹沖向流人隊伍,高舉的砍刀在灰白的天空下發著寒。嘶吼震天,好吃懶做的役人無論是從意志還是數量都被絕對倒,只能狼狽逃命。
無人顧及的馬車被棄在路間,謝蘭胥被幾名山匪拉出馬車,強行帶上一匹黑馬,轉眼就向林中絕塵而去。
山匪擄走謝蘭胥后,為首模樣的山匪吹響口哨,召集同伴調頭撤退。
短短一盞茶的時間,謝蘭胥和山匪就消失在了林間,只剩驚魂未定的流人和衙役面面相覷。
“所有人都先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一名甄迢的長解還算有幾分主見,大喊出聲。
六神無主的眾人跟著他的指示,急行了一段路,在一背靠山崖的空地前停了下來。
直到這時,役人們才總算想起清點人數。經過剛剛那麼一遭,流人了十九個。
別說十九個,就算再十九個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沒的那十九個里,包含一個廢太子孤,這說不準會是掉腦袋的大事。役人們你看我我看你,個個都滿臉焦慮。
荔知對謝蘭胥的擔心,比他們只多不。趁混剛過,人多眼雜,悄悄靠近正在商量對策的役人。
Advertisement
“現在的山匪怎麼這麼大膽子,連差的隊伍都敢襲擊?”
“很明顯他們就是沖著廢太子孤來的,我們是不是要稟告上級?”
“廢話!這麼簡單的事兒還用得著你說?!”
鄭恭呵斥完上一個城池派來的短解,轉頭看向和自己同屬一個署的長解甄迢:
“甄兄,平日你見多識廣,你說——我們現在怎麼辦?”
甄迢有些出神,臉上表捉不定。被鄭恭喚醒后,他依然顯得有些躊躇。
役人們都不解地看著他。
片刻后,甄迢定神道:“我們已經走了大半行程,此時調頭反而花費更多時間。不如讓一名腳程快的,快馬加鞭六十里,向重城縣令稟明此事后調兵營救。”
役人們沒有更好的主意,便同意按甄迢所言行事。
鄭恭帶著兩名短解去解馬車前的馬匹時,荔知皺著眉頭快速思索。
三十里快馬加鞭,再加上稟告縣令調兵遣將,來回最也要一夜。如果是廢太子的政敵想要斬草除,一夜的時間足夠謝蘭胥死個千百回。
變數太多,無法袖手旁觀。
流放之路荒無人煙,即便逃跑功,最后也只可能是落虎口或是迷路死,再加上流放罪人大多帶著沉重的木枷,衙役們本不擔心流人擅自逃跑。
托了看守松懈的福,荔知趁他們在卸馬車無暇其他,悄悄往林間挪去。
原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行,被荔知同父異母的妹妹荔香看見了。不可思議地瞪大雙眼,質問口而出:
“你要干什麼?!”
無數目向荔知,在被役人攔下之前,荔知頭也不回地往林中奔去。
“站住!”長解鄭恭氣急敗壞地追了上來。
若是被捉住,不單救不了謝蘭胥,自己恐怕也會沒了小命,荔知使出吃的力氣不要命地狂奔,不知什麼時候,林間只剩自己一人。
荔知停下腳步,氣吁吁。打量四周環境,尋到夕的方位,據早年在一本游記上看到的方法,辨別出東南西北。
朝向找到了,想要找到來時的路就容易了。
荔知花了快一炷香的時間,終于走出林間。豁然開朗后,眼前便是剛剛發生戰斗的空地,無人收殮的尸就這麼曝尸荒野,等待野顧。
沿著山匪消失的方向,毫不猶豫再次踏茂的樹林。
馬蹄踩踏必然留下痕跡,尤其是大隊人馬經過的地方。荔知輕而易舉就跟著馬蹄印找到了山匪們的大本營。
山寨坐落在山頂,寨墻依山就勢,大門閉。簡陋的瞭塔上坐著兩個正在值守的山匪。
荔知借著山林掩飾,略觀察了山寨的環境,能夠看見的寨墻最矮也有二十尺,想要靠翻墻混進山寨毫無可能。
如果不能混進去,那就只能讓山匪自己帶進去。
荔知看著地上的齏雪,決定賭一把。
……
“什麼?有個人想要投奔我們山寨?”
披著狼皮的太師椅上,形魁梧的山寨大當家瞇眼看向下方匯報的小弟。
“的——十四五歲,說自己是此次押解的流人之一,因為我們才有機會從隊伍中逃出來。”小弟解釋道,“看門的兄弟不知怎麼置,特來稟告幾位當家。”
“這有什麼不好置的?”長發披散的二當家說,“既然是的,就和寨子里擄來的人放到一起——寨子里的兄弟們難道還怕人多嗎?”
二當家和大當家換了一個邪的眼神,兩人默契地大笑起來。
“可是——可是……幾位當家還是看看人再說吧!”
“這人可是有什麼稀奇?”大當家被挑起了興趣,“既然這樣,那就讓進來,我們三兄弟親自掌掌眼!”
小弟領命而去。
不一會,小弟再一次踏進群英廳的門檻。
“快進來,我們當家的要見你!”小弟朝門外喊道。
太師椅上的三位當家不約而同朝門外去。
方方正正的門框,細碎的塵埃在鮮艷的夕里飛舞,一名著素的低頭進門檻,像一片迷路的雪花。
三位當家的視線都凝在上。早先的輕視不知不覺消失不見。
“你抬起頭來。”大當家沉聲發話。
像是遲疑,又像是怯弱,大當家發話片刻后,才緩緩抬起了頭。
那是一雙華璀璨的眼眸。小山重疊一般的眉像是在膩白的紙上作畫,漸細漸淡地鬢角。一片雪花停在的長睫上,隨著睫的上下眨,仿佛進三個人的心中。
大當家頭了,剛要說話——
“我要。”
聲氣的聲音來自一直沒有開口的三當家。他龐大的軀陷在椅子里,像一灘羊腸包裹的油。
“咳——”大當家清了清嚨,下呼之出的貪念,“既然三弟喜歡,做哥哥的自然支持。你——你什麼名字?”
荔知重新垂下眼,輕聲道:
“奴名李夏。”
大當家很滿意荔知卑躬屈膝的態度,和悅道:“我問你,你愿不愿意做我三弟的夫人?”
荔知看向癱坐在椅子上的一塊。
“我們三兄弟是同母所生,因府迫不得已落草為寇。”大當家說,“你若愿意跟我三弟,我們今后就是一家人。雖說沒有榮華富貴,但也能吃香喝辣,比你在外流浪好過一百倍。”
“……自然愿意。”荔知說。
“好!”大當家大喜,當即拍板,“擇日不如撞日,今夜我就為你們主婚!”
猜你喜歡
-
完結410 章

寡人有喜了
重生之前,青離的日常是吃喝玩樂打打殺殺順便賺點“小”錢,重生之后,青離的任務是勤政愛民興國安邦外加搞定霸道冷酷攝政王。情敵三千?當朝太后、嬌弱庶女、心機小白花?青離冷笑,寡人可是皇帝耶!…
71.6萬字8 24938 -
完結598 章
宮女奮斗日常
凌歡冰肌玉骨貌若天仙,卻無心權勢,一心想著出宮。最終母子二人皆不得善終。重來一次,她的目標是養好崽崽自己當太后。大女主宮斗文。女主心狠手辣智商在線。情節很爽。
87.7萬字8.18 59562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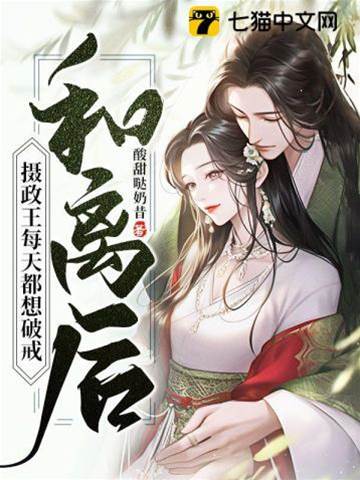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308 -
完結719 章

熾野纏情
【雙潔 花式撩夫 逗逼 甜寵爽文】沐雲姝剛穿越就是新婚夜與人私通被抓的修羅場,新郎還是瘋批戰神王爺容九思!救命!她捏著他橫在她脖子上的刀卑微求饒:“王爺,我醫術高明,貌美如花,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留我一命血賺不虧!”他:“你溫柔體貼?”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很兇殘!”容九思最初留沐雲姝一條狗命是閑著無聊看她作妖解悶,後麵發現,她的妖風一刮就能橫掃全京城,不但能解悶,還解饞,刺激的很!
126萬字8 43209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90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