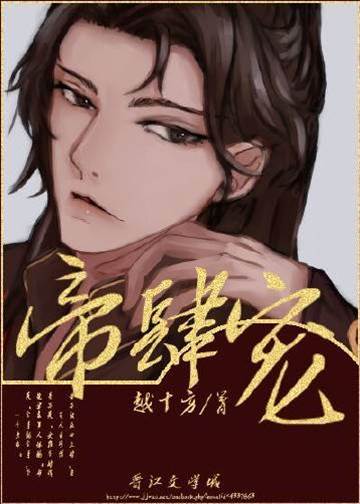《細腰美人寵冠六宮》 第26章 第二十六章
虞姝懷著忐忑又彷徨的心邁殿。
在得知那日自己跳了鱷魚潭, 且封衡毫不顧慮也跳了下去,此刻心幾乎是錯綜復雜的。
絕對不會天真的自信到認為自己魅力無限,令得帝王就連命都不顧, 也要主中的人計。
據說皇上的武功可以以一抵百,大抵是皇上對他自己的實力甚是自信,區區鱷魚潭本不放在眼里。
至于春桃的死, 虞姝倒是沒有懷疑到后宮其他嬪妃頭上,卻是……覺得皇上甚是可疑。
皇上登基三載, 至今僅有一個公主和一個皇子,子嗣不。想來定會惜孩子, 春桃卻大膽到要讓后宮嬪妃絕育,皇上豈能寬恕?
當然, 皇上要弄死誰,不是能夠置喙的,更是不覺得春桃死得可惜。
不是佛普照的大度圣母,春桃這些年的所作所為,足可以讓對春桃的死為之一笑。
這大抵就是惡有惡報了吧。
思路千轉百回之間, 虞姝已經來到了前,王權退開了幾步, 但并未離開,這天化日之下, 王權以為皇上必然不會像那日一樣失控。
他可是看著皇上長大的,對皇上那可怖的自控力甚是了解。
皇上是一位清冷自持的君主!
誰知, 王權剛站定,封衡便眸幽幽的看了他一眼。
王權一噎。
封衡淡淡啟齒, “王權, 你還有何事?”
王權還有什麼不明白呢。
他終于了前多余的人了, 忙垂首,“皇上,老奴告退。”
他連連后退了數步,這才轉過,一路疾步走出了書房,還很心的從外面關上了殿牖。
外面的線被隔開,氣氛陡然不對。
虞姝恍惚了一下。
Advertisement
是因何而來?
對了!
是來報恩的。
如今姨娘與二哥的一切都在好轉,便也不像一開始那樣求帝寵。
人一旦沒了目標與求,果真就容易消極懶惰。
但捫心自問,虞姝激帝王。不喜歡虧欠任何人,總該報之以瓊瑤。
封衡看著前的子,半斂眸,穿了一套前幾日已經穿過的低領束腰云錦宮裝,發髻統統盤起,只余耳旁幾碎發,脖頸顯得纖細雪膩,往下是一大片如雪般白皙的鎖骨。
封衡目落在了那繡了一片荷花瓣的襟領口上,眸一度暗了暗。
殿安靜到針落可聞。
虞姝等了小片刻,沒有聽見靜,稍稍一抬眼,正好發現了帝王的目。
虞姝順著封衡的視線低頭一看,頓時到耳子如被火燒,滾燙了起來。
“皇、皇上?!”低低質問,到底是不敢放肆。
虧得坐在龍椅上的男子是帝王。
若是換做旁人,早已被虞姝罵做登徒子、浪兒。
封衡倒是落落大方,毫不遮掩。他就如同豺狼虎豹,攻略十足,眸也是如此。
他是帝王,虞姝是他的后宮嬪妃。
他看,自是天經地義。
封衡角掠過一薄涼,似笑非笑,讓人不敢造次。
“你二哥的病已有好轉,他自習武,子骨強健,不消幾日就能下榻行走。朕才惜才,日后會重用他。”
封衡的目仿佛在傳達這麼一個訊息:話已經說到這份上了,虞人你自己看著辦吧。
虞姝將涼茶擱置在龍案一角,再度福行禮,“嬪妾多謝皇上搭救二哥之恩,嬪妾……定會永記皇上恩德。”
封衡眸微微一挑,“哦?那妃打算如何謝朕?”
Advertisement
話,已經說得更加明了了。
虞姝抬首,無疑,甚是錯愕。
明明聽聞,皇上是個寡淡、自持之人。
封衡對出了手。
虞姝愣了一下,意識到沒法后退了,遂只能把自己的手過去,封衡一握住就稍一用力,把人直接撈了過來。
虞姝大吃一驚,好在這一次有了經驗,沒有嚷嚷出聲,雙手本能的抵在了帝王的膛。
手心隨即一燙,詫異于帝王子骨竟這般/滾/燙。
虞姝已經能知到對方不尋常的氣息。
聽說皇上這幾日都忙于政務,并沒有踏足后宮,這個時候過來請安,便正好是羊虎口。
但,虞姝也不矯,的確心有余悸,可也知道得寵才是在后宮的唯一出路。
來都來了,還畏畏作甚?暗暗告誡自己。
矯給不了安立命的資本。
想通之后,虞姝糯糯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皇上,去、去別可行?”
這里可是書房!
這算不算是間接坐在了龍椅上?
為了坐穩了,的一只腳還踩在了龍椅的邊沿。
后背抵在龍案,陣陣生疼。
封衡卻不依。
就仿佛塵封了二十一年的困/終于蘇醒,他更像是得了一件中意的玩,若非有意克制,當真可稱得上是不釋手。
再者,他素來疑心重,很難信任任何人。
虞姝則不同,是救過他一命的子。
因著這一層緣故,又有清容與傲人段加持,便讓虞姝現下為了封衡唯一/的子。
人都到手上了,沒有再放走的道理。
封衡倒是覺得龍椅上甚好,直接把虞姝提到了龍案上。
龍案左右兩側擺放了冰鑒,視野亦是寬闊,無疑挑起了男人的胃口。
礙事的奏折被一手拂開,封衡低低一笑,那張素來清冷無溫的臉上,浮現一抹邪意,“朕覺得,此甚好。”
虞姝,“……”
默不作聲,著龍案上的冰涼與順。
甚至還想象的到,這個地方,每日都有大臣與帝王商榷國家大事,探討山河國運。
如此莊嚴神圣之。
而,正與帝王做著荒/唐之事。
不消片刻,虞姝又要嚇哭了。
本不是一個脆弱之人,也萬沒想到自己會這般沒出息,哭得急了,鼻孔里冒出一個泡泡,誰知恰被封衡看見了。
他像是瞧見了什麼新奇之事,竟是愈發得意。
如草原之上追逐獵的野豹,狂放極了。
虞姝的手無安放,到了一塊玉質極好的鎮紙,忽然想起一樁事來,帝王登基之,先帝黨羽之首,曾對新帝不敬,被封衡用書房龍案上的鎮紙砸破了半顆腦袋,那位大臣一月之后不治亡。
虞姝哭得更厲害了,立刻推開了那塊可怖的鎮紙。
許久……
久到虞姝昏昏沉沉的做了許多夢。
夢見了諸多模模糊糊的場景。
好像其中一個畫面,便是與帝王在樺樹林的巨石上,的/兜/又是岌岌可危,還被帝王嘲笑是個哭包,那片樺木林綠蔭匝地,飛鳥群。
虞姝驚夢醒時,人已經躺在了書房殿的塌上。
如蝶羽的睫扇了扇,眸中漉漉的,像迷途羔羊,支棱起子,抬頭看向半開的窗欞,只見外面的日頭已經往西邊移了。
這都到了午后了麼?
一朝得帝寵,不知今夕是何夕。
淑妃這三年來獨得圣寵,是如何渡過這漫漫三載的?
虞姝實在太好奇了。
剛要下榻,雙足才落在楠木腳踏上,封衡從外間款步走來,男人已經沐浴,鬢角發微,五襯得更是立,他上只披著一件寶藍綾羅綢緞中,這種材質的料甚是,可以毫無保留的襯出男人頎長修韌的段。
寬肩窄腰長,一覽無余。
就連膛的廓也若若現。
只看了兩眼,虞姝立刻撇開視線。
以前只覺得隔壁的沈家哥哥生得俊,卻不想皇上更勝一籌,如此俊的男子,若是生在世家高門,早就被貴門踏破門檻求結親了。
有些像辰王……
大概是親兄弟,眉目之間有些神似。
思及辰王,虞姝立刻讓自己撇開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
年的歡喜,大多都是一場虛無的荒唐。
封衡在塌邊沿落座,一只手撐在了虞姝側,迫使又躺了下去。
眼看著男人的臉逐漸靠近,虞姝從花癡中回過神來,一手抵在了男人前,“不、不能的!”
封衡擰眉,“為何?”理直氣壯。
他是天下之主,有何不可?
虞姝嗓子啞啞的,被男人視著,口無遮攔,道:“皇上勤政民、雄才大略、日理萬機,乃曠世明君,如定要以龍為重!”
籠罩在虞姝上的不僅僅是封衡。
還有他上的雪松香。
虞姝不說還好,這一提及“龍為重”四個字,封衡自的認為自己被涵了。
他又往下俯了俯,笑意薄涼,“朕究竟做了什麼?讓你覺得,朕年紀輕輕就需要保重龍?”
虞姝愕然。
說錯了麼?
沒有宮之前,對男之事一竅不通,除卻辰王和沈卿言之外,幾乎不曾接過其他外男,哪里會懂那樣多的彎彎繞繞。
但就在封衡隔著一層薄薄布料,咬了一口時,虞姝豁然明了了。
只可惜,明白的太遲了,已是為時已晚。
以至于到了暮四合之時,才被放出了書房。
封衡又賜了轎輦。
虞姝巍巍走出書房時,回頭看了一眼,燈火之下,年輕帝王已經捯飭的一不茍,恢復了清冷如冰的模樣,正伏案批閱奏折,神專注,眉心鎖,下筆如神,仿佛將他的魂與都注了山河社稷之中。
二十一歲的景,擔起了家國天下。
虞姝愣了一下。
有些分不清,封衡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
林深送了虞姝去朝閣,回到書房復命。
按著尋常的習慣,封衡聽過之后便不會再多言,但他忽然停筆,抬首問道:“虞人回去之后可有不適?”
封衡良心發現了,也知自己今日有些過火。
林深不敢有所瞞,如實回稟,“皇上,人主子一直神蔫蔫,下了轎輦就走向了朝閣庭院中的清泉池子旁,趴在太湖石上不肯回殿,還嘆了一句……”
太湖石曬了一整日,趴在上面熱騰騰的,可以緩解腹痛。
封衡眸一凜,“還嘆了一句什麼?”
林深為難,又不敢隨意更改說辭,按著原話,道:“人主子嘆,說淑妃娘娘當真好力。”
與淑妃有何干系?
封衡一愣,下一刻,全明白了,“……”
當晚,仿佛是采//補/的帝王,力甚是旺盛,就在書房用了晚膳,隨后繼續理政務,還宣見了幾位大臣。
朝中的肱骨大臣們被累到神萎靡,離開時拖著沉重的步子,步步艱辛。
直到心腹立侍前來,封衡單獨見了此人。
十三,是影子人。
顧名思義,是活在暗的人,他們之中有男有,但沒有自己的名字,只按著序號排名。
這批影子人是封衡還是太子的時候,就暗中培養起來的。
普天之下,僅效忠于他一人。
封衡能在先帝十分不喜的況下,依舊順利登基,這批影子人也起到了關鍵助力。
十三抱拳,像個沒有任何緒的木頭人,“皇上,奴才找到了辰王安在后宮的眼線,那眼線如今在尚書閣當差,就在今晚,他一直在朝閣附近徘徊,但虞人閉門不出,眼線沒有尋到機會。”
辰王……
封衡豈會不知辰王與虞姝之間的曲折過往。
那個小子還真會救人。
救了他,也救了辰王。
封衡眸微瞇,在蒼茫夜之下,目凜然,“繼續盯著,不要打草驚蛇,但莫要讓他傳出任何消息去宮外,一旦有任何異,立刻來報。”
辰王只是一條小魚。
封衡真正在意的,是宮外的那個人!
眼下還不是收網的時候。他只是此前沒有想到,會牽扯進來一個虞姝。
十三應下,“是,皇上。”隨即一個轉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
辰王府。
一錦男子從甬道走來,只見不遠的一株水桶細的海棠樹下,白袍男子負手而立,背影拔清瘦,月華落在他上,仿佛將他隔絕在了塵世之外。
錦男子在三步遠的地方站立,抱拳道:“王爺。”
辰王聞聲,先是一頓,隨即轉過來,聲線低啞,像沉默良久不曾開口說話之故,“如何?”聲音有些急迫。
錦男子名溫年,是辰王心腹,跟在辰王邊數年之久。他對辰王與璟帝的兄弟關系甚是了解,對辰王和虞姝之間的過往也比誰都清楚。
故此,溫年比誰都想勸服辰王。
溫年苦口婆心,“王爺,虞姑娘……如今已是皇上的人,王爺您也有婚約在,張丞相把持超綱,您若退婚,就是與張相為敵了啊,太妃也不會同意的。”
辰王仿佛就沒聽見一般,直問,“在宮里過得如何?那個嫡姐可曾欺?說!”
辰王豈會不知虞姝當初在將軍府的遭遇,他甚至于暗中威脅過虞若蘭。
他也知道兩年前,將軍府將虞若蘭和虞姝掉包了,送了嫡宮。
但辰王私心作祟,沒有將此事捅出來。
昨年主請纓前去北地,本以為可以掙來軍功,借此與太妃抗衡,可誰知他還是遲了幾日。
也就幾日!
他已經盡力了。
他真的盡力了。
辰王沒法想象虞姝前陣子來王府三次,卻又三次被慘遭驅逐,那樣的人鮮會有求于人,到底該有多絕,才會登門求助?!
回想那日在書房的形,他看見虞姝低垂眼眸,一副擔心怕的模樣,一人孤在后宮,皇兄又是不茍言笑的男子,應該會怕極了吧?
辰王垂在廣袖下的手掌,死死握,手背青筋凸起,再度質問,“說!”
溫年無法,只得如實說話,“王爺,咱們安排在皇宮的線人,暫未送出消息,又或者……消息沒法傳遞出來。”
溫年的話已經很委婉。
封衡雖年輕,才問鼎帝位三載,但絕非是可以糊弄的君主。
線人到底還在不在,已經難說了。
辰王眉目鎖,夜之下,他眼中微和月華重合,像有什麼東西在無聲無息閃。
溫年退下,辰王命人送了一壇子老花雕過來。
這酒夠烈,他正需要。
原來,這世上當真有些事,會讓人無能為力……
猜你喜歡
-
完結471 章

王妃日日想和離
前世葉非晚被封卿打入冷院鬱鬱而終,哪想一朝重生,竟重生在賜婚後。 葉非晚再不動情,作天作地、“勾三搭四”、為封卿納妾填房、敬而遠之,隻求一封和離書。 未曾想,那封卿終於被惹惱應下和離,卻在第二日詭異的反悔了,開始漫漫追妻路。 她跑他堵,她退他進,她撚酸他便砸了醋罈子,她要紅杏出牆…… 某王爺:乖,前世今生,冇人比本王更眼瞎。 葉非晚:…… 後來。 “娘子想要睥睨天下還是遍覽江湖?” “有何區彆?” “你若要天下,便是弒神弒佛,本王也給你奪了來。” “那江湖?” “舍王位,棄功名,此生白首不離!”
85.4萬字8.86 593445 -
完結43 章

君既無情我便休
“相爺,求您快回去看看夫人,夫人真的快不行了,她就想見您最后一面。”“你回去告訴她,她若不是真死,那麼……本相便送她一程!”——在南宮辰的心里,蕭傾泠一直都是一個謊話連篇的蛇蝎女子,直到她死的那一刻,他都不曾相信她……在蕭傾泠的心里,南宮辰…
4.5萬字8 25854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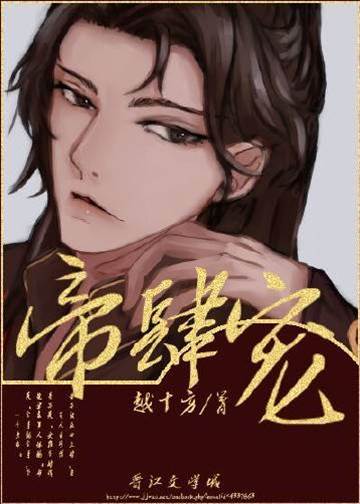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81 -
完結836 章
神偷世子妃
一朝穿越神偷變嫡女,可憐爹不疼繼母不愛,還喂她吃泔水! 為一雪前恥,她廣撒家中不義之財,誰知這劫富濟貧之事竟然會上頭……山賊窩,貪官污吏,吃人皇宮,甚至皇帝寶座……嗯,都能不放過……不巧倒霉偷走他的心,從此「惡魔」 纏身。 「娘子,說好要七天的」 「滾」 「哎,說話要算話……」 「滾」 這哪家王府的世子啊,拎回去挨打好嗎!
153.1萬字8 19823 -
完結337 章

重生后王妃嬌軟不可欺
京城人人傳說,杏云伯府被抱錯的五小姐就算回來也是廢了。還未出嫁就被歹人糟蹋,還鬧得滿城皆知,這樣一個殘花敗柳誰要?可一不留神的功夫,皇子、玩世不恭的世子、冷若冰霜的公子,全都爭搶著要給她下聘。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麼多好姻緣這位五小姐竟然一個都不嫁!她是不是瘋了?冠絕京華,億萬少女的夢,燕王陸云缺去下聘“那些人沒一個能打的,昭昭是在等本王!”宋昭挑眉,“你個克妻的老男人確定?”陸云缺擺出各種妖嬈姿勢,“娘子你記不記得,那晚的人就是本王?”宋昭瞪眼原來是這個孫子,坑她一輩子的仇人終于找到了。這輩子,她得連本帶利討回來了。
61.7萬字8.18 194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