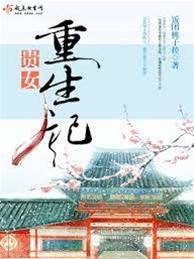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與兄書》 第 5 章 第五章
謝霽顯然沒想到謝寶真一推就倒,微張著淡的,有些怔愣。
“郡主!”紫棠和黛珠駭了一跳,齊齊奔來攙扶起跌坐在地上的謝寶真,又是撣土又是查看手掌,雜焦急道,“郡主您沒事兒罷?傷著哪兒了?”
黛珠‘呀’了一聲,握著謝寶真的手都有些發抖,驚呼道:“手流了!”
說是流,其實也只是破了一點皮而已,和謝霽上那些深深淺淺的新傷舊痕比起來,本算不得什麼。可英國公府的掌上明珠連掉頭發都是大事兒,更不用說傷了。
兩個侍婢心中忐忑極了,原以為以謝寶真氣的子,定要跳起來大鬧一頓才肯罷休。可誰知,平時咋咋呼呼的小郡主此時卻一聲不吭,只垂著頭,生悶氣般看著自己臟兮兮破了皮的掌心,撲簌的眼睫上有晶瑩的淚花將落未落,抿著強撐的模樣可憐得不行。
紫棠很快穩住心神,用帕子極輕地拭去謝寶真傷口上沾染的灰塵,低聲哄道:“郡主別怕啊,上點藥就好了。”
可是府中上下對謝寶真保護得很好,極讓傷,故而廂房中并沒有常備這類藥膏,大多都是燕窩、阿膠糕之類,派不上用場,只能向國公爺和梅夫人請示……可如此一來靜鬧大,兩個侍婢不得要因疏于看管而責備了。
正哄著抿著不語的謝寶真,一旁的謝霽終于反應過來,有了作。
他向前一步,指了指謝寶真的手掌,又比劃了個手勢,也不知道是想表達些什麼。見謝寶真依舊垂著頭,他又執拗地將那個手勢比劃了一遍。
黛珠生怕這位素‘打人’的九郎又傷到謝寶真,忙護住道:“郡主金枝玉葉,九郎下手又沒個輕重,還是離遠些好。郡主的傷,奴婢們自會理干凈的!”
Advertisement
謝霽緩緩放下了比劃的手,果真不再靠近,烏黑的眸子只定定地看著謝寶真。
他的目實在太過扎人,謝寶真忍著淚抬頭,在他眼里看到了些許愧疚。
這位九哥寄人籬下,又是個不能說話的啞,活得像只驚弓之鳥,謝寶真知道方才那一推幾乎是他本能的抗拒,而并非存心有意傷害自己……反正之前自己也曾對他出言不遜過,這跌的一跤就當扯平了。
想到這,謝寶真心中寬了不,但仍是有氣,著睫小聲嘟囔:“若是想道歉就免了,我又看不懂你在比劃什麼……”
謝霽依舊看著,眉頭微皺,又很快松開,然后指了指自己后的房舍,做了個包扎纏繞的作。
謝寶真這會兒看懂了,謝九郎是說自己房里有藥,可以給包扎上藥。
謝寶真屁還疼著,心里也憋屈,本想拒絕,但一看兩個侍婢戰戰兢兢的模樣,又改了主意,挲著掌心的傷口半晌,方踢著腳尖勉強道:“你這有藥的話,就隨便敷點罷。”
“郡主……”紫棠仍有些顧忌。
謝寶真卻低聲打斷:“破點皮而已,何必鬧大了讓爹娘擔心。”
這件事的確可大可小,兩個侍婢對視一眼,喏喏不再言語。
謝寶真跟著謝霽的步子進了一間類似書房的屋子。紫棠說得不錯,謝霽挑的這屋子雖然偏僻冷清,但屋該有的陳設件一樣不,雖不見得多奢華,但勝在整潔干凈,想必是阿爹照顧謝霽的喜好,暗中派了仆役打掃的緣故。
謝寶真剛進門,前方的謝霽忽的停了步子,警覺地轉過來看著。
那眼神依舊虛無,非喜非怒,虛無到極致了便顯得有些冷。謝寶真猝然一驚,然后才反應過來謝霽并非在看,而是越過的肩頭落在跟進來的紫棠和黛珠上。
Advertisement
謝寶真見他沉默地看著侍婢們,便猜想以他孤僻的子,定是不想讓外人進屋。想明白后,回對黛珠和紫棠道:“你們在外頭候著罷。”
主子不讓進門,下人自然不能進門,兩個侍婢不敢違逆,垂首道了聲‘是’。
謝霽果然收回了目。
房間的炭盆里頭也堆著最上等的銀骨炭,卻并未燒燃,只當擺設似的放著。謝寶真到一涼意從骨子里滲出,冷極了。
看了眼在蹲在矮柜旁翻找藥瓶的謝霽一眼,幾乎口而出道:“天好冷,為何不燒碳?”
話一出口便后悔了。
方才好心關切謝霽的傷,卻反被推了一跟頭,這會子還管他冷不冷的作甚?
謝霽并未理會的小糾結,自顧自找到外傷藥,又打了盆干凈的水過來,朝謝寶真微微一笑,示意在書案后坐下。
謝寶真依言坐下,屁還有些疼,不由蹙眉輕哼。
謝霽已擰干帕子遞過來,謝寶真遲疑了一會兒才接過,有些生疏地用帕子拭去傷口周圍的灰塵臟。剛放下帕子,謝霽又將藥瓶遞了過來讓涂抹。
謝寶真拿著那只細口的小瓷瓶翻來覆去看了半晌,才順利拔下塞子,放到鼻端嗅了嗅,然后便將瓶對著傷口倒藥,卻怎麼也倒不出來。眨眨眼茫然了一會兒,才發現里面裝的不是藥,而是凝固的藥膏,難怪無法倒出。
謝霽靜靜地看著折騰,著實沒想到謝家上下竟將這孩慣到連抹藥都不會的地步。
猶疑片刻,他終是敗下陣來,手臂一抬取走了手中的瓶子,隨即拿一旁扁細的玉簽子細細地挑了一尖兒藥膏,剛要遞給謝寶真,卻見極為自然地過雙手,將的手掌心攤開在他面前的案上。
謝霽愣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是要自己幫忙上藥。
還真是個生慣養的小。
謝霽垂下眼蓋住眸中晦暗的愫,角依舊掛著淺淡的笑意,將那玉簽子上的藥膏輕輕點在謝寶真的傷抹勻。
小一看就是十指不沾春水的,指尖白帶,指甲修剪得很是圓潤剔,連掌心的紋理都像是雕細琢般的淺淡漂亮。相比之下,謝霽那雙青紫疊、指腹帶繭的手就要顯得糙可憐得多了。
藥膏抹勻在小蔥白般纖細好看的手上,謝霽角的笑卻越發淡薄。
相對而坐的謝寶真并沒有察覺出什麼不對。
心單純,平日里了委屈也是哥哥們哄著才好的,何況謝霽并非阿爹親生,又世可憐,早已打消了對他的敵意。
這藥膏刺激傷口,又疼又,難得很,謝寶真哼了聲,想要回手,卻被謝霽一把按住。
這人看起來瘦,手勁可真大啊!謝寶真乖乖坐好,不敢掙了。
不一會兒上好了藥,謝寶真便回手吹了吹傷,藥膏被溫化,散發出一子草藥的清香,微涼的覺漸漸取代了先前的灼痛。謝霽將藥瓶和玉簽子整理好歸類,袖口也隨之微微敞開,不經意間,謝寶真又看到了他手上的劃傷。
很想問問謝霽那些傷是怎麼回事,然而張了張,終究又閉上。仍介懷方才謝霽手推人之事,心有余悸……
可那些傷實在太礙眼了,看起來比自己要可憐得多,謝寶真坐立難安,幾番吞咽,終是沒忍住:“……是有誰欺負你嗎?”
晦暗的線中,謝霽側了側頭,肩上一縷頭發自然垂下,出疑的表。
謝寶真小心翼翼地指了指他手上的傷,問:“這些,我爹不管你嗎?”
謝霽恍然,而后拉下袖子蓋住傷口,笑著搖了搖頭,也不知意思是‘不管我’還是‘沒有這回事’。
他好像除了微笑和搖頭就不會做其他的了,而奇怪的是,謝寶真卻難得沒有毫不耐,只是覺得這年傷得這麼重還能笑得出來,著實厲害。
“你傷了右手,不好包扎罷?”抹了藥便忘了疼的謝寶真像是打開了話匣子,又問,“為何選這麼偏僻的住,還不讓仆役進門服侍?”
這會兒謝霽不搖頭了,只用食指沾了點銅盆里的清水,在桌上一筆一劃寫下稚氣的兩個字:喜靜。
謝寶真‘噢’了聲,一邊輕輕按著掌心上了藥的地方,一邊悄悄抬眼打量謝霽,沉默片刻又問:“你謝濟,是哪個濟?”
年依舊用食指沾了水,寫下一個字:霽。
“啊,原來是這個字。”謝寶真眼眸一亮,“我在書上見過:雨雪天晴,怨懟消散,是為‘霽’。‘朗風霽月’也是這個‘霽’,你的名取得真好。”
年下意識彎了彎眼睛,眉骨的傷痕和角的淤青已經很淡了,更顯得他笑容干凈和煦。
“你多大了?”謝寶真打心眼里好奇。
年寫道:十五。
“十五?你竟然有十五歲啦?!”謝寶真不可置信地睜大眼,“我瞧你這個子形,還以為你和我差不太多呢。”
想來也是因為謝霽自小流離在外,吃不飽穿不暖才發育遲緩的緣故。
兩人相對無言了一會兒。
“你給我上了藥,禮尚往來,我也給你包扎一下罷……只是,你可別再打我。”謝寶真抿了抿珠,眼眸純凈,坦然道,“這些傷別人瞧見了不好,會以為謝家苛待你。”
猜你喜歡
-
完結483 章

休了那個陳世美
大閨女,「娘,爹這樣的渣男,休了就是賺到了」 二閨女,「渣男賤女天生一對,娘成全他們,在一旁看戲,機智」 三閨女,「娘,天下英豪何其多,渣爹這顆歪脖子樹配不上你」 小兒子,「渣爹學誰不好,偏偏學陳世美殺妻拋子,史無前例的渣」 腰中別菜刀,心中有菜譜的柳茹月點點頭,「孩兒們說得對! 我們的目標是……」 齊,「休了那個陳世美」
89.7萬字8 1699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612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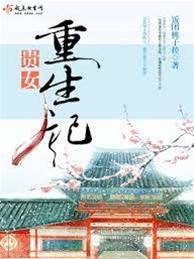
貴女重生記
大晉貴女剛重生就被人嫌棄,丟了親事,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將未婚夫賣了個好價錢!被穿越女害得活不過十八歲?你且看姐佛擋殺佛,鬼擋殺鬼,將這王朝翻個天!小王爺:小娘你適合我,我就喜歡你這種能殺敵,會早死的短命妻!
62.1萬字8 1245 -
連載773 章

洞房夜,給禁欲殘王治好隱疾后塌了床
穿成丑名在外的廢柴庶女,洞房夜差點被殘疾戰王大卸八塊,人人喊打! 蘇染汐冷笑!關門!扒下戰王褲子!一氣呵成! 蘇染汐:王爺,我治好你的不舉之癥,你許我一紙和離書! 世人欺她,親人辱她,朋友叛她,白蓮花害她……那又如何? 在醫她是起死回生的賽華佗,在朝她是舌戰群臣的女諸葛,在商她是八面玲瓏的女首富,在文她是下筆成章的絕代才女…… 她在哪兒,哪兒就是傳奇!名動天下之際,追求者如過江之卿。 戰王黑著臉將她抱回家,跪下求貼貼:“王妃,何時召本王侍寢?” ...
142.7萬字8.18 132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