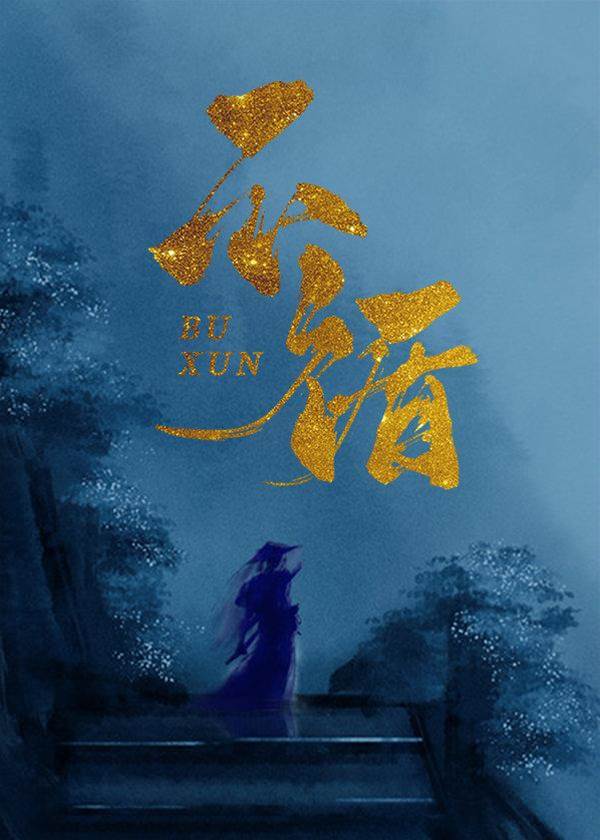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重生后成了權臣掌中珠》 第96章 賠罪
滿院靜寂, 不見半點燈火。
皓月卻已爬上柳梢, 灑下淡淡的霜白清輝。
魏鸞不知盛煜葫蘆里賣什麼藥,難得見他這樣故弄玄虛,倒也沒拒絕。雖然面龐仍微微繃著,腳下卻半推半就,隨他進了廂房。春嬤嬤原打算跟上去,卻覺袖被染冬牽住, 見那位抿搖頭示意, 忙駐足留在原地。
屋門推開, 月照進去,里面似有張白的帷幕。
不過很快盛煜就掩上了屋門, 阻斷亮。
魏鸞這才發覺, 廂房的窗戶都被厚厚的布從里面蒙住了, 以至于此刻門窗闔,半兒月都不進來,屋里只覺一團漆黑。
如此做派,顯然是早有布置。
魏鸞不免心生好奇,黑暗里瞧不清周遭,忽覺某火微閃, 忙扭頭過去。那火是帷幕后亮起的,不過片刻功夫,微紅的燭迅速亮起,過白的帷幕映照出來,朦朧生暈。滿室漆黑中, 那方天地格外惹眼,將整張帷幕照得分明。
也終于看清,那帷幕上繪有綿延的碧草山坡,斜逸的繁茂花樹。
旋即,一道纖小的人影投在帷幕上。
那人影似以錦繡緞帛裁,又像是繪在紙上后裁制,發髻青堆疊,側的眉目婉轉清秀,便連頰上極淡的胭脂都極神似。子削肩瘦腰,上穿著蜀錦短衫,底下繡了折紙海棠的長搖曳,便連腰間的宮绦錦帶都分明。
一眼瞧去,只覺云鬟腰,栩栩如生。
不高不低的鼓聲便在此時響起,纖裊的子漫步于春日郊野,縱無言辭,單聽那鼓點,便覺愉悅歡快。迎面有道影子由淡而深,投在燭映照的帷幕上——那分明是個男子,騎著駿馬著勁裝,正于山野間疾馳,兩道影子漸行漸近,在撞上之前,男子收韁勒馬。
Advertisement
故事由此開始。
帷幕上人影替,在燭映照下鮮妍而生,斷續的鼓點樂聲里,男的聲音流替。魏鸞曾在宮宴上看過莊嚴雄渾的樂舞,曾在赴宴時瞧過唱腔婉轉的曲目,卻還沒瞧過這種把戲,起初只覺新奇有趣,漸漸地有些沉浸其中。
不算很長的戲,卻仍有足夠的悲歡。
相識日久的兩人漸而悉,也有了爭執,男子口出狂言,轉離去。
原本歡快的鼓點在那瞬間忽然停息,只剩滿屋安靜。的目落在出昏紅燭的帷幕,看著后面形單影只的子截然而立,心也輕輕揪了一下。鼓聲的停頓似乎只是片刻,卻又仿佛很久,在極輕的笛聲緩緩奏起時,男人的影子再度出現。
他走得踟躕猶豫,又仿佛決心已定。
青衫磊落的剪影走到子畔,拱手作揖,樂聲也隨之輕快起來。
“先前的事是我行事莽撞出言不遜,惹姑娘生氣,萬萬不該。今日特來賠罪,任憑置。”男子嘎又暗藏溫的聲音響起,是戲里一貫的簡單直白,帷幕上剪影靜止,姑娘背對著他席地而坐,男子則保持著拱手的姿勢。
鼓點漸而輕緩。
盛煜的聲音也在此時湊到魏鸞的耳畔,“你說,該如何置?”
熱乎乎的氣息,聲音亦是溫和的,他開手臂,試探著將魏鸞環在懷里。
魏鸞半顆心沉浸在剪影燈燭的故事,半顆心沉浸在男人的懷抱,明白他安排這出戲的用意后,有些哭笑不得,便輕哼了聲道:“這男人脾氣臭得很,又武斷自負,平白無故惹人生氣,原該遠遠趕走才對。不過看他還算誠心——”頓了下,回看向盛煜。
燭穿帷幕,照在他的臉上。
Advertisement
男人冷的廓被朦朧芒映照得溫,那雙眼深如沉淵,藏了幾分歉意。
像是威風凜凜的獅虎難得低頭。
想了想,很快拿定主意,因知道帷幕后必有不人唱戲,便微踮腳尖湊到他耳邊,用唯有盛煜能聽到的聲音道:“固然誠心可嘉,卻也不能敷衍了事。不若寫封懺悔書,將錯寫明白,往后引以為戒。否則,便是含糊過去,不知癥結所在,往后還會再犯。”
說罷,退后半步微挑黛眉,等他回答。
盛煜的臉有點尷尬。
他原以為,以魏鸞的子,或是氣哼哼地在他膛錘幾拳數落一頓,或是罰他做些事來彌補,終不兒心。卻未料會提出如此要求——天子若犯錯,會以罪己詔檢討過失,他寫個懺悔書,原也無妨。但這東西一旦寫了,往后便是罪證。
就像在手里的小辮子。
但事已至此,他既擺出了這般架勢,總不能言而無信。
遂咬著牙,頷首答應。
……
盛煜寫過無數奏報與衙署公文,卻從未寫過悔過書。
如何開頭,便是個頭疼的問題。
梢間的小書房里筆墨俱全,盛煜擰眉,筆尖遲遲落不下去。
魏鸞則悶氣稍解,自去沐浴梳洗。
待得沐浴畢,換了套細的綢緞寢,鉆進被窩翻了會兒書,連頭發都干了,才見菱花門人影一晃,盛煜長走了進來。仆婦侍皆已退出去,屋里唯剩夫妻二人,他行至榻邊,慣常的頎長姿態,也沒多說話,只側坐上去。
對折的紙箋旋即遞到了魏鸞跟前。
接在手里,并未急著展開,只覷著盛煜神,揶揄道:“寫好啦?”
“請夫人過目。”盛煜說得一本正經。
如此看來,他對這事并不算太抵——魏鸞原本還擔心,以盛煜心高氣傲的脾氣,就算這回有心放低姿態,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也不會太上心,甚至在提筆的時候,改變主意。若果真是這種蠻橫脾氣,往后的路可就難走了。
而今看來,他還是講道理的。
遂展開紙箋,越往下看,角便忍不住彎起,待到最末,輕咳了聲清嗓,正道:“當真是辭藻端麗,兼韻律,窺一斑而知全豹,引類譬喻發人深省,家務瑣事倒跟朝堂社稷有了相通之。夫君這般文采,若當初是以文舉仕,想摘狀元的桂冠,定是輕而易舉。”
這話雖含些許打趣,卻也是真心夸贊。
——魏鸞時讀書,跟著飽學鴻儒,也學過做文章的皮。后來往魏嶠的書房跑的次數多了,雖是去撒玩耍,也跟著讀過不文章,盛煜這篇短論以小見大,絕非尋常讀書人能寫出來的。
倒是把懺悔書寫了明經高論。
這樣的夸贊,也多沖淡了盛煜低低頭認錯的尷尬。
遂了靴,盤坐上床榻,不無得意地淡聲道:“當初我也曾得時相夸贊,算得上文武兼修,考進士如探囊取。”
“失敬,失敬。”魏鸞失笑。
紅綃帳長垂,燈架上明燭的芒簇簇映過來,照得眉目婉轉,旖。這一笑之間,如春初照,冰消雪融,黑白分明的眸中漾起揶揄笑意,流盼生輝,靈可親。在爭執僵冷后,終于又了明艷瑰麗的人。
盛煜笑而臂,將勾進懷里。
“不鬧脾氣了吧?”
“夫君既肯講道理,我自不會胡攪蠻纏鬧脾氣。”魏鸞將臉在他膛,隔著單薄的衫,能聽見里面心跳的聲音。想起那晚母親所說的陳年往事,心中愈發,將雙臂環著盛煜的腰,低聲道:“其實我近來生氣,是因夫君不問青紅皂白,僅以揣測而指責于我。往后,至跟我問清楚,再做論斷,好不好?”
軀在懷里,如此語解釋,足以令盛煜沉溺。
他低頭,在眉間親了親,低聲道:“好。下不為例。”
從庭州千里趕回,卻上如此齟齬,著實勞人心神。
此刻誤會消解,重歸融洽,盛煜長舒了口氣。
親吻自眉心蔓延而下,至瓣、脖頸、香肩,連月分別之后,在臨近中秋的月明之夜,夫妻終得團圓。
……
翌日清晨,盛煜仍未去衙署,在同魏鸞到西府問候過長輩后,騎馬出城。
——既為散心,兼作賠禮。
時日倏忽,離上回夫妻策馬踏青已是半年有余,期間兜轉起伏,形勢迫,魏鸞除了放心不下去朗州之外,幾乎沒怎麼出城。如今朝堂上暫時風平浪靜,盛煜又難得有空暇,便親自做護衛,陪出去游玩。
時近中秋,京城外的濃綠嘉木漸漸轉了,這時節踏青有個好去,是林木繁茂的飛霞谷。這地方有起伏高聳的峰巒,亦有峰回路轉的山坳,里頭林木深,野眾多,可策馬獵烤吃,也可登臨高賞玩秋日風。
因附近人不,盛煜帶魏鸞去的是最深。
此峰巒疊嶂,里清泉迭出,深山里不便閑人居住,倒是修了不道觀。
新安長公主所住的長春觀便在此間。
他是帝王之妹,雖不得章太后歡心,卻頗永穆帝照拂,觀中除了有百上千的侍衛守護外,周遭十數里亦設有路障,不許閑人輕易踏足。唯有公侯卿相、重臣皇親駕臨,護衛才不敢阻攔,多是先恭敬含笑地放進去,再請長公主定奪。
盛煜雖非卿相,卻是生殺在握的權臣。
長公主的那點矯規矩,在他眼里著實不算什麼——譬如兩三月前,他就曾率玄鏡司在此設伏,捕章績。當時他親自去商議此事,新安長公主雖份貴重,卻也很識時務,態度甚是客氣謙虛,說這規矩只為防閑人擾清凈,盛統領是朝廷棟梁,無需客氣。
今日盛煜攜妻游玩,亦長驅直。
侍衛如常去稟報給新安長公主,那位原本正閑坐賞花,聽說竟是盛煜空帶人來游玩,倒覺意外,旋即饒有興致地道:“難得這位大忙人有空,竟也有閑心游賞。稍后傳話過去,請他到觀中喝杯茶。”
作者有話要說: 老盛漸漸低下了高貴的頭顱
猜你喜歡
-
完結1354 章

神醫嬌媳:寵妻狂魔山里漢
“美男,江湖救急,從了我吧!”情勢所迫,她反推了隔壁村最俊的男人。 ……穿越成小農女,長得有點醜,名聲有點差。她上山下田,種瓜種豆,牽姻緣,渡生死,努力積攢著功德點。卻不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勾走了她的心,勾走了她的身,最後還種出了一堆小包砸!
115.2萬字7.82 116552 -
完結789 章

重生王妃又闖禍了
“王爺!王妃把皇後打了!”男人冷眼微瞇,危險釋放,“都是死人?王妃的手不疼?”家丁傻眼,啥……意思,讓他打?“王爺,王妃把宮牆城門砸了!”某男批閱摺子動作不停,“由她去,保護好王妃。”“王爺,王妃被抓了!”“好大的狗膽!”屋內冷風四起,再睜眼,某王爺已消失在原地。自那之後,某妃心痛反省,看著某男因自己重傷,她淚眼婆娑保證,“夫君我錯了,下次絕對不會這樣。”然——好景不長。“王爺,本宮又闖禍了!”
138.1萬字7 264466 -
連載1606 章

有了讀心術後王爺每天都在攻略醫妃
21世紀醫毒雙絕的秦野穿成又醜又不受寵的辰王妃,畢生所願隻有一個:和離! 側妃獻媚,她各種爭寵,內心:我要噁心死你,快休了我! 辰王生病,她表麵醫人,內心:我一把藥毒的你半身不遂! 辰王被害,她表麵著急,內心:求皇帝下旨,將這男人的狗頭剁下來! 聽到她所有心聲的辰王憤恨抓狂,一推二撲進被窩,咬牙切齒:“愛妃,該歇息了!” 半年後,她看著自己圓滾滾的肚子,無語痛哭:“求上天開眼,讓狗男人精儘人亡!”
146.5萬字8 841031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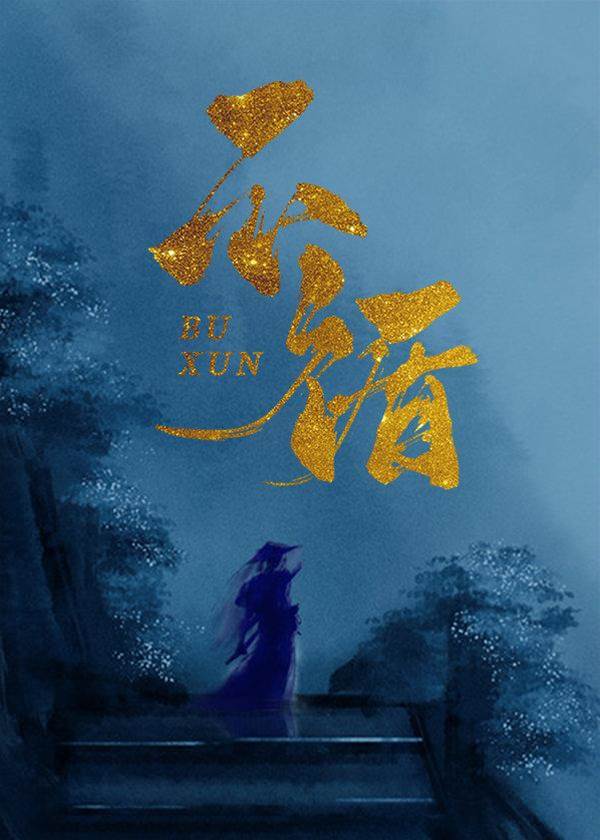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59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