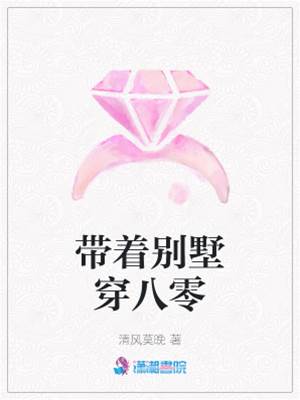《誘甜》 第58章 我有私心。
這是個溫失控的過程。
沈暮薄荷綠雪紡衫的短袖至肩側,細帶也跟著半落不落。
被他抵膝難以彈,小白鞋都掉了一只。
如墜云間般,思緒剝繭,斷斷續續。
該說是巧合還是注定。
沈暮偏就今天穿的不是子。
七分小腳牛仔款式修,包裹纖細筆直的長,腰也是收的設計。
穿搭含蓄但極顯材。
只是對男人而言,肯定不比子方便。
興許是憋得慌,懷里的小貓開始嗚嗚抗議。
江辰遇慢慢停下來。
曲肘支在兩側,眸很深,癮著繾綣。
他松開掣肘的一瞬,沈暮驀地偏過臉大口呼吸久違的新鮮氧氣。
江辰遇居高臨下俯視。
沈暮眼睛朦朧著水,雙殷紅瀲滟,清純的面容此刻渲出后的明艷。
只是模樣凌,看起來慘兮兮的。
不過江辰遇也好不到哪去。
原本端正的領帶被軀底的姑娘扯開大半,松垮掛頸,西裝外套皺地丟在地面。
似乎將他襯衫的第一顆紐扣也拽蹦了。
當然并非有意的。
最主要的,是江辰遇對這姑娘怎麼都褪不下來的牛仔有些無奈。
只能泄勁放過。
沈暮斷著聲息:“你、你干嘛……”
怎麼還強制捉走。
白皙泛的臉又純又分明勾人。
江辰遇低的尾音短促:“你招我。”
什麼賊喊捉賊的新說法。
沈暮眼神無辜:“……什麼啊?”
再深緩幾口氣瞪回去:“你先把我拉走,你先親我的!”
惱時候的語半嗔半怨,脆脆地有如撒,氣息不勻又像黏著。
江辰遇嚨不由溢出聲啞笑。
他大方承認:“嗯。”
略彎:“我只想要個早安吻,你拽著我領帶不放。”
Advertisement
問題被他輕描淡寫地把拋回來。
沈暮愣了下:“我……”
江辰遇垂眸示意自己脖頸:“沒有麼。”
他領帶的溫莎結完全扭曲,是犯罪的證據。
“那是因為……”因為站不穩了嘛。
沈暮底氣不足,抿不語。
故意要給看似的,江辰遇兩指修長了領口:“我紐扣呢?”
是被他咬耳朵時,沒控住勁扯壞的。
沈暮心虛瞟開眼:“……不是故意的。”
試探著反咬:“我推你,你不讓。”
江辰遇溫著笑音逗:“我等下怎麼出去?”
沈暮一聽,瞬間覺得自己也很吃虧啊,把口紅都吃干凈了,誰看不出來他們做了什麼。
“那我也沒法回去啊。”
沈暮癟癟,索想耍無賴,但人還陷在沙發里,被他健朗的軀圈覆著,整個人化般無力。
最后沈暮不愿嘀咕:“可以扯平。”
江辰遇輕笑后靠回沙發,沈暮撐手想跟著起,江辰遇隨后便彎臂攬背將扶坐好。
沈暮臉頰比掃了腮紅還艷。
默不作聲低頭整理散的,又俯將落的那只小白鞋穿回去。
江辰遇倒是沒,任它著。
穿好鞋子,沈暮順手將他扔地的外套撿起來。
“等我下班不行嘛……”
就這麼著急。
低著聲絮絮叨叨,邊拍了拍西裝外套折疊起來擺到沙發一旁。
江辰遇一直在看:“你在我這留便當。”
沈暮抬眸含:“怎麼了?”
江辰遇微掀:“故意讓我抓心撓肝想著你?”
倏地被歸咎,沈暮沒反應過來,老實解釋:“哪有,就是想給你吃啊。”
忽然頭緒一:“不好吃嗎?”
江辰遇笑了下:“好吃。”
Advertisement
心意在他溫回饋后得到肯定,沈暮眉眼不經意漾滿足的笑意,后知后覺地害臊起來。
沈暮一向對年輕人的娛樂活無甚興趣,所以大家約室逃的時候興致是不高的。
但還想和他一起嘗試新鮮事。
因為他的存在。
突然間覺得世界都開始有意思了。
可能是怕他拒絕,沈暮略微斟酌,聲音低緩下來:“喻涵們說想玩室逃,你要一起來嗎?”
其實也認為玩游戲對他來說很稚。
江辰遇卻沒怎麼考慮,只問:“什麼時候。”
誒?
沈暮雙眸不由清亮。
立刻回答:“周五下班。”
江辰遇隨意點了下頭:“知道了。”
接著反倒是沈暮怔愣住。
意外他居然真的愿意陪玩兒。
驀地有了些,有男朋友的覺原來是這樣的啊,似乎做什麼都能擁有這個人無原則的陪伴。
心底一秒擰噴出甜甜的碳酸汽水。
沈暮抿住角樂的痕跡:“那我,先回辦公室啦。”
“再待會兒。”
江辰遇不放人,長臂撈到懷里。
沈暮原是乖坐著的,被他一摟,就側靠到了他上,腦袋正在他左心房的位置。
右臉頰著,過薄的深藍黑襯衫,沈暮能清晰到他堅實的理和男人特別的溫。
心跳一激一躍,沈暮聲調無意:“你耽誤我上班了。”
說話間還是乖乖在他懷里窩著。
沉默頃。
江辰遇忽然問:“真的喜歡這份工作麼。”
沈暮沒多想:“喜歡啊。”
江辰遇:“喜歡畫畫還是工作。”
真是奇怪的問題。
沈暮微頓后回答:“工作就是畫畫。”
江辰遇指腹輕肩頭。
“不一樣,影視工只能在一定的文字范圍變通,不像自由畫家那麼隨意。”
他驟不防正經和聊天,沈暮懵著,而后便又聽他不慌不忙說下一句。
“除此之外也不是純藝,與繪畫不相干的要素很多。”
沈暮約覺他別有深意。
抬頭狐疑覷過去:“你想說什麼?”
江辰遇帶著笑:“我想說,會限制你的天賦。”
沈暮聞言,子往他臂彎再斜進些,安靜無息地自己調整到舒服的姿勢。
江辰遇輕開散落的長發。
“為什麼想考工業設計。”
沈暮理所當然:“因為我是工設畢業的。”
江辰遇略怔,繼而失笑。
無可奈何地掐掐臉:“所以也不是你自己喜歡啊。”
沈暮不假思索:“我不反呀。”
雖然也談不上喜歡就是了。
江辰遇指腹慢條斯理頰側。
過了會輕輕喚一聲:“暮暮。”
沈暮長睫忽,一暖流倏然涌上心間。
這是他第一次這麼。
他的嗓音蘊著被化的穩重,人著迷。
仿佛隆冬雪夜一杯香濃的熱咖啡,彌漫著惹貪的溫暖。
也許是他知道,宋景瀾這個名字永遠都和宋家有牽扯,更想聽現用的。
無形中有熱氣剎那盈滿沈暮的心窩。
愣著。
他繼續說。
“未來很長,你還小,不要圈自己。”
江辰遇說這句話時娓娓可聽,帶有慵然的意味,似是有安眠的功效,能平躁。
沈暮眼波一漾,在他的話里若有所思。
聽懂了江辰遇的意思,也知道工作和考研都是事出有因,可能過程也是生出了幾分興趣的,但那都不是為自己。
靜默良久,沈暮慢慢從他懷中坐起來,在沙發側著,半個子轉過去面對他。
沈暮不否認,只是被他徹底看穿,有點兒憋屈:“怎麼看出來的?”
江辰遇只笑不答。
四年時間足夠到對畫畫的熱。
“去做你想做的事。”
他語氣很松弛,輕巧地如在談論天氣。
沈暮卻有差異,犯難:“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水墨畫油畫,不都是你的強項麼。”
江辰遇頭調侃:“小畫家。”
他過分溫,致使重拾幻想。
說實在的,畢業之前沈暮都沒想過什麼職業規劃,考進院單純就只是喜歡畫畫而已。
自由畫家是大多生向往的生活。
可那都不切實際。
只肖片刻沈暮便泄下氣,嘆了嘆:“可我沒這麼多陶冶的資本。”
斂眸垂下,想藏起眼底的頹然。
“在世畫家要出名特別難,通常都是死后才有價值,如果真的不管不顧只畫畫,我會連自己都養不活的。”
宋家又不是多年前的宋家了。
這就是所謂的夢想很滿,現實很殘酷吧。
待講完,江辰遇靜靜看住問:“我呢?”
沈暮沒明白:“什麼?”
江辰遇微笑間字句清晰:“不是還有我麼。”
誰說沒有資本的。
他完全可以任放肆揮霍。
男人的縱容是溫泉浸潤肺腑,給予無窮的暖。
但同樣也令沈暮患得患失。
因為自己被他放在待遇最優等的位置,而卻什麼都給不了他。
當無法回報給他同等的好,就會產生落差。
這種落差會讓不斷否定自己。
沈暮不敢深這話題,隨口扯到別:“你什麼啊,東藝展的兩千萬就是你討開心買的,跟我的畫都沒關系,我一點兒都不開心。”
聽著很像是秋后算賬。
江辰遇完全放了聲:“我當時不知道是你。”
在這件事上沈暮相當清醒:“知道了也是一樣的結果呀,都不是因為我畫得怎樣。”
江辰遇捉過手,握在指間輕輕。
“不要妄自菲薄,能作為應屆畢業生展足以證明你的優秀。”
時期的經歷肯定是有影響的。
沈暮向來缺乏自我價值。
而眼前的男人恰恰相反,他可靠,思想獨立,世之道慣有分寸。
這些都是沈暮沒有的。
故而在他邊,容易滿足,心理上的滿足。
沈暮無法用語言描述出來。
安全大概是最直接的。
不由自主地像個稚小孩,沖他埋怨:“可是有那麼多院的同學,基本沒人畢業了還選擇純藝的。”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條件和勇氣。”
“我也沒有……”
“你有。”
沈暮眼地過去。
江辰遇對上目:“你給我當書是開玩笑的,也不能讓方碩失業,但我還真想過辭退你。”
沈暮一瞬揚起委屈的小眼神。
江辰遇薄翹起好看的弧度:“不是教過你,要盡其用麼,我可以給你安心畫畫的環境,好好準備IAC的比賽,只要你想。”
他的引導像檀香安神,沈暮漸漸沉溺其間。
太在意他,所以這一刻是脆弱的:“可這樣,我會覺得你在單方面付出。”
江辰遇拇指在手背挲,握著攏著,好似分秒都不舍得松。
“我是認真的,既然談了就沒想過結束。”
一句徐沉聽的低音炮。
沈暮眼睫往上掀了掀。
江辰遇深凝進眸底,口吻鄭重:“為什麼不能坦然接我的好。”
沈暮沉抑著呼吸,有些懷疑況的真實。
半晌聲音細若蚊:“你是不是傻?”
江辰遇端詳一會:“我有私心。”
以為自己聽到能心安理得的理由。
沈暮盯住他:“什麼?”
江辰遇有了笑意:“希你每天都是真的高興。”
他不拐彎抹角,用最直白的話來表達心意。
沈暮大腦一秒充盈甜,像是被他冠上環,可以貪心地做永遠的小公主,在他的寵和擁戴下。
眼前不知不覺朦朧起一層薄薄的霧。
從爸爸媽媽離婚到現在這麼多年,曾經所有的心酸苦楚仿佛都有了存在的意義。
這一瞬沈暮忽然想明白。
原來的人生軌跡是先苦后甜的啊。
沈暮將那口微微哽咽的氣輕輕倒吸回去。
此刻是乖順的:“你是不是早就準備要說這些,所以特意帶我上來?”
無疑他是理智和溫并存的男人。
“不是。”
江辰遇若無其事地否認:“就是想見你,然后吻你。”
他故意把自己說腦。
沈暮住角泛濫災的笑痕。
甜兮兮地腹誹,才不信呢。
沉思頃刻,沈暮溫下聲:“你讓我想想。”
江辰遇笑容分明:“好。”
///
當晚。
沈暮早早就洗漱完畢坐在書桌前。
不得不承認被江辰遇的話說了心。
怎麼會不想呢。
比起錮在工作的框架里,當然更傾慕自在的生活。
社會是適者生存的社會,可既不圓也不要強,適合歸屬私人的自由。
沈暮抱膝坐在靠椅里,長發半半干披散后。
正心猿意馬地想著,突然接到一通境外來電。
是霍克教授。
沈暮看著亮起的手機屏幕,吃驚好半天,回神后忙不迭接起。
霍克先咬著音調上揚的法語出了聲。
“Serin,好久不見。”
沈暮心頭漫起久違的喜悅:“你好教授。”
四年的師生誼能讓人記得深刻。
并且霍克曾在公開場合表達過,沈暮是他迄今為止最得意的門生。
互相寒暄幾句后,霍克說到:“我在IAC的初賽圍作品里看到了你的作品,太驚艷了,讓我猜猜,畫里的麗子是不是你?”
沈暮眼底暖著笑意:“對,是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懷表里的老照片。
霍克又是對好一番盛贊。
最后表明來意:“要不要回來院待一個月,以你的技巧能力,只要再做些指導訓練,我有信心助你在決賽突出重圍。”
沈暮臉上的笑容略微一頓,慢慢愣住。
要回法國一個月啊……
沈暮沒有當場作出決定。
給霍克的回答是考慮兩天再答復。
///
然而直到周五,沈暮都沒想清楚。
對江辰遇和霍克教授都是。
這天下班的時候,工部格外興,因為大家預定好了室逃。
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得知江辰遇要來。
激歸激,但沒人敢搭大佬的車。
故而他們一群人了兩輛出發。
沈暮和江辰遇約在地下車庫,到時,那輛布加迪已經停出來靠邊在等待了。
拉開副駕駛的門坐進去。
沈暮邊系安全帶邊甜甜地說:“走吧。”
江辰遇沒有開車,看了會。
突然好整以暇說了句:“怎麼不人?”
沈暮懵了一下:“啊?”
江辰遇不語,只眉宇帶著淡笑凝住雙眼。
沈暮腦子一時間沒轉過彎來。
他們現在的關系,還要恪守上司下屬那一套嗎?
但出于禮貌教養,沈暮還是不不愿抿抿:“……江總。”
江辰遇微愣,兩秒后沒繃住笑出了聲。
嗓音不言而喻地低沉下去:“讓你這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0 章
薔薇航班
褚穆是最年輕的駐德外交官,霸道強勢、殺伐決斷、喜怒無形。舒以安幸運地見證了他從一個青澀的少年成長為成熟穩重的男人,可惜那些最好的時光,陪在他身邊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學姐陶雲嘉。陶雲嘉為了留學後能進入外交部就職,輕易接受了褚穆父親的提議,背棄了這段感情。所以當褚穆突然向舒以安求婚時,舒以安妄自菲薄地認為,或許他隻是想找一個合適的人結婚而已。在愛情麵前,理智早已無處棲身。縱然舒以安有著百轉千回的疑慮,都敵不過褚穆的一句“嫁給我”。
16.8萬字8 7932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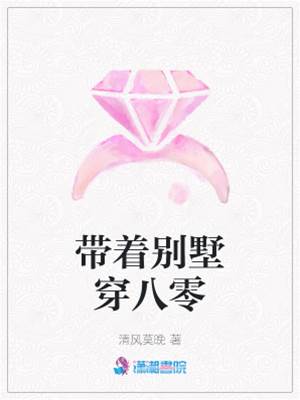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5822 -
完結397 章

豪門二嫁:只偏愛她
她是見不得光的小三的女兒。也是一個二嫁的女人。聲名狼藉的她卻在全城人的目光中嫁給了風頭正盛的沈家大少。豪門世家,恩怨糾葛。再嫁的身份,如何讓她在夾縫中努力生存。而他沈彥遲終是她的良人嗎?
85.6萬字8 9029 -
完結1965 章

寒少寵妻套路深
回國當晚,葉幽幽意外被暗戀十六年的男神吃干抹凈,她表示:幸福來得太突然,要抓緊! 於是坊間流出傳聞,顧家那位矜貴無雙,冷酷無情外加不近女色的大少爺閃婚了! 據說還是被對方死纏爛打拐著去的民政局?! 葉幽幽不屑地哼了一聲,「明明是人家救了他,他以身相許的好不好……」 說完,開始制定婚後小目標,那就是:撩他撩他使勁地撩他。 然而,計劃還沒實施就被某男直接撲倒,美其名曰:「報恩」 當晚,葉幽幽就知道這個男人同樣制定了一個小目標,那就是:撲倒她,狠狠地撲倒她,隨時隨地撲倒她……
340.5萬字8.18 1751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