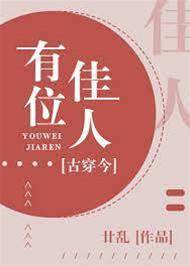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養大小皇帝后他總想娶我》 92
輕的禮樂聲悠揚而起,合宮上下一片喜慶歡愉。
今年的宮宴上,那個不滿周歲的小兒算是焦點,出盡了風頭。凡是生養過的宮妃,命婦,宗親都上前與顧值夫婦說兩上兩句養兒育的辛苦話。
那個昔年顧值離宮時看也沒看一眼的養母賢妃,也搖一變又了那個孩子的正頭祖母,抱著孩子合不攏的笑著。
引得原本興致不大的顧攸也抻著脖子了一眼:“七弟,你說長姐的孩子會是什麼樣的?”
“長姐生的孩子,自然是和長姐一樣了。”顧修應答道。
“那是,佛祖保佑長姐生的孩子可千萬別有一點像那個漠南的老賊鷹,否則我見了他就想他。”顧攸抱著肩膀,關于顧錦遠嫁漠南的事,無論過了多年他也依舊耿耿于懷。
“六哥,你覺得可能麼?”
“那就保佑長姐生個兒,孩子多好啊。”顧攸邊說邊憧憬著幾個月后,顧錦抱著一個白白的小嬰從漠南歸來,到那個時候他便把滿京城的鮮花都挪到公主府去。
顧修沒有答話,但是心里也莫名的憧憬起來。他那個溫端麗的長姐帶著新生的兒回朝省親。他要帶著那個孩子看遍這世上最好的山河,最壯的風,給人世間最好的一切,就好像顧錦護他那樣。
除夕宮宴過后,新歲伊始。
顧修與韓墨初從大年初一便開始在軍營忙碌,忙著督辦初春時節新兵營,以及邊境換防等事。依舊是早出晚歸,連一日也沒有歇過,直接導致戰王府里備下的年貨都擱置了。
氣得辛苦采辦年貨的吳嬸娘叉著腰在院子里嚷嚷:“上好的鴨不吃,大過年的在府里閑一兩日怎麼了?什麼事兒那麼急啊?不能過了年再辦麼?虧得我辛辛苦苦的把這廚房堆滿了,這年前汴京城的菜市都快踩死人了,可憐我那日為了兩尾活魚差點兒同那四五個婦打起來。這倒好,一口沒吃都養起來了。”
Advertisement
吳氏今年四十多歲,兒子和丈夫都死在了靺鞨邊關。顧修去與送了銀子的第三天,便夾著包袱到了戰王府,一分錢月銀不要,做了這府上的廚娘。拿顧修當了親兒子一般照顧起來。
除了廚下的事,顧修和韓墨初這兩個大男人稀里糊涂的日子也幾乎都由持打理,例如一日三餐,四季袍,還有那間在歸云宮時能的波瀾壯闊的書房,都在的打理下井井有條。
吳嬸常說,他們兩個的日子若是沒有在,估計連這戰王府的頂子沒了都發現不了。
顧修和韓墨初都恍惚有種錯覺,這個吳嬸便是晴昭公主冥冥之中給他們兩個派過來的克星。
院子里吳嬸的嘮叨不斷的鉆到耳朵里,書房顧修與韓墨初兩人對視一眼,明顯是鼓起勇氣將房門推開,盡可能快的從院中吳嬸的邊穿過。
不出所料,新一的嘮叨像雨點似的朝兩個人飛了過來。
“誒誒誒,早膳不吃又走了?外頭的東西不干凈知不知道?回頭吃壞了怎麼好!”顧修與韓墨初持著馬鞭往外走,吳嬸便跟在兩人邊追問:“今日什麼時辰回來?用晚膳還是用宵夜,當主子的也給句痛快話啊。”
“吳嬸,我們今日許是不回來了。”韓墨初笑瞇瞇的擋在顧修前給顧修打著掩護。
“又不回來了?日里憋在軍營里,這王府空得都快鬧了鬼了,一天到晚的不見人影。”眼尖的吳嬸還是抓到了顧修的把柄:“今日這什麼天氣啊,殿下又把狐裘了!穿的這麼騎馬回頭再著了風!殿下!你等等!把狐裘穿上再走!”
趁著吳嬸回的功夫,韓墨初與顧修幾步便邁到了大門口,翻上馬的一瞬間兩個人都松了口氣。
Advertisement
“可算是出來了。”顧修坐在馬背上騎出一段距離,才側過子輕聲道:“師父,我想吃餛飩面。”
“殿下,若是給吳嬸知道您不吃府上做的早膳去吃餛飩面,回頭又要去人家攤子上嘮叨了。”
提起這話,韓墨初不由得想起了那個去歲時常帶著顧修顧的豆漿攤。原本是因為他二人上朝的時辰太早,不畘酆想讓府中麻煩。誰知吳嬸知道了,是每日去人家的攤子上檢查每一顆豆子上有沒有瑕疵,最后到底把人到了臨街去擺攤了。
“那,不讓吳嬸知道,不就了?”顧修看著他,明顯是早就打定主意了。
“那好吧,殿下回頭可不要自己招認了。”韓墨初這些日子的心都很好,自從君王口旨不與顧修選妃后他的心氣便順暢了許多,每日哪怕再多的軍報過來,他也能事倍功半。
隨著顧攸的婚期將近,顧修除了日常繁忙的公務外,也不得要去顧攸府上幫著持。
顧攸的未婚妻徐氏,是蘇州人氏。家中曾經數代都是前朝皇家的買辦,如今前朝落寞,家中倒是愈發足。徐氏的父母原本在兒出生時便發了愿,絕不讓兒沾染皇親。不想今日緣分到了,他們也不想做那棒打鴛鴦的事。
唯一的要求,便是希自家的兒能以當時蘇州的婚俗出嫁,次日再皇城行禮謝恩。
上了年紀的君王非但沒有覺得不妥,反而覺得新奇有趣。于他而言,只要不出圈,這婚事辦什麼樣都無妨。
為了這場能全了蘇州婚俗的婚禮,顧攸還特地花大價錢請了幾個蘇州籍的賓相幫著辦。
這蘇州的婚俗與京中的婚俗相差也不算太多,唯有接親時有一套新娘哭嫁,新郎搶親的風俗要守。
為得便是讓這新郎知道這新娘娶之不易,將來才會將新娘視為珍寶。
到迎親那日,新娘家的男丁會守在大門,挨個考問新郎才學。新娘家的眷則會守在中門,挨個考問將來婚后夫妻間的閨閣小事。
若是到了時辰新郎答不出不是新娘子便接不走,新郎及同行的男伴不得還要挨上這些眷幾掌。
足得看著這新郎誠意足了,才能將自家的千金出去。
徐家的父母話也說的很明白:憑你什麼皇親富貴,想娶走我家的珍寶,便要過了這幾關。
從這場婚禮開始籌備時起,顧攸便時不時覺得這是不是他當初伙同幾個兄弟刁難那位阿蘭世子的報應。
要讓這徐家好好把他折騰一通才算完。
寧王大婚前兩夜。
寧王府中燈火通明。
正廳書房之,收拾布置的奴仆來來往往,忙的腳不沾地。顧修撐著額頭,一言不發的看著眼前背著手搖頭晃腦的背催妝詩的顧攸。
“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若道...”顧攸念著念著又卡了下來。
“若道團圓似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顧修嘆了口氣,冷冰冰的提醒道。
“哎呀...七弟...怎麼連你都背下來了?”
“六哥,今天晚上這四句詩,你已經背了不下三十遍了。”顧修無奈的撐著額頭:“是個人都背下來了。”
“那我怎麼背不下來?定是韓參軍您找的催妝詩太難了,能不能再改兩首簡單點的?”顧攸眼的看著一旁正在剝花生的韓墨初:“不然后日我連徐家的院子都進不去。”
“寧王殿下,您要的七首催妝詩臣半月前便給了您了,而且都是七言四句。再簡也簡不出更短的了。”韓墨初拍了拍手上的浮灰,如實答道。
自從聽聞蘇州婚嫁有做催妝詩的習俗,顧修便求著韓墨初給顧攸找了幾首簡單上口的。讓他到了日子,迎親時直接背出來,也省去許多麻煩。
誰曾想這廝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本背不出來。
“那怎麼辦?我這會兒就是背不下來。”顧攸抓心撓肝的在屋里轉圈,忽然如同抓著救命稻草一般的抓住了顧修的肩膀:“七弟,要不后日你替我背吧,不?”
“六哥,后日是你娶親還是我娶親?”顧修抱著肩膀沉聲道。
“啊!!!我不活了!!!娶親太難了!!!”已經人的顧攸再一次不管不顧的一屁坐在地上嚎了起來。
顧攸在地上嚎了兩聲,發現顧修和韓墨初兩個人一個在喝茶一個在剝花生誰也不搭理他。便又悻悻的從地上爬起來,拍拍上的灰塵站在韓墨初跟前,鄭重其事的問道:“韓參軍,過去您給我七弟做師的時候,若是我七弟有書背不下來,最后您都是怎麼辦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