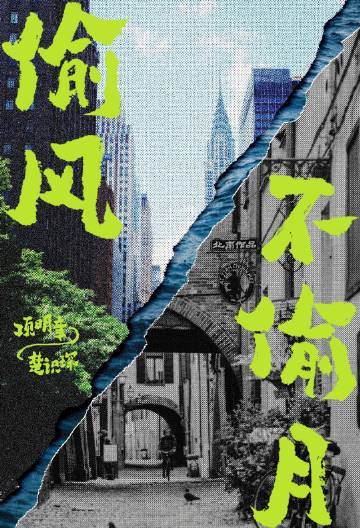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三喜》 86
二爺反應如此之大,沈敬亭自己也是始料未及,徐燕卿急急踱了兩步,轉過來問:“這禮你可退回去沒有?若是還沒,爺這便人送回他丞相府去。”
沈敬亭便說:“這禮我自然是不會收下來的,圜圜年紀尚,并不著急親事。”
徐燕卿松下一口氣,頷頷首道:“還是小君你思量得周全。”
沈敬亭見他這副模樣,暗中覺得好笑,想到他方才所言,便故意道:“依我之見,丞相家的那位公子為人謙和,端方有禮,模樣也周正英俊,現在先不說如何,先觀察下來,若真是個好的,來日和圜圜作一對,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徐燕卿一聽,自是知道沈敬亭是在揶揄他,畢竟徐瓔珞不是他的親兒,他方才那副模樣,儼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徐燕卿無言以對,堂堂尚書大人在朝上牙尖利,卻在自家正君面前,竟被堵得說不出話來。
他一拂袖:“不可理喻,我找圜圜玩兒去!”
“那請二爺慢走。”后頭輕飄飄地響起一句。徐燕卿本來只是佯做要走,這會兒可是非走不可了。
聽到那腳步聲漸遠,沈敬亭無奈地笑著搖頭,也不起來追出去,心道,還是等今夜再回頭來哄他一哄,于是就低頭專心看起賬來。
落花輕飄,窗下,男子一手支頜,一手翻著頁,有哪些不對的,就拿起筆來一劃。
這才清靜了不過一盞茶的工夫,便有一只手掀開珠簾。只瞧那指節分明的纖手執著一小簇玉白杏花,步伐無聲地繞到了男子的后。
沈敬亭正專注地讀賬,未曾察覺那冤家去而復返,直到那杏花在了耳邊,跟著他就被男人從旁邊抱個滿懷。
“哎,二、二爺——”沈敬亭一驚。來人卻摟著他,道:“有道是,桃花爛熳杏花稀,春人不忍為。”徐燕卿強湊過來,在男子的臉上親了好幾下,說,“那小君說,此等春,為夫是負還是不負……?”
第77章 番外(七)
尚書大人無論是在朝上或是人前,大多時候都是橫眉冷眼,輕易不予好臉,獨獨在自家小君面前,那一個沒臉沒皮。這大白天的,二爺就悄悄把下人全打發出去,安的也自然不是什麼好心。
他方才上吃了癟,氣沖沖地去院子轉了一圈,然而徐二爺這悶氣來得快,消得也快,這會兒還不腆著臉回來了,將人摟在懷里輕薄一番。沈敬亭被男人強抱著調戲了一回,臉上又熱又臊,抬手就將徐燕卿推了一推,嗔睨道:“去找圜圜玩兒去,莫在我這兒討嫌。”
他這幾天都忙著徐瓔珞的事,府里的事積累山,這二爺幫不上忙也就罷了,還盡挑在這時候給他添子。
徐燕卿也不惱,心覺小君推他那一只手綿無力,大抵就是做個樣子,故此手臂便由后將那腰環住。沈敬亭掙扎了會兒,反是教他越抱越,徐二爺趁機在那臉蛋上香了幾口,拂過耳垂,果真讓沈敬亭一激靈,小聲道:“……二爺!”
那聲乎乎的“二爺”聽起來似氣惱又似嗔,直喚得徐燕卿心猿意馬,里越發不干不凈起來:“今個兒春正好,小君一人不免寂寞,不如,和爺……好好地‘玩一玩’。”
沈敬亭耳一熱:“你——”話沒來得及說出口,就讓人給噙住了。
徐二爺素來最多花花腸子,便是親個兒也能玩出花樣來。他將人扣在懷里,那舌頭跟條狡猾的水蛇也似,不住地招惹人去,直將人挑逗得又又憤,方深吮慢吻,四瓣分分合合,在這花香滿溢的室親得滋滋作響。
俄而,二人分開,只看男子面頰紅霞,呼吸不順地輕著,他耳邊別著一簇杏花,杏花白瓣芯,是極其的,更襯得眼前人而不,而不妖,瞧得徐二爺也氣息不均起來,兩手不由越來越重地起這個子來。
“二爺,不、不可……”沈敬亭微弱地掙了又掙,倒也并非是假正經,只不過眼下天化日,拋下一大堆正經事不干,竟在這書房里頭白、白日宣……
“不可?不可什麼……嗯?”男人毫不正經的輕笑聲和窸窸窣窣的聲響在耳邊回。
沈敬亭被逗得又恨又惱,忍不住去掐男人的手,徐燕卿吃痛地“哎哎”地了幾聲,可是非但不肯安份下來,反倒是越挫越勇,將那整整齊齊的裳得凌起皺,之后就在嬉笑聲之中扯松了帶,總算將雙手探進沈敬亭的服里。
沈敬亭兩手抵于案頭,那炙熱的掌心一住,他的子便了一。徐燕卿由后摟著他,住他的子,在那散發著異香的頸窩親了又親,嘶啞地絮語:“小君這些天,想不想為夫?”
這陣子,沈敬亭白天忙得腳不沾地,有時候夜里回來,就在自己的院子歇了,如此一來,不小心便冷落了自家夫君。
那一只手按著自個兒的口,得男子覺得心口都發熱起來。那熱度從心口,漸漸地升溫,由上頭燃燒到了腰腹,神不知鬼不覺地,染指到那于啟齒的地方。沈敬亭被撥得臉紅氣,上卻不甘道:“你……貧、貧。”
“哦?”徐燕卿不怒反笑,覆在男子間的手掌驀地握住了那半不的玉。那灼熱的掌心一到弱,沈敬亭便猛地一躬子,整個人往前趴在了案子上。
舊時乃是按流水記賬,一旦攪了思緒,那就是前功盡棄,又得重頭翻過。沈敬亭真是氣都來不及氣,那住玉的手心便緩緩地捋起來,霎時,這惱意就化作春水,流淌心間。徐燕卿見他眼神逐漸迷蒙,分明是快得很,忍不住輕咬著他的耳垂道:“小君心里不想,此……倒是想爺想得很。”
跟著,掌心就到了后頭,用力拉扯幾把,就將那子給拖拽下去,一對白的玉便彈出于眼前。沈敬亭忽覺下一涼,不一陣哆嗦。
徐燕卿著那兩團,下手時輕時重,這雙白瑩潤,時便如一對玉兔輕,徐燕卿玩興大起,含笑地嘶聲問:“小君口是心非,你說,當不當罰?”
沈敬亭睜開潤的眼,氣呼呼地往后一瞪,輕哼了一聲。這一瞪,反教男人骨頭一,下腹邪火急躥而來,只不過,徐二爺馳騁風月慣了,定力尤為驚人,他見沈敬亭毫不買賬,臉上反是勾一笑:“……看二爺怎麼整治你!”說罷,揚手就在那屁蛋子拍了一下。
“啪”地一聲響,沈敬亭臉上頓時燒紅起來,難以置信地:“你、你——”
“又。”徐燕卿跟著又打了一下,沈敬亭整個人劇烈一,竟覺后有一麻麻的覺襲來。徐燕卿連打了三下,就看那白花花的玉上紅了一小片,恰似那簇杏花一樣,白中帶,艷麗。徐燕卿正覺快意,哪想卻猛地聽見一聲啜泣,他連忙將人翻轉過來,就見沈敬亭神惱不已,兩眼瞥著旁邊,竟生生被氣得掉了淚。
徐二爺這是玩大發了,須知他家小君臉皮薄得很,哪經得住如此欺辱,趕忙出聲認錯:“我、為夫,為夫知錯了——”徐燕卿趕用袖子為他了淚,著急地哄道:“爺的好小君,好寶兒,好心肝兒,萬萬別氣壞了子,這,要不……我讓你也打回來?”
聞言,沈敬亭破涕為笑,一時之間,宛若春暖花開,就連徐燕卿也不由看得微愣,卻瞧男子紅了紅臉,小聲說:“我不是生氣。”這又教他如何能說明白,他是因為那麻的覺,激之下,就落了淚……
徐燕卿沒想到原來是誤會一場,亦跟著失笑,隨后便俯首溫地將人吻住,曖昧地廝磨一陣,分開時沈敬亭卻又帶著三分懊惱,反口道:“我是惱二爺不錯,你瞧瞧這些賬,可如何是好?”
瞧著這片狼藉,沈敬亭就覺得腦仁疼了起來。徐燕卿鼻息重地將他子了扔到邊上,兩分開,摟著他的腰微道:“那待會兒二爺幫幫你便是了。”說著時,沈敬亭便察覺一個熱頂在會,不正不經地起來,如今箭在弦上,多說無用,加之他亦是被纏磨得,念縷縷繚繞心間,尤其當那熱抵在口,有一下沒一下地頂著,不由子一松。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三嫁鹹魚
林清羽十八歲那年嫁入侯門沖喜,成為病秧子小侯爺的男妻。新婚之夜,小侯爺懶洋洋地側躺在喜床上,說︰“美人,說實話我真不想宅鬥,隻想混吃等死,當一條鹹魚。”一年後,小侯爺病重,拉著林清羽的手嘆氣︰“老婆,我要涼了,但我覺得我還能繼續穿。為了日後你我好相認,我們定一個暗號吧。”小侯爺死後,林清羽做好了一輩子守寡的準備,不料隻守了小半年,戰功赫赫的大將軍居然登門提親了。林清羽
42.5萬字8 13569 -
完結126 章
禁宮男後
他百般折磨那個狗奴才,逼他扮作女子,雌伏身下,為的不過是給慘死的白月光報仇。一朝白月光歸來,誤會解開,他狠心踹開他,卻未曾想早已動心。當真相浮出水麵,他才得知狗奴才纔是他苦苦找尋的白月光。可這時,狗奴才身邊已有良人陪伴,還徹底忘了他……
27.3萬字8 6400 -
完結114 章

貌合神離
你有朱砂痣,我有白月光。陰鬱神經病金主攻 喬幸與金主溫長榮結婚四年。 四年裏,溫長榮喝得爛醉,喬幸去接,溫長榮摘了路邊的野花,喬幸去善後,若是溫長榮將野花帶到家裏來,喬幸還要把戰場打掃幹淨。 後來,溫長榮讓他搬出去住,喬幸亦毫無怨言照辦。 人人都說溫長榮真是養了條好狗,溫長榮不言全作默認,喬幸微笑點頭說謝謝誇獎。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這樣走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溫長榮的朱砂痣回來了,喬幸的白月光也回來了。
32.8萬字8 9088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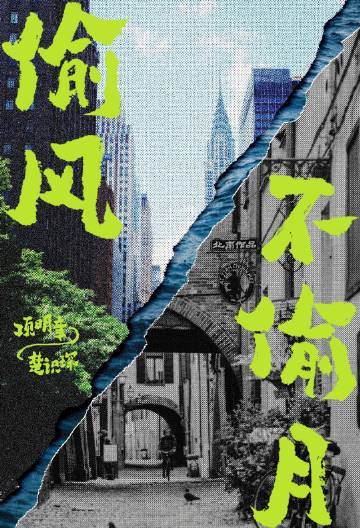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