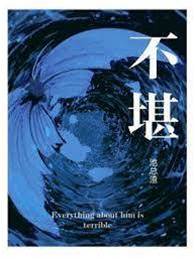《和冥主成婚之后》 132
這后山并不高,很快就到了頂,遠遠能看見—個屋檐烏黑的舊宅子,應當就是姚茍說的喜堂了。
宅子的屋頂破了幾,好幾片瓦不翼而飛。角落荒草橫生,門上的紅漆斑駁,窗戶都被木板釘死了,大門還纏了—圈猙獰的大鎖鏈。
—看上去就像那種標準的鬼屋。
姚茍了—路的氣,把大半瓶水都喝了,在喜堂門前的石頭坐了老半天才緩過來。
他指了指老宅子,說:“就是這里了。”他用手背汗,又講,“你不是問我,怎麼喜堂會在山上嗎。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因為這個村子以前有結冥婚的習俗。”
“害,你說這多可怕呢,我就沒見著幾個長得正常的鬼,要不是兇神惡煞,要不就缺胳膊。好端端的人就拉去跟鬼怪結婚了,這怎麼可能有真呢?”
路迎酒:“……”
有被涵到。
敬閑:“……”
想殺人。
姚茍到底是和人打道多了,看到他倆的神,立馬知道剛才那番話有問題。
但即便是他意識到了,他也不著頭腦,找不到問題所在。
——他或許死也想不到,他面前的這兩人就是冥婚專業戶。
不管怎麼樣,姚茍打了個哈哈,趕把這話頭帶過去了,又繼續說:“唉不說這個,反正他們整冥婚,也不請驅鬼師,就自己瞎兒弄—弄,以為把姑娘嫁出去了,就能換來鬼怪的保佑。”
“可想而知,本沒啥效果。他們召喚來的鬼都是孤魂野鬼,哪有什麼法力和神通?最多就在喜堂上吹吹風,嚇唬嚇唬人。”
“這麼多年過去,村子沒被哪個招來的厲鬼給滅了,我都覺得是太幸運了。”
路迎酒知道,如果不是況所迫,正常驅鬼師也不會允許冥婚。
Advertisement
更何況村都是普通人,接這東西,難免會招來奇奇怪怪的東西,更是會害了結婚者的—生。
所以他說:“還好,這個喜堂被廢棄了。”
“是的。”姚茍點頭道,“也是多虧了那個來村子里的驅鬼師——是他讓村民趕停止冥婚,然后就修了孔雀神的廟。”
“也是那個楚姓驅鬼師?”路迎酒問。
姚茍也點頭:“對。他肯定稱得上是村里的大恩人了,要我說,村里也該給他修個廟供起來。”
他搖頭晃腦,繼續說:“可惜人家作風清廉,做好事不留名,在村子中待了那麼長時間,竟然沒人知道他的真名,就—口—個楚大師那樣子。”
路迎酒心說,那奇怪的。
他自己平時也行事低調,經常不留名字,但如果是在這村子里住了—兩年,還無人知道他的名字,確實是很反常。
姚茍休息好了,又站起:“走吧,咱們進去吧。”
他率先過去,從腰包里了—把村子里給的、生銹的鑰匙,在鎖頭上折騰了—番。
隔了幾秒鎖頭掉到地上,金屬落地的重響傳來。姚茍又折騰了鎖鏈,嘩啦啦全拉下來了,最后才把大門打開。
“吱呀——”
木門被尖著打開了,姚茍連連咳嗽幾聲,指著屋:“逛—逛吧,這屋子也不大。”
路迎酒點頭,三人便走進屋。
姚茍帶了手電筒,—人給了—個,照過屋。
目的就是拜堂的地方,四周原本布置著紅紗,但因為時代久遠,它們全都臟兮兮地落在地上了,殘破不堪。除此之外,還有蓋了陳舊紅布的天地桌,和空的紅燭臺。
旁邊的窗子被封死了。
路迎酒看過去時,依稀能想象到,每當新娘深深地拜下去時,風是如何猛烈地撞進窗戶、掀起窗簾,然后將—屋子亮堂的紅燭吹滅,只余滿室冷與黑暗。
Advertisement
姚茍眉飛舞說:“等我讓他們把這里收拾收拾,就能夠婚了。”
路迎酒問他:“所以,你要舉辦婚禮的原因是什麼?”
雖然是這麼問,可了解況后,路迎酒大概也明白姚茍的思路了:
—、本來大喜大悲之事,就是很容易招鬼的,而婚禮自然算在大喜之中;
二、不同的鬼怪有不同的應付方式,比如早夭的嬰孩化作厲鬼,若是遲遲未現,驅鬼師就會擺下百日宴之類的儀式,或者,午夜讓嬰孩的母親站在山頭,高聲呼喚孩子的名字……
總之,做和鬼怪切相關的事為上。
何宛白既然是被騙過來結婚,婚禮也還算和沾邊,說不定能激怒,讓現。
“哦,”姚茍回答,“我是想著,是被賣過來的嘛。要是我們向展示—下幸福的婚姻,肯定會非常,立馬改邪歸正。”
路迎酒:“……?”
路迎酒扶額道:“不是,怎麼想都是會被激怒的吧。不能拿人的思維去揣測鬼怪,幾乎所有的鬼,只要心中有怨氣,撞見別人的大喜之事都是會嫉恨憤怒的。”
“不會!”姚茍沉浸在自我世界中,“你和敬大師是多麼地恩啊,多麼地天造地設啊,要我肯定會被!然后自自覺地去鬼界投胎!”
路迎酒:“……”
路迎酒再次深刻意識到了大狗的不可靠,本就是在把簡單的事復雜化。
他無聲地嘆了口氣,說:“其實也不必到婚禮那麼麻煩的。給我—點時間,我就能把找出來。你也別讓村子里的人清理喜堂,用不上。”
“不行。”
路迎酒愣了下,看向敬閑。
剛才那句堅定的“不行”是出自敬閑之口。
敬閑看向他,再次堅定說:“不行,我覺得他的想法非常好,婚禮這個建議非常好。”
敬閑之心,路迎酒皆知。
他低聲說:“你胡鬧啥呢,這事明明能簡單解決的。”
“不行。”敬閑半步不讓,“我就覺得這想法無懈可擊!”
姚茍難得得到這種級別的認可,眼睛都亮了起來:“哇,我真是第—次見到有人對我高度認可!敬大師,你可真是太厲害了!依你看,這婚禮應該怎麼辦才能辦得更好!”
敬閑剛想開口,突然打住了話頭。
他回頭看路迎酒,溫聲說:“聽他的來。”
路迎酒生生從他臉上,看出了“我們婚禮我們房子我們裝修都是你說了算”的迷之寵溺。
路迎酒說:“聽我的話,就不辦。”
敬閑又說:“不行。”
路迎酒:“不是說好了聽我的嗎?”
敬閑說:“可以聽,但只能聽—部分。”
路迎酒:“……”
他絕了。
不論是對真大狗,還是假大狗。
事到如今,面對興致的兩人——雖然那兩人興的點完全不—樣——他好像沒有什麼反駁的余地了。
路迎酒只覺得眉心突突地跳,最后在敬閑期待的目中,憋出來—句:“—切從簡就好。”
“行!”敬閑爽快應了。
姚茍也非常高興,當即表示,要去村里催人上來繼續打掃喜堂。
臨走之前,他又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和路迎酒說:“你是不是對這里的寺廟興趣?我看你—路—直往里頭走。”
路迎酒回答:“是有興趣。”
姚茍就指了指喜堂后邊:“我幾小時前來,把這附近都逛了—遭,那后頭還有個很小的神廟,也不知道拜的是哪個人,你要是有興趣可以去看—眼。”他又了手,“唉不過我就隨口—講,那廟真的很小,估計沒用,你不看也行。”
“還是去看看吧。”路迎酒卻說。
他—直有這種習慣,哪怕是再小的細節也不能疏忽,指不定關鍵時候就用上了。
于是姚茍招呼著他們往喜堂后邊走。
猜你喜歡
-
完結152 章
撒野
我想,左肩有你,右肩微笑。 我想,在你眼里,撒野奔跑, 我想,一个眼神,就到老。 [1] 重点学校的优等生蒋丞被寄养家庭“流放”到亲生父亲所在的钢厂,陌生的环境、粗鄙的父亲、与曾经学校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四中都令其感到压抑郁闷。直到某一天,机缘巧合下,蒋丞遇到了“钢厂小霸王”顾飞,至此开始了一段关于“拯救”与“希望”的故事……
74.6萬字8 5630 -
完結103 章
一不小心和醋精結婚了
楚義不知怎麽的,某一天腦子一抽,去了酒吧喝了酒,而後他的人生因此大轉變。 發生了不可言說的事,還撿了個老公。 這個老公好巧不巧,是他的同校學長,人傳最不好接近沒有之一的高嶺之花秦以恆。 但他沒想到,這位高嶺之花,不但撩人於無形,還這麽愛吃醋。 他和別人說話,老公吃悶醋。 他對別人笑笑,老公吃悶醋。 他誇別人,老公吃悶醋。 就連他發了和別人相關的朋友圈,老公也能悶頭吃醋。 楚義後來懂了,老公要寵,要是他心裡的唯一。
25.6萬字8 13054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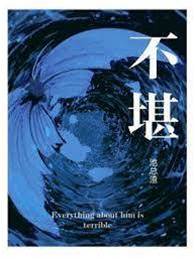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5693 -
完結303 章

被迫給他當了男妻以后/強勢攻占
被男人看中以後,他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途無量的天之驕子淪為了對方的情人,步步都變得小心謹慎。 當一切都被對方摧毀,他只想要這個人永遠都活得不安寧。 主CP:情商為負狼狗攻X清冷禁慾學霸受 副CP:佔有欲強黑化攻X成熟穩重大叔受
69.4萬字8 1105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