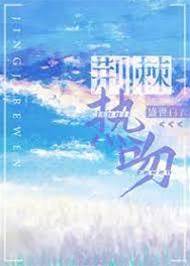《他與愛同罪》 第十三章
傅征上不上船,陪不陪都不是自己能夠決定的。
整艘驅逐艦,特戰隊只有他們一支,他們需要完的任務往往是技兵做不到的,這就需要把他們的力量放在刀尖上使,務必一擊即中。
傅征答應不了,也不能答應。
燕綏也明白這個道理,話一出口就后悔了,只是收回也來不及了。
電話鈴再響起來的時候,沒再猶豫,拎起話筒。
——
里弗坐在船長室里,腳踩著就綁在控制臺邊上的船長后背,指尖夾了煙,沒幾口,那煙灰全抖落在船長的上,把他的格子襯衫燙出了一個個黑邊翻卷的破。
等聽到那端明顯醞釀后發出的聲,他把煙湊到滿是胡渣的邊,吸了一口:“現在能過來談事了嗎?”
他的語氣相當平靜,就像是無風無雨天氣下的海灣,海水只能泛起小浪花。
燕綏做好了巖石會被海浪兜頭澆淋的惡劣設想,事到臨頭卻只是被海水了腳趾,和就近的邵建安換了個眼,換了種懷政策:“可以,避免到時候發生誤會影響合作,我過去前有幾件事想和你再確認一下。”
里弗毫不意外這個人會得寸進尺地提出條件。
他低頭看了眼蜷著子努力一團的船長,點了點煙管,已經燃燒了大半將落不落的煙灰瞬間撲簌簌落下,煙灰里暗藏的火星濺落,燙得船長悶哼一聲,開始掙扎。
幾秒長鏡頭的寂靜,就在燕綏默認里弗的沉默是默許時,聽到聽筒那邊輕微的鞋底用力地板的聲音,約還有重的呼吸聲,忽近忽遠。
眉頭漸漸蹙起。
應急小組負責題板提示的翻譯還在不停的提醒要讓里弗應允的幾個條件,反復提示無果后,拿著題板靠近,手扯了扯燕綏的袖。
Advertisement
不料,這一下就像是點燃了引信,燕綏嚯地站起,抬手撳下題板。
所有人,都被燕綏突如其來的反應嚇了一跳,紛紛停下手頭的工作,抬眼向看去。
燕綏在聽到里弗特意折磨船長令他發出時就被引了,來來回回在電話線的允許長度踱步數次后,到底沒忍住,怒喝:“不是讓你老實點不要傷害人質嗎?”
幾乎忘了原定的磨泡計劃,火氣噌噌噌地往上竄,僅有的一點理智讓自把語言切換了中文:“人渣。”
里弗聽不懂,但猜燕綏的語氣應該是在罵他,不僅沒生氣,反而愉快地笑起來:“你再耍花招我就不止拿煙頭燙他了,聽你的船員說,這位老船長為你工作了幾十年,也不知道后半生能不能好好養老。”
燕綏冷哼了一聲,沒激,但也沒有了剛接電話時的好臉:“贖金前,我需要親眼確認二十二名船員的安全。”
里弗笑了聲,爽快地答應:“可以。”
“我要帶一位公證人上船。”的語氣完全沒有商量的余地,直接省了和里弗涉的口舌:“男的,高……”
燕綏轉頭目測了一下傅征的高:“一米八五。”
正在指揮室待命的胡橋,瞄了眼傅征復雜的臉,心里嘀咕:“估了……”隊長要不高興的。
大概是沒見過燕綏這種臨場發揮型的,整個指揮室的氣氛都有點低迷。
關鍵時刻,連邵建安也不由自主地放輕了呼吸,等著里弗的回答。
預料之中的,里弗拒絕。
燕綏一點挫敗也沒有:“高太有迫的話我可以挑個……”
的目在胡橋上溜達了一圈:“一米七的。”
胡橋:“……”等等,他有這麼矮?
Advertisement
里弗大怒。
他脾氣本就不好,燕綏這種挑白菜湊合的口吻顯然刺激到他了,但眼看著就要收贖金了,他不好真讓人質缺胳膊缺,抑著,只能起,拎著凳子,一手砸向船長室的玻璃。
再厚重的玻璃,都被里弗用盡全力的一砸砸得蛛裂。
燕綏被那聲音刺激得頭皮發麻,蜷了蜷手指,用力地用指甲摳住手心:“我不會帶任何武,如果你撤離時需要,我愿意跟你走。”
燕綏激進要求下的退步,出乎所有人意料,這不在任何預案中。
原定計劃在一步驟,二步驟連續失利的假設下,盡數在里弗撤離上。
里弗收了贖金,會母船接應。
他不傻,軍艦就在幾海里外,他肯定也做好了收完贖金被狙擊的打算,不帶上人質想安全撤離?那是做夢。
燕綏猜想,里弗一定會帶上船長,等撤離到安全的海域再釋放人質。
燕安號的老船長,在燕戩在任期就為燕氏集團工作,數十年,長途遠洋,跑了不知道多趟的船。
記得,這是老船長最后一趟出船。
——
邵建安皺眉,不贊同地看了燕綏一眼。
但很快,里弗答應了的條件,電話掛斷,談判順利得出乎意料。
之前寫了整整一頁紙的各種應答方案都沒有用上……
用手背了有些發汗的手背,深吸了一口氣做足了心里建設,才敢轉。
等待中的批評并沒有到來,邵建安雖然覺得燕綏的決定不夠理智,但這種況下,戰備時間都是著用的,他本不會用來浪費。
整個指揮室立刻恢復了剛才的忙碌,一道道指令吩咐下去,所有人都和陀螺一樣,忙得團團轉。
反而燕綏這個要登船的人……閑著沒事干。
喝了一會水,又起來活了下手腳,盡管早已經把燕安號的船結構記得清清楚楚,為求心安,又仔仔細細地默背了一遍。
直到這會,邵建安才顧得上,親自到跟前重復了一遍注意事項。
生怕又臨場發揮,橫眉豎目地要求道:“等會聽指令,別橫干。”
燕綏連連點頭。
“等會路黃昏陪你上船,”邵建安下聲音,給講道理:“傅征太顯眼,路黃昏單兵作戰能力也很強,更能好好保護你。”
燕綏干笑了聲,和邵建安換了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其實他和邵建安都知道,無論是誰,只要一上船就會被限制行能力。不管路黃昏打不打眼,里弗都不可能放任一個有作戰能力的軍人跟在邊,那是對里弗最大的威脅。
但選擇路黃昏,邵建安的確是有考慮的。
傅征隊里的人,隨便拉出來一個,單兵作戰能力都以一敵十,路黃昏上船對燕綏而言,的確是一個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
下午四點,一切安排就緒。
日漸漸偏黃,海上起了風,風吹得桅桿輕響,一直跟船的海鷗仍舊盤旋著,始終不離軍艦左右。
傅征在指揮室隔壁的船艙找到倚窗而的燕綏時,正準備去洗手間再洗把臉。
迎頭撞上要進來的傅征,燕綏怔了一下,問:“找誰?”
“找你。”
傅征提了提手上的防彈:“這個穿上。”
燕綏寵若驚,但手上作麻利,下外套隨手掛在一旁,接過他手里的防彈。結果低估了這家伙的重量,燕綏的手一墜,險些沒拎住。
傅征及時收了力,垂眸看了一眼,示意手:“套上。”
他那一眼,目沉靜,莫名的就把燕綏有些浮的心穩住了。
抬起手,看著他俯替收防彈的結扣。他低著眉眼,臉部線條和,被躍進船艙的夕暖化,明明還是那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姿態,燕綏愣是到了他難得的溫和。
傅征替穿好防彈,退后一步端詳了兩眼:“轉。”
燕綏依言轉背對著他。
下一秒,燕綏覺他靠近自己,近到幾乎著。然后角被掀起,一柄槍,槍冰涼,斜進的腰。
燕綏下意識想低頭去看,手剛扶上腰,傅征低頭,近到幾乎著的耳畔,低聲道:“別。”
燕綏僵住了。
“上船會搜,”傅征放下的角蓋住槍:“上去后找機會。”
找什麼機會,他不說燕綏也知道。
手里要是真的沒點防的東西,基本任人宰割。
——
槍悄悄遞了,話也說完了,傅征退后兩步,轉離開。
剛走到門口,被燕綏住,難得嚴肅正經地了他一聲“首長”。
傅征停住腳步。
墨的作戰服把他姿襯得格外修長拔,他在夕的余中轉,無聲的用眼神詢問:還有什麼事。
偏斜了一些,燕綏有一瞬間看不真切傅征的臉。
到腰間被他別上的那把槍,槍托上蹭掉漆的和從司機那買的那把槍一模一樣,應是傅征去找辛芽要來的。
抿了抿,似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忘記多久前了,我在南部軍區見過你。”
朗譽林到軍區視察順便看戰友,正逢也在南部,就捎上了一條小尾。
那是秋末冬初了,窩在窗臺下的靠椅上倒時差,太曬,兜臉罩了件外套。外套從臉上下來的時候,一抬眼,就看到了負手立在外公旁的年輕男人。
不知道在聊什麼,他角掛著淡淡的笑,眼里的卻清而疏淺,不浮不躁。連窗外那支海棠,都沒能過他的。
“登船后才兇險,”醞釀著,逆著,笑容依舊清晰明:“所以有些話得提前說清楚。”
傅征隨時能抬就走,聞言,按著槍袋的手落下來,好整以暇地等著聽要說什麼。
不負他所,燕綏很誠懇:“對你的冒犯,純屬鬼迷心竅。”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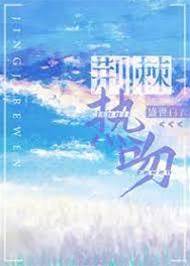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29720 -
完結74 章

沉浮你懷中
[1] 被迫學游泳的那個夏天,談聽瑟見到了父親為她找來的“老師”。 “你就是小瑟?” 聞名商界、閱歷深沉的男人此時渾身濕漉漉的,目光像幽然池水,令她目眩神迷。 他給她高壓生活中片刻喘.息的自由,給了她人生中缺失的在意與關愛,那場芭蕾匯演的觀眾席里他是唯一為她而來的人。 談聽瑟的木偶式人生中忽然燃起叛逆的勇氣,她青澀地學著引誘,故意換下保守泳衣穿上比基尼出現在他面前。 終于那次酒后,他們有了一晚。 “你父親知不知道你做了什麼。”他站在床邊,明明笑著,目光卻冷靜而陌生,“我有未婚妻,你現在準備扮演什麼角色?” 這個男人從不是什麼慈善家,利益至上的商人骨子里是冷血,為了一份人情,對她的好只是冷眼旁觀的偽裝。 [2] 一句氣話而已,陸聞別以為沒必要解釋,直到得知她遭遇了游輪事故,失蹤后生死未卜。 幾年后一支水下芭蕾的視頻爆紅,陸聞別和無數人一起看著大廈LED屏將這支視頻循環播放。 視頻里的舞者,正是令他執念了兩年多、又死而復生的人。 她與嚴家少爺在宴會上言辭親昵,面對他時卻冷冷道:“陸聞別,我們別再見了。” 陸聞別以為自己能做到再也不見。 然而談聽瑟落水的那一刻,他想也不想就跟著跳下去將她救起。 原本光鮮倨傲的男人渾身濕透地半跪在她身側,眼眶被種種情緒染紅。 “你和他什麼關系?” 她微笑,“玩玩而已。” “玩?”他手指顫抖,“我陪你玩。” “抱歉,陸先生。”她濕漉漉的腳踩在他胸口上,將他推開,“我對你這種老男人沒興趣。” 夏日滾燙,她曾沉浮在他懷中。 原來他這些年的人生,還不如她掀起的一小朵浪花有滋味。 【男主說的氣話,沒未婚妻|年齡差十歲】
26.6萬字8 7362 -
完結1738 章

閃婚嬌妻:老公,深深愛
新婚夜。她被逼進了浴缸里,哭著求饒,“顧靖澤,你說過不我們是假結婚的。”他狠狠逼近,“但是是真領證了!”第二天.“顧靖澤,我還要看書。”“你看你的,我保證不耽誤你。”要不是一時心灰意冷,林澈也不會一不小心嫁給了這個看似冷若冰霜,其實卻熱情無比的男人……
304.1萬字8 74278 -
完結1105 章

重生之國民男神
【本文女扮男裝,重生虐渣,酸爽無比寵文+爽文無虐,雙強雙潔一對一,歡迎跳坑!】前生司凰被至親控制陷害,貴為連冠影帝,卻死無葬身之地。意外重生,再回起點,獲得古怪傳承。司凰摸著下巴想:這真是極好的,此生必要有債還債,有仇報仇。*重臨娛樂王座,明裡她是女性眼裡的第一男神;執掌黑暗勢力,暗中她是幕後主導一切的黑手。一語定股市,她是商人眼裡的神秘小財神;一拳敵眾手,她是軍隊漢子眼裡的小霸王。嗯……更是某人眼裡的寶貝疙瘩。然而有一天,當世人知道這貨是個女人時……全民沸騰!*面對群涌而至的狂蜂浪蝶,某男冷笑一聲:爺護了這麼久的媳婦兒,誰敢搶?「報告首長,李家公子要求司少陪吃飯。」「查封他家酒店。」「報告首長,司少和王家的小太子打起來了。」「跟軍醫說一聲,讓他『特別關照』病人。」「啊?可是司少沒事啊。」「就是『關照』王家的。」「……」*許多年後,小包子指著電視里被國民評選出來的最想抱的男人和女人的結果,一臉糾結的看著身邊的男人。某男慈父臉:「小寶貝,怎麼了?」包子對手指,糾結半天才問:「你到底是爸爸,還是媽媽?」某男瞬間黑臉:「當然是爸爸!」小包子認真:「可是他們都說爸爸才是男神,是男神娶了你!」某男:「……」*敬請期待,二水傾力所作現代寵文,劇情為主(肯定有感情戲),保證質量!請多支持!*本文架空,未免麻煩,請勿過度考據!謝謝大家!
221.2萬字8 10214 -
完結498 章

寵妻100式:爹地放開我媽咪
她舍不得,卻要繼續掙扎:“你都是有孩子的人了,為什麼還揪著我不放?”“因為,我愛你?”他抱得更加用力了。她心中一軟,但還是不愿意就范,”你孩子他媽怎麼辦?“”你來做孩子他媽。”他有點不耐煩了,就在她還要說話的瞬間,吻上了她的唇。“你要我做后媽?”
85萬字8 476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