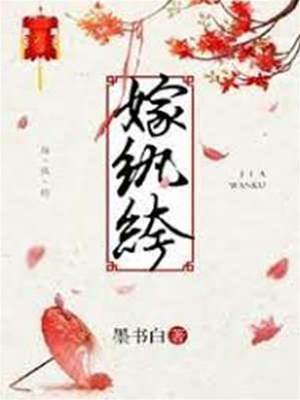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將軍帳里有糖》 第63章 親緣已斷
不認得爹爹媽媽、祖母祖父, 倒記得同胞的二哥,這事兒可真稀奇。
甘霈跟個猴子似的,原地跳著腳直擺手:“哎, 我不搶你蟈蟈兒,多大的人了,二哥背你下來!”
哪知道妹妹更來勁兒兒,撒了歡似的哇哇的哭,“我不相信你, 你把手爪子收回去!”
甘霈急眼了, 還沒來得及解釋,側面上緩緩移過來一個人,鐵青著臉, 一雙鷹眸盯死了甘霈。
甘霈嚇的一個哆嗦,仰頭給妹妹做了個噓的手勢,收聲,只是一切已然來不及,父親甘瓊那雙為百姓扛過泥袋子的大手,啪的一聲落在了甘霈的頭臉上, 把他掄了個魂飛魄散。
“十七八的人了,一點兒正事兒不干, 除了會欺負妹妹還會做什麼?給我滾回去讀書!”
父親甘瓊罵完了還不解氣,又沖他腰側踹了一腳,這才消了氣,回往馬車上一手, 笑容重新回到了臉上——只是常年嚴肅的人,乍一笑開來,落在旁人眼里頭, 跟見了鬼似的。
“來,雪團兒,爹爹背你。”
那馬車上的哭聲兒急促地收住了,再看妹妹的臉上,除了一雙略略紅腫的大眼睛,哪里還能看出來哭的痕跡?甘霈氣的在下頭跳腳,指著妹妹氣急敗壞,“爹爹,娘親,您看妹妹,還沖我吐舌頭吶!”
雪團兒沖著爹爹笑眼彎彎,俯在了爹爹的背上。
爹爹的脊背寬厚,負著小小的孩兒,一步一步走的深穩,沒來由的,雪團兒鼻頭一酸,悄悄抹了下眼淚,小聲兒跟爹爹道了聲謝,小聲地嘀咕了一句,“怪道兒老想著認個干爹,原來是悄悄地想您了。”
負著雪團兒的高大軀略頓了一頓,腳步繼續,“瞎鬧,一個閨還不夠爹爹疼的,旁人還想來分?看我弄不死他。”
Advertisement
定國公府的朱漆大門緩緩大開,一座琉璃制的鶴紋影壁赫然而現,再穿過兩側載著海棠和芭蕉的松木游廊,晨自那游廊上頭的枝葉散落,將這一行人照進融融的影里。
后是娘親、祖母祖父同兩位哥哥,再往后是隊的仆婦,雪團兒在爹爹的背上,環顧著周遭的環境,只覺得記憶深的畫面席卷而來,海棠濃郁的香,芭蕉清冽的氣味,游廊隔幾步掛著的燈籠,有著燭火熄滅過后的淡淡的香……
雪團兒拍拍爹爹的肩,“放我下來放我下來。”
甘瓊聞聲,將兒小心翼翼地放下來,就見自己這個小兒獵豹一般地沖了出去,往第一進闊大的院落沖過去。
二哥甘霈嗷嗚一聲,“爹娘,雪團兒又不干好事兒!”
南夫人一個掌掄過去,甘霈捂著臉一臉的痛苦和委屈,“我是咱們家唯一一個讀書人,仔細腦袋給我打壞了,咱們家就徹底了一人窩!”
看娘親還要上手打,甘霈再也不敢吭聲,抱著頭跟在雪團兒后面一溜煙地沖過去了。
南夫人領著后頭一串兒仆婦丫鬟,也跟著過去,剛進那院落,就見雪團兒邁著,在那墻角數青磚,左邊走八步,右邊走八步,到那一個栽著睡蓮的大黑缸下,把缸下的泥土使勁兒拉拉,掀起一塊青磚,里頭埋著一個小攢盒。
雪團兒也不嫌手上沾了泥,在臉上抹了一抹,抱著攢盒剛想打開,忽然警惕地看了一眼在一旁虎視眈眈的二哥。
二哥氣的手直抖,“看我做什麼,什麼好東西,也配我來搶……”話雖這麼說,眼睛還是被盒子裝的事給吸引住了。
里頭裝了一桿象牙雕葡萄筆,一只汝窯的荷花青蛙筆洗,還有一只小小的子母貓筆架。
Advertisement
甘霈嗷嗚一聲起來,指著那盒子,抖著手指,“……原來是你給我藏了起來!”
元宵節頭一天,祖父賞了甘霈這一套筆,第二天早上就找不見了,時隔七年,終于破案,原來是被妹妹給藏了起來。
雪團兒笑嘻嘻把筆往二哥手里頭一丟,再去敲小墻,敲著敲著就又從犄角旮旯的地方,找出了許多小玩意兒,土里埋著裝琉璃珠子的盒,磚里藏著小風車,便是連海棠樹下,都埋著一串兒金羊拐……
有些積年的老仆婦便抹著眼淚,在后頭說著話兒。
“……這些小玩意兒,也只有姑娘能找出來……”
“說是不記得人了,可小玩意兒都能記起來……”
雪團兒抱著一堆小玩意兒,抱在懷里頭,本來是笑嘻嘻的,可笑著笑著就哭起來,“臭哥哥,若不是你老搶我玩的,我何至于把這些玩意兒都藏起來……”
這句話一落下來,甘霈就一個后退,遠離了自家娘親蠢蠢的魔爪。
他期期艾艾地走到妹妹邊兒,蹲下來拍拍妹妹茸茸的腦袋,“……那你上哪兒去了啊,七年了,一到過年娘就揍我,一直揍到正月十五……你上哪兒去了啊妹妹,二哥想死你了啊,你不在,我替你扛了多揍啊!二哥太可憐了啊!”
說著一把摟住了妹妹的腦袋,兄妹兩個抱頭痛哭,南夫人在一旁默默地拭淚,上前摟住了這兩兄妹。
說起來,那時候甘霈同雪團兒年紀相差不大,從小一起招貓逗狗一同長大,府里頭誰都沒他倆親厚,雪團兒六歲時,甘霈正式去前院兒上學,倆人還生離死別了一番,兄妹自是好到不像話。
一切塵埃落定,定國公府里喜氣洋洋,南夫人自帶雪團兒拾掇,那一廂老定國公甘崧通知親眷,便擇了一黃道吉日大擺宴席,為雪團兒接風。
雪團兒丟了之后,定國公府對外只宣稱,雪團兒去了滇南的滇王府外祖家,可帝京這些高門里,仍有許多人家心里頭也有點兒影子,這一回定國公府大擺宴席,用的名頭仍是國公府嫡長孫由滇南回來了。
定國公喜氣洋洋,可武定侯府卻愁云慘淡。
武定侯辛士安年約四十,可形頎秀,長相俊朗不凡,年輕時有帝京雙玉的名,此時正負著手匆匆穿過游廊,往自家兒子的院子而去。
一旁的長隨亦步亦趨,急促地向侯爺回稟著。
“……世子爺這傷,夏大醫瞧過了,說差半寸就到心口,極為兇險,這一回高熱不退,則是因著傷口崩裂開,流不止。大醫還說了,大約是到了極大的沖擊,世子爺心有氣郁結,怕是命攸關。”
長隨看了一眼眉頭鎖的侯爺,又帶了點小心翼翼,“聽跟著回來的陳校尉說,世子爺是為救一位姑娘才的傷,侯夫人……長公主殿下覺著這一位姑娘鉤住了世子爺的魂,前去教訓這位姑娘……其中不知道怎麼的,又牽扯進了定國公府早年丟掉的大姑娘,小的聽了個糊涂,也不是很明白。”
辛士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剛想追上去,卻見房門使勁兒被推開,兒子蒼白著面龐踉蹌而出,往外奔去。
后竇云急促地跟了上去,陳誠看著二人離去的方向,急匆匆地向辛士安行禮問安:“侯爺,將軍他知道長公主殿下進了宮,這便藥也不吃沖了出去,卑職這便要跟上去,您見諒。”
辛士安捶頓足,急道:“備馬遞牌子進宮!”
重階金頂、皇城巍峨,西六宮的太后寢宮壽春宮里,長公主陳爰坐在下首,正向著寶座上的母后祝太后細細地說著話,沒一時便有監高聲唱道:“圣上駕臨。”
長公主忙起下拜,自家兄長建德帝徉徉而來,見妹妹坐在那,親切地問了一句:“妹妹今日怎麼得空進宮了?母后這些時日還念叨著你。”
建德帝快近五十了,有些老邁的樣子,倒是能看得出來年輕時的風貌,他在上首坐下,帶了一疲倦的笑意,“你生的好兒子,為朕一掃邊關,把胡人退了兩千里,這是不世的奇功啊!他這些年立的功勞太多,朕一時竟不知如何再封賞他了。”
長公主面上掛著顯而易見的意得,兒子出息,這個做娘的也揚眉吐氣,在母親和兄長心里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家天下家天下,我兒為大庸打仗,效忠的是自家舅舅,自是比旁人更忠心些。”吹了一下茶盞上的熱氣,輕抿茶。
“說起來有一樁奇事兒,才將妹妹才同母后說過,長星帳下右玉軍力倒出了一個扮男裝的人,這本就是死罪不說,此人在軍中更是貪生怕死,臨陣逃,日日同那些兵卒們混跡一,那場面實在是有礙觀瞻……”
建德帝好荒,本就不是個賢良之主,此時聽了兩句便有些不耐煩了。
“你既說了,一定是忍不下了。憑你做主,宮監頒我的旨意,賜死。”
長公主得了這樣的旨意,自然是滿意了,便也不往下說了,正同兄長、母后說著話,便聽外頭有一聲回稟:“上柱國大將軍辛長星持天子之令,在宮外覲見。”
長公主心一驚,有些不好的預浮上心頭,見太后已然笑著說:“快宣,本宮的好外孫來了,得好好賞賜他才是。”
見建德帝頷首,那監便往外宣了旨意,不多時,殿外清明的日籠著一個形頎秀的青年,緩步而來。
辛長星面清俊,卻蒼白,他此時仍是高熱不退,兩頰至耳后都掛著些許的緋,他沉默不語,步履深穩,先是向三位尊長跪拜問安,起之后并不落座,語音清朗溫潤。
“陛下,母親口中所說扮男裝之人,并非貪生怕死之人,不僅勤于練,還因為捉拿細升任小旗一職,在土剌城一戰中,還立了戰功。”他朗朗而言,并不去看上首的母親。
建德帝果然來了興趣,看了看長公主,又看了看自家這個外甥,“不過一個小兵,竟惹得你違逆母親,朕倒有些好奇了,是什麼樣的子?”
長公主的手指牢牢抓了椅座,氣涌如山,剛想駁斥兒子,卻在一剎間,撞上兒子的眼神。
那眼神悲涼,像是失頂無法言喻,長公主一霎兒手腳冰涼,刺骨的寒氣涌上心頭。
辛長星緩緩地搖了搖頭,先向著自己母親道:“母親,不能如您愿了。”
他再度看向老邁的天子,接下來的話擲地有聲。
“陛下,臣愿以八萬朔方軍的軍權,換此命無憂。”
天子心頭一震,不敢置信地看向了辛長星。
長公主一句“不”險些便要口而出,殘存的理智讓閉了,心頭一片冰涼。
同吳王易的籌碼,便是辛長星八萬的朔方軍軍權,如今兒子輕飄飄一句話,就要將軍權上繳,這豈不是將放在火上炙烤?
死死地抓住了椅圈,抖著雙手。
好像自己這一步做錯了……不過是一個微末子,即便是定國公府丟了的那個姑娘又怎樣?何至于用八萬的軍權去換?兒子豈不是瘋了?
天子冷靜地看了辛長星一眼,想起了太子的諫言。
“上柱國大將軍此番立下不世戰功,民間聲勢浩大,民心所向,皇父切記兵高蓋主,起謀逆之心。”
天子面上擺上了慈的笑容,頷首。
“娘親舅大,你為舅舅分憂,舅舅又豈能不諒你的難?不過是一位子,既是你心,朕赦無罪便是。”他笑言,“你在外征戰已久,也該休息休息,朕邊的殿前司還無人可用,你先來舅舅邊清福。”
辛長星默然領命,向著天子和太后告,大踏步出了壽春宮。
良久,后傳來母親急促的聲音,帶著憤怒和不甘。
“不孝子!八萬軍權豈能說扔便扔?你是豬油蒙了心?”怒吼著,在自家兒子的后拉扯著他的手臂,“大事者怎能耽于私,你可真母親瞧不起!”
辛長星頓住了腳步,將母親的手臂拂開,星眸凌厲。
“大事者?”他重復了母親的這句話,“母親想什麼大事?效竇太主?做皇帝?”
“母親封地食邑不菲,父親每年供給公主府萬兩白銀,您是短了吃穿還是缺了銀錢,要去收吳王販鹽販鐵的巨額賄賂?您無實權無軍權,吳王因何要孝敬與你?”
“如今母親牽扯其中,泥足深陷,兒子如今已被歸為吳王一黨,這一切是拜您所賜。”
上一世,他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會被太子針對,最終援兵不至,死牙狼關,這一世終于明了,這一切的源頭,在自己的母親上。
長公主駭然,被兒子的盛怒駭住,“你在胡說什麼?”
辛長星長舒一口氣,緩緩而言。
“定國公效忠正統,被吳王認作太子一黨,因兒子同雪團兒定下親事,吳王深恐兒子被定國公府拉攏過去,使人略賣了雪團兒,您知曉此事,卻袖手旁觀任憑一個流落在外,您也是為人母,將心比心,若是妹妹被人如此算計,您的心不痛麼?”
他的眼眸里狠戾,怒火熊熊,近了自己的母親。
“這些且不論,兒子至之人,您卻百般折辱,您的孩子是人,旁人的孩子也是人,何至于要如此做派?此事過后,您竟然還不悔改,妄圖蒙騙天子,賜雪團兒死罪,您的心是什麼做的?”
長公主萬沒料到兒子竟然查清楚了這一切,是個倨傲之人,絕不認為自己錯了,此時仍強道:“我這一切全是為了你!我是你的母親,還能害你不!”
辛長星靜默,眼中的狠戾倏忽而收,有些絕的垂下了眼眸。
“……兒子曾做過一場長夢。”他的聲氣兒和緩,淡淡道,“在夢里,兒子被圍牙狼關,太子留中軍不發,援軍遲遲不來,兒子中數箭而亡,全骨沒有一是完整的。”
他將自己的襟扯開,如玉的上赫然而現道道傷痕,日煊赫,將這些傷痕照的清晰,看在長公主眼里,只覺得心驚跳。
“您口口聲聲為了兒子,可惜到最后害的卻是兒子。”他看著自己的母親,神淡漠而疏離。
“兒子深知我朝以孝治天下,可您的品行和行事兒子實在無法認同,從今往后,我與您親緣已斷,還請珍重。”
長公主面慌,眼淚終于落了下來,與生俱來的倨傲讓忍不住咒罵起來,“你敢!你是我十月懷胎生下來的,竟敢為了一個賤人忤逆為娘!”
到這個時候了,還不知自己錯在何,辛長星到了極致的失。
長公主抓住了兒子的手,可得到的不過是輕蔑一眼,兒子甩手而去。
辛長星甩手而去?卻在背轉的那一刻淚流滿面,說不來是委屈和難過,他大踏步而去,后只余下母親捶頓足咒罵的聲音。
淚水迷蒙中,看到宮門前一個清頎的影,那樣慈的眼神就那樣悲憫地看著他。
辛長星再也忍不住,這些時日的委屈和難過涌上心頭,一個箭步沖了過去,在父親的前跪了下來,像個孩子一樣地啜泣起來。
“父親……”
辛士安扶起了兒子,中起伏,眼淚落在他的手臂,他點頭讓兒子安心,沉重而又心痛,“孩子,一切有父親在。”
作者有話要說: 有的小問題要征求小仙們的意見,以后行文是用“青陸”還是“雪團兒”呢?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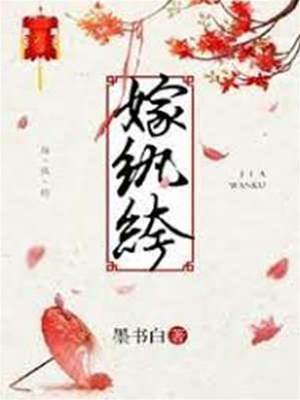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506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398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0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