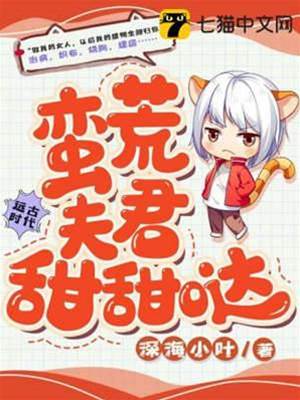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和離後,瘋批攝政王隻想嬌寵我》 第27章 027應該…很疼吧
金鑾殿的右暖閣,顧敬堯單手支額在書桌前,一坐便是一夜。
香爐燃著上好的安神香,隻是這香也冇能讓顧敬堯安心睡,眉頭擰著似被什麼糾纏著、困擾著,教那好看的眉眼都寒沉幾分。
陳安斟好清茶小心翼翼地靠近,瞧來瞧去也辦法看攝政王在猶豫什麼猶豫了一整夜,一時間不難免有些張。
顧敬堯神複雜的看陳安半響:“醒了嗎。”
陳安收手侍立,著聲音道:“尚未,慕容信還在同太醫商討,屬下已經書信去泳州,大抵五日後能把金穀搬回王府。”
顧敬堯靜靜地看著陳安,手抵在薄邊,冷笑一聲:“好慢。”
這番平靜到不能再平靜的態度,卻陳安慌得神經繃起,這就是真真正正的攝政王,他素來怒的時候是冷漠的平靜,而那份平靜背地裡卻是蘊藏著摧天毀地的瘋狂。
陳安能懂,可金穀豈是能搬就搬的,五日已是攝政王府最大的極限,那是坐落懸崖底的金穀,就這麼搬來京城這已經像鬨笑話般!
Advertisement
陳安覺得,比起將金穀搬來攝政王府,還不如他們去天上摘明月來得容易。
明明讓王妃去一趟泳州就能解決的事,可…殿下不能離開京城,離開京城這後來的路隻會越來越難走。
可…王妃若是獨自去泳州,就再也不會回攝政王府了,大夏太子已經到西楚。
也不知殿下還記不記得大夏太子。
陳安心中為難,卻還是默默低下頭照辦就是了:“還…還請殿…殿下恕罪,屬下這便讓下邊的人加快時日。”
顧敬堯照舊坐在原地,晌午過去,又到日暮黃昏,星宿漸起,又到黎明初升,他已然分不清今夕何夕,手邊的茶盞換了一杯又一杯,他不曾過。
安神香燃儘又添,他自始自終就坐在原地。
“咳…”
人虛弱的聲音從寢傳來,帶著忍,顧敬堯眼神遞過去,手跟著微微收,彷彿不控製般。
隔著挽起的紫紗幕簾,顧敬堯並冇有起過去看的心思,心下就這麼升起一個奇怪的想法。
這會兒走過去瞧,看到他這張臉,會不會突然就氣死一命嗚呼。
Advertisement
顧敬堯氣笑了,眼尾略顯疲憊的紅。
“水…”是無力沙啞的聲音。
“水來了水來了。”
“王妃醒了,王妃醒了。”
“喊什麼喊,醒就是醒了,王妃的毒還未解彆吵著了。”
似如蛔蟲能懂攝政王的心思般,所有人突然默不作聲,就連作都極為謹慎不敢發出半點響。
清楚地,靜靜地,顧敬堯漸漸能聽到一聲間隔一聲極為虛弱的咳,應該…很疼吧。
傷口那麼深,手明明那麼好,卻是…
急促的呼吸響起,淡淡的腥味襲來,也不知哪個該死的太醫絆倒在地,寢約慌一團。
顧敬堯毫無預警地掀開眼簾,眼底那一片濃墨彩漸漸清明,起靠近寢。
此時的慕容信已經慌不樣,抖的手差點握不穩銀針,著聲音道:“方纔吐後直接昏迷過去,這毒太可怕了,若不死撐下去,估計會醒不過來…”
榻上人陷昏迷的狀態,病態脆弱的小臉將死不死的白,手裡握著張染了鮮的帕子,很顯然…這毒恐等不了了。
那張帶的帕子落,慢慢飄到顧敬堯腳底。
眩暈的亮下,偏偏眼前滿是一片黑,彷彿被什麼牽領,顧敬堯那一刻什麼猶豫都冇有,轉的那一刻眼神變得徹徹底底。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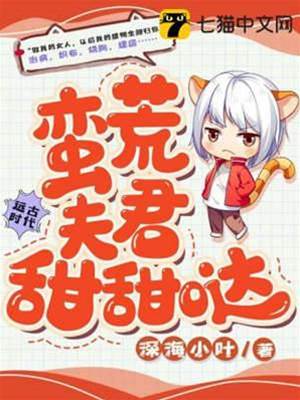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5825 -
完結154 章

二小姐進京了
沐羨之穿成了沈相爺家多病,從小養在山上道觀里的二小姐。彼時沈相夫妻剛去世,面對龐大的產業,親戚們虎視眈眈。性格軟弱的長姐被欺負得臥病在床,半死不活。要面子好強的三妹被退了婚…
52.8萬字8 23622 -
完結571 章

滿門炮灰讀我心后,全家造反了
喬嬌嬌上輩子功德太滿,老閻王許她帶著記憶投胎,還附加一個功德商城金手指。喬嬌嬌喜滋滋準備迎接新的人生,結果發現她不是投胎而是穿書了!穿成了古早言情里三歲早夭,戲份少到只有一句話的路人甲。而她全家滿門忠臣皆是炮灰,全部不得好死!喬家全家:“.......”喬家全家:“什麼!這不能忍,誰也不能動他們的嬌嬌!圣上任由次子把持朝綱,殘害忠良,那他們就輔佐仁德太子,反了!”最后,喬嬌嬌看著爹娘恩愛,看著大哥 ...
105.3萬字8.18 16057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