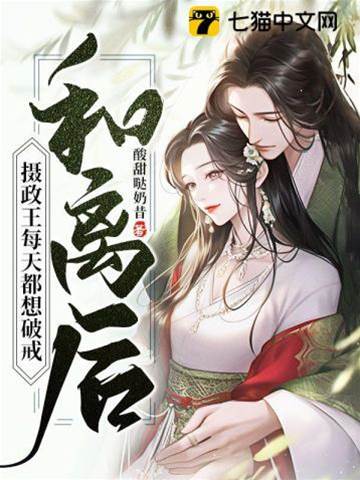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深宮繚亂》 第103章 大雪(3)
宮里接人的事兒,好像都不得董福祥出馬。皇后才大婚, 發話把人討進宮來不合適, 便由太皇太后下懿旨, 由董福祥承辦, 上承恩公府接人。
承恩公的那位福晉,真是個見的刺兒頭,就是宮里去人, 也敢板。到底姑娘在手里沒過過好日子, 也怕姑登了高枝兒,將來回過頭找的麻煩, 其實問問這位繼福晉的心, 是斷斷不愿意出姑娘的。
董福祥到了門上, 說清了來由,起先還賠笑:“給福晉請安啦。奴才奉老佛爺的命, 來府上接殊蘭姑娘, 進宮玩兒幾天去。”
營房福晉那雙鷹隼般凌厲的眼睛在他面上轉了一圈, “奉老佛爺的命?你是哪個值上的,我怎麼從來沒見過你?”
董福祥心里暗暗嘿了聲,面上還是一團和氣的模樣, 垂手說:“奴才算哪塊名牌上的人, 不過慣常給老佛爺跑跑兒,福晉自然沒見過奴才。”
這位營房福晉, 原是中下等人家出, 祖上出過一位武狀元, 那也是好幾輩兒前的事了,論出排不上名號,但因頗有,且是個沒許過人家的老姑娘,因此被承恩公捧寶貝似的捧回了家。營房福晉心地不好,見識也不高,似乎不知道宰相門前七品的道理,對這個玻璃頂子的沒什麼好氣兒。聽那口吻,一副要拐騙他家姑的意思。董福祥抹了把臉,心說晦氣,換了別的人家,二話不說先封元寶利市要,這開門紅。這位倒好,別說銀子了,干脆堵著門兒不讓進去。外頭風雪連天的,他在門外凍出了一皮疙瘩,腳趾頭在靴子里要結冰,都快沒了知覺了,恐怕今兒跑這趟,回頭得生凍瘡。
Advertisement
營房福晉還在窮琢磨,那水淋淋的大眼睛帶著三分疑,七分不耐煩,“好好的,老佛爺怎麼想起我們家姑娘來了?”
董福祥道:“福晉不知道嗎,您家公爺是孝慈昭皇后的哥哥,您家姑娘是當今萬歲爺的表妹。老佛爺有了年紀,記掛親戚,這不,打發奴才來,接殊蘭姑娘進宮說說梯己話兒。”
正是這說說梯己話兒,才營房福晉萬分戒備。多禍端是一來一往閑聊里頭生出來的,覺得宮里人是吃飽了撐的,孝慈昭皇后都死了十七八年了,這會子記掛什麼勞什子親戚。抱著,歪著頭,哼笑了聲道:“一表三千里,萬歲爺心江山社稷還心不過來呢,沒曾想咱們姑娘倒有這造化。”
話說到這份上,再攔著也不了,只得放下胳膊讓出了道兒。只不過好話還是沒有的,“諳達,您給個示下,老佛爺接我們姑娘進宮,是不是心抬舉?”
董福祥喲了聲,“福晉這就難為奴才了,上頭的事兒,奴才怎麼能知道!不過依奴才之見,也就是進宮敘敘話,過兩天還讓姑娘回府的。”
營房福晉嗤鼻一笑,“上回孝慧皇后殯天,繼皇后不也是接進宮去玩兒兩天,敘敘話的嗎。”
董福祥頓覺服了這糊涂婆娘,孝慧皇后那回是大喪,這回是大喜,能一樣嗎?就這號人,四六不懂,天只知道使壞,虧當了這些年的福晉,眼皮子淺得跟肚臍眼兒似的。
他呵呵干笑著:“說起這個,上回也是我接的皇后主子進宮,納公爺家別提多客氣。”
營房福晉一哂,“那是齊家有心攀高枝兒,納辛是個結頭兒,咱們家可不一樣。姑娘沒名沒分的,進宮干什麼?阿瑪才給說了門兒親,這會子進去倒不好。要不就勞諳達替咱們回個話,就說謝謝老佛爺厚,咱們姑娘說話兒要出門子,進不得宮了,請老佛爺見諒。”
Advertisement
這下子董福祥臉上不是了,誰讓他不了差事,就等于殺了他爸爸。他搐著一邊角,壞相全做在了面兒上,不不道:“福晉,這是太皇太后懿旨,懿旨您知道嗎,你以為是街坊和您打商量吶?公爺是個大肚彌勒佛,看來沒好好教您規矩,您接了懿旨要下跪磕頭口稱‘謝太皇太后恩典’,您可好,這會子還腰站著呢,這是藐視老佛爺,要抄家問斬的,您知道嗎?”
營房福晉被他這麼一說,嚇了一跳,別的不在乎,唯有這兩件,掉腦袋排第一,抄家排第二。原本是想著,要是上傳口信兒,太皇太后對人能不能進宮應該沒有執念。沒有執念最好置,三言兩語糊弄過去,殊蘭就用不著進宮了。結果沒想,這個辦差的不好相與,還是一口咬定了要帶人走,這就讓福晉到很苦惱了。
怎麼辦呢,有錢能使鬼推磨。想了想,即刻打發人取銀子來,然后把銀子捧在自己懷里,漾著笑臉說:“咱們家有難,諳達不知道。我是這麼個想頭兒,倘或宮里真要晉位,我霸攬著不放是我的不是;可要是接進去玩兒兩天,來回倒騰多麻煩,不如不去,您說是不是?”
董福祥的視線落在了手里的銀包兒上,其實多銀子他都見過,但他就是不服氣,這位福晉的利市,他是非拿不可。
“那依著福晉,怎麼料理才好呢?”他靦臉笑,“今兒公爺在家,您要是問了他就知道了,早前孝慈昭皇后還在的時候,公爺進宮會親,都是奴才引進宮門的,咱們也算老相識……福晉有心里話,不妨和奴才說說,奴才要是能幫上忙的,愿意為福晉分憂。”
營房福晉笑得愈發和了,“諳達真是個知心的人兒,我也沒有旁的意思,就是想請諳達上太皇太后跟前言幾句,別我們姑娘進宮了。我上不好,還指著姑娘伺候呢,一走,我這兒就轉不過彎兒來了。”
董福祥涼涼笑了兩聲,這東西,心肝是煤做的吧?公府里頭下人都死絕了,要個金枝玉葉的大小姐端屎把尿不?太監是窮人窩兒里出來的,窮兇極惡的不是沒見過,但歸結底都是應在一個窮字上。像這號人家,公爺領著皇糧,吃穿不愁,還這麼憋著壞地兌人,連面子都不要了,可見福晉這劣是長在骨頭上的,不死改不了了。
“話不是不能替福晉傳到,不過……”他說了半截兒,小眼神鉤子似的,頗有深意地瞧著那銀包兒笑。
營房福晉會意了,既然能買出這句話來,可見事不難辦。太監這號人,到底不見兔子不撒鷹,便把小包袱擱到了董福祥的手里,“如今家道艱難,這麼點子小錢兒,給諳達買酒喝。老佛爺跟前,還請諳達周全,回頭我我們老爺子專程答謝您,不?”
董福祥掂著那銀包兒,太監的手就是桿秤,只要一過手,就能約出分量來。十兩的銀錠子五個,那就是五十兩,雖不算多,推兩局牌九也夠了,遂笑道:“那還有什麼說的,不過一句話的事兒。不過奴才來了這半天,還沒見著正主兒。福晉把殊蘭姑娘請出來,奴才看姑娘一眼,回去好給老佛爺回話兒。”
那是小事一樁,營房福晉很爽快地打發底下人,“去,把姐兒請出來。”
很快那位皇表妹就出來了,好的姑娘,穿了件樫鳥藍的夾袍,梳著利落的大辮子。只是瘦,又瘦又蒼白,就顯得眼睛出奇的大。看人是怯生生的,多可憐,好好的公府小姐,弄得像個丫鬟,這窮旗營里出來的娘們兒,真個夠千刀萬剮的。
董福祥是銀子也到手了,人也見著了,對這福晉也沒什麼好客氣的了。他上前去,呵著腰說:“給姑娘道吉祥。奴才是宮里來的,奉了老佛爺懿旨,來接姑娘上宮里玩兒去,姑娘說說,倒是想去不想去?”
殊蘭因前兩天那丹朱和說過這事兒,翻來覆去想過無數遍,橫豎在這個家是沒有出頭之日了,不如進宮去,還有個奔頭兒。于是答得斬釘截鐵:“諳達,我去。”
營房福晉立刻橫眉立眼,“父母在,有你做主的份兒嗎?”
董福祥喲了聲,說不好意思的,“既然姑娘自個兒說去,那奴才也沒轍了。這麼的吧,福晉托我的事兒,我不能不辦,姑娘跟著走,在宮門上候著,要是老佛爺發話回去,那就把姑娘給您送回來,您看這樣不?”
“什麼?”營房福晉打鳴似的一聲高呼,“您別和我耍里格兒楞,打量誰是傻子?”
董福祥再也不聽的了,揮手讓底下聽差的太監把人帶出去。營房福晉在后頭大喊大,“干什麼,搶人不是?”沖邊上侍立的呵斥,“你們都是死的,人都欺負到頭上來了,你們還看熱鬧吶?”
這一罵醍醐灌頂,所有小廝和戈什哈都躁起來。可是沒等他們起哄,董福祥回手指著郭福晉的面門,高聲道:“都別!我是奉了太皇太后和皇上的旨意,你們誰敢,我這就上九門找提督去,一氣兒平了你們信不信?”
這句話一出,倒震住了那些人,董福祥的那手指頭像火銃似的,指哪兒哪兒就矮下去半截。他錯牙冷笑,“了不得,今兒長見識了,我還沒見過這麼沒王法的人家呢,連宮里的旨意都敢不遵。福晉您別急,才剛您的話,回頭奴才一點兒不給您傳到,咱不能平白拿您銀子不是!”說罷一笑,邁著鶴步往門上去了。
郭福晉他唬住了,愣了半天沒出聲兒,等馬車一走才回過神來,站在院兒里拍哭喊:“哎喲,這個斷子絕孫的殺才,騙了我的銀子,還把我們家姑搶跑啦……”
誰還聽的呢,馬車在大道上碾冰前行,進了神武門。到順貞門前勒馬下車,董福祥上引路,笑著說:“姑娘有年頭兒沒進宮了吧?奴才上回見您,還是先頭福晉治喪那回,這一晃都五六年景啦。”
“噯。”殊蘭笑了笑,笑容里有苦的味道。
這宮廷,說悉也悉,說陌生也陌生。早前母親帶著進來,小孩兒家,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一門心思只知道玩兒。如今不一樣了,沒人帶著,什麼都得靠自己,每行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邁錯,丟了阿瑪和哥哥的臉面。要是細數,母親生病臥床后就沒再進過宮,實打實地算,應該有八年沒來過這地方了。八年啊,多麼漫長,好些東西都變了,站在慈寧宮直長的甬道上,有種是人非的覺。宮人默默上來引路,垂著頭邁進了門檻,這里個個都是主子,連抬眼的膽子都沒有。
跪下去,趴在栽絨毯上以頭搶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南炕上的太皇太后說伊立吧,仔細瞧瞧姑娘的臉,扭頭對太后道:“還小那陣兒常進來的,那時候是個圓臉兒,怎麼這會子臉這麼小?”
皇太后說:“大十八變麼……不過忒瘦了點兒。”
殊蘭有些難堪,著手絹無所適從。其實不宮里,外頭都是這樣,有份的公府人家打量起姑娘來,恨不得掰開看牙口。在宮里終究沒什麼依仗,皇太后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太皇太后呢,又是姑母的婆婆。姑母在還好說些,姑母不在,基本也沒什麼可指的了。要說近,倒不如皇帝和皇后來得近些,抬起眼,悄悄看了看,玫瑰椅里那一錦繡的年輕姑娘應當就是皇后。皇后生就一副和氣可親的長相,見了,心里倒稍稍安定了些。
嚶鳴調過視線問董福祥,“你上門接人,事還順遂嗎?”
這一問,打開了董福祥的話匣子,他把營房福晉的惡形惡狀添油加醋說了一回,最后道:“奴才有個同鄉,在承恩公府上當差,奴才登門前先找他打聽了,人家一提起這位福晉臉都綠了,說這主兒是踩著高蹺唱大戲,半截不是人啊。宮里主子仁慈,沒拿祭大刀,要是換了脾氣大點兒的,不收拾了倒奇了。”
太后聽完了直皺眉,“竟說咱們搶人?這人還知不知道個尺寸長短?”
太皇太后臉上淡淡的,偏過端起茶盞抿了一口,“原就是咱們手了人家的家務事兒,要細說,是咱們的不是。”語氣里大有不該摻合的意思。
殊蘭有些慌,惶然看了看皇后。嚶鳴明白的顧慮,這回是撕破了臉才從家里出來的,要是就這麼回去,那往后的日子愈發不能過了。
同樣的人,所的待遇有時候千差萬別。嚶鳴一早進宮那會兒,太皇太后表現出了極大的熱,不像這回,總有些意興闌珊的樣子。
其實里頭緣故并不復雜,那時候阿瑪是輔政大臣之一,哥哥又在吉林烏拉做昂邦章京。家里福晉娘家是大學士,自己生母一門都是武將,和眼前這位皇表妹有天壤之別。世上的人,幾個不長勢利眼?離權力越近,權衡利弊的嗅覺就越靈敏。
看來太皇太后是沒有要安排的意思了,太后又不問事,沒法子,嚶鳴只好自己攬下來,笑道:“橫豎進來了,就在宮里多住段日子吧。”一面對太皇太后道,“皇祖母這兩日忙于抄經,這件事就不勞煩皇祖母了。我把人領回去,一應由我來安排吧。”
太皇太后說也好,復聲道:“再聽聽那滿有什麼說頭兒吧,要是也和他那糊涂福晉穿一條子,那人就留不得,還是讓家去吧。”
嚶鳴道是,領著人回了坤寧宮。
殊蘭把這些年的委屈都和說了,臨了擼起袖子讓看,上頭星星點點陳年的傷疤,印在姑娘的皮兒上,有目驚心之。
“怎麼回事兒呀?”
殊蘭垂著眼說:“福晉小蘭花兒,奴才伺候的時候,火星子燙的。”
嚶鳴覺得難以想象,一個人的心腸能壞到什麼程度,才能干出這種事兒來。把的袖放下來,溫聲說:“萬歲爺念著小時候的兒,不忍心見你落難,特囑咐我看顧你。這會子既然進來了,把心放回肚子里吧,往后的事兒自有我替你做主。”
殊蘭一聽,忙跪地給磕頭,聲說:“謝萬歲爺和娘娘恩典,娘娘這份恩,奴才就是磨,也報答不盡。”
嚶鳴示意邊上宮人把攙扶起來,才要說話,過南窗見九龍肩輿到了宮門上,噯了聲,“萬歲爺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10 章

寡人有喜了
重生之前,青離的日常是吃喝玩樂打打殺殺順便賺點“小”錢,重生之后,青離的任務是勤政愛民興國安邦外加搞定霸道冷酷攝政王。情敵三千?當朝太后、嬌弱庶女、心機小白花?青離冷笑,寡人可是皇帝耶!…
71.6萬字8 24930 -
完結598 章
宮女奮斗日常
凌歡冰肌玉骨貌若天仙,卻無心權勢,一心想著出宮。最終母子二人皆不得善終。重來一次,她的目標是養好崽崽自己當太后。大女主宮斗文。女主心狠手辣智商在線。情節很爽。
87.7萬字8.18 59248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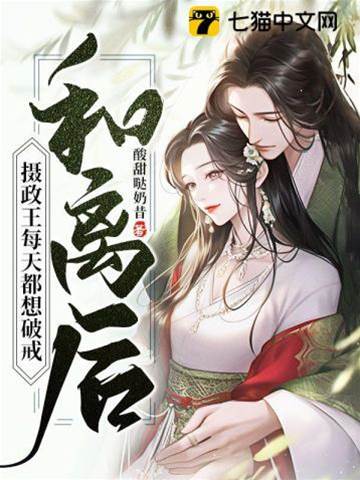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005 -
完結719 章

熾野纏情
【雙潔 花式撩夫 逗逼 甜寵爽文】沐雲姝剛穿越就是新婚夜與人私通被抓的修羅場,新郎還是瘋批戰神王爺容九思!救命!她捏著他橫在她脖子上的刀卑微求饒:“王爺,我醫術高明,貌美如花,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留我一命血賺不虧!”他:“你溫柔體貼?”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很兇殘!”容九思最初留沐雲姝一條狗命是閑著無聊看她作妖解悶,後麵發現,她的妖風一刮就能橫掃全京城,不但能解悶,還解饞,刺激的很!
126萬字8 42868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