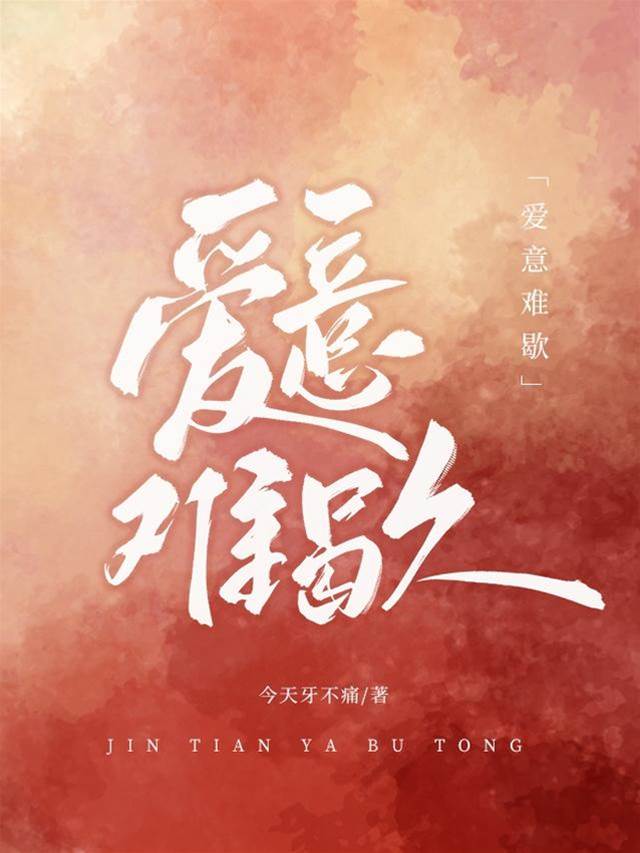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80章
這條巷子很淺, 還未前行多久,便來到拐角。
在寂靜無聲的巷道里,醇厚夜凝固有如實的黑氣, 水銀月灑在地面, 映出野草扶疏的影子。
四周的人家都熄了燈火,唯有一毫不起眼的破舊木屋亮著。
寧寧甫一上前, 便有微風拂過。木屋門前深黑的厚重紗帳被夜風揚起, 如同在半空起的一縷水波, 層層漣漪此起彼伏, 出紗帳里的幾分昏黃燭。
那就是紙條中提到的“簾帳之后”。
裴寂向來謹慎, 握著劍先行把簾帳掀開,等探確認安全無事,才把寧寧拉進黑帳中。
在來之前, 曾經設想過許許多多所謂“簾帳之后”的景象,然而此番親踏足此地,還是不由到了些許意外。
就裝潢來看,這里與貧民街區的其它房屋沒有太大差別。
仄陳舊、狹窄沉悶,黯淡燭填滿每個角落,與不愿散去的夜彼此勾纏, 放眼去盡是灰塵、裂痕與搖搖墜的蛛網, 潦倒得可以直接出道去拍鬼片。
一排排貨架雜地陳列其間,讓本就狹小的空間顯得更加邁不開腳。當寧寧細細看去, 能在貨架上見到凌擺放的符紙與典籍,還有許多從未見過的稀奇古怪的東西。
幾幅歪歪扭扭的畫被掛在墻邊, 寧寧好奇去,一眼就被其中一張吸引了注意力。
畫上是一無際的天空,輕而淡的穿過層層凝聚的云翳, 出紗幔般溫和的鵝黃澤。
畫作之下,赫然寫著幾個大字,一字一頓地念出來:“《纖凝破》——和宋纖凝的名字好像啊。”
“小店可不敢瓷那位夫人。二位想要點什麼?”
Advertisement
陌生男音突然響起,寧寧尋聲抬眸,在滿地散落的書冊里,發現了坐在書堆上的年輕男人。
雖然看出這是個商鋪,對店里的商品卻是一無所知,正要思考應該如何回答,就聽旁的裴寂道:“城主夫人來過這里?”
他真是毫不客套,開門見山。
青年聞言神一變,仍然保持著盤而坐的姿勢,脊背稍稍直了一些。
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卻已經生了大把白發與厚重眼袋,黑白相間的搭配上驚天地黑眼圈,往地上一坐,跟國寶了似的。
“城主夫人?”
男人打了個哈欠:“你說哪個城主夫人?”
寧寧一怔:“你的意思是……們兩個都來過?”
對方不說話了。
“要是說實話,我們自會給你報酬。”
想起自己可憐、每天都在一滴也不剩的邊緣瘋狂試探的錢袋,咬牙繼續道:“不知閣下能否一些報?”
“開玩笑,我是那種會因為錢財喪失原則的人嗎?客人的私必須完完整整保護好,這是我開店的信條!”
青年嘿嘿一笑:“但如果你們愿意多給點,也不是不——”
他話沒說完,就見到一束白茫茫的劍迎面而來,冷冽如冰,恰好劃過他幾縷垂落的發。
青年角一。
那個深夜進店的小姑娘和善又漂亮,語氣與神態都是溫溫,沒想到邊的年人像條瘋狗,拔了劍就是明晃晃地直接威脅,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惡匪打劫,把他嚇得夠嗆。
近日正值十方法會,這兩個隨帶劍的年輕人一看就是仙門小弟子,雖然都穿了黑,心里鐵定白得跟紙沒什麼兩樣。
他的本意是矜持客套一番,把報價位慢慢往上抬,好生糊弄糊弄這些不諳世事的名門正派,沒想到被對方當場來了個下馬威,劍氣又冷又兇,全然沒有一一毫正道的做派。
Advertisement
這是哪個宗門的徒弟?莫非……
腦海里緩緩浮現起某個門派的赫赫大名,青年不由得一陣哆嗦:“你們難道是,玄虛劍派的弟子?”
寧寧看出這位想要訛人,并未攔下裴寂,應聲笑著點頭:“對!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他哭無淚。
廢話啊。
除了玄虛劍派,沒有哪個宗門能把弟子的頭顱掛在船上飛,堪稱魔幻主義巔峰大作,不服不行。
這個恐怖門派早就鬧得滿城風雨,活生生了嚇小孩的鬼故事素材,今日真是三生積來的福分,讓他能與這兩位見上一面,果真名不虛傳。
論殘暴程度,玄虛劍派天下無敵。
裴寂對陌生人從來沒有太多好脾氣,更何況這店家擺明了歪心思,他握著劍面不改,把寧寧之前的話重復一遍:“兩位城主夫人都來過?”
“有話好好說!都來過,都來過!”
青年慌忙應道:“你們想打聽什麼?”
那姑娘還是笑意盈盈的模樣,眼見同伴拔了劍,居然毫沒有想要阻止的意思:“這家店有何特殊之?們都來做過什麼?”
他總算看出來了。
這兩人的心,是在同一個煤堆里滾過的。
“我這兒的貨,大多是咒和符篆。”
見寧寧出些許失的神,青年趕忙道:“這些符咒與名門正派的那一套可大有不同!我這鋪子里,最講究一個‘邪’字。”
邪。
寧寧眉目稍斂:“邪?”
“正是!”
青年從書堆里勉強直起子,語氣不自覺許多:“正道的心法,大多講究五行相生、因循有道,我的這些呢,嘿——跳出五行之外,怎麼有用怎麼來。”
修真界法眾多、派別林立,寧寧所接到的玄虛劍道,只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在了解的所有修行之道里,符可謂最是詭譎多變。
意在筆先、揮毫落紙,點橫折捺皆有講究,哪怕錯位分毫,都可能與本意判若天淵;而筆墨丹青、朱砂浸,繪制符咒所用原料不同,功效亦會大相徑庭。
“我看二位都是劍修,或許對咒不甚了解。”
青年很是客氣,沖著寧寧咧一笑:“邪法多與詛咒、制和魂魄相關,既能千里之外奪人命,也可將旁人煉可供控的傀儡,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
寧寧認真應道:“是邪乎。”
“還有更邪門的呢!”
男人來了興致:“我聽說啊,舊時魔族還有一種替命之,能以他人的氣運抵消己孽障,一旦功那便是瞞天過海,連天道都奈何不了你毫。不止這些——”
他講到一半察覺到裴寂不耐煩的視線,心知自己偏了題,有些尷尬地輕咳一聲:“言歸正傳啊,那位宋夫人來找我,是想問有關換魂的事兒。”
寧寧心口一,聽他繼續說:“那時與城主不太好,來我這兒時面灰白。可換魂乃是逆天改命的大忌,雖然古籍中有過記載……但我畢竟就是個小店老板,哪會曉得的法子,只能告訴莫能助。”
寧寧若有所思地應聲:“除了這個,還有沒有問過別的什麼?”
“是有點言又止的樣子,不過直到最后也沒問出來,離開這里沒過幾天,就突發重癥病倒了。”
青年眼珠子一轉,往前傾了些,把聲音低:“這還不是最離奇的——等宋纖凝死后不久,鸞娘尚未嫁給城主時,居然也在某日進了我的店里,詢問有沒有骨重塑、蘊養靈力的法子。”
他說著頓了頓,似是講得口干舌燥,端起旁茶杯猛地一灌:“你說奇怪不奇怪,我這家店向來行事收斂,很出風聲,來的多是達貴人,尋常百姓很能清底細。然而鸞娘自長在暖玉閣,連門都很出,是從哪里得到消息的?”
寧寧點點頭:“這‘骨重塑’——”
這幾個字顯然問到了點子上,青年忽地咧笑笑,俯把音量得更輕:“可不就是煉魂之!以他人的魂力滋養己,不但可以維持容不老,對修為提升也是大有裨益。”
他說罷森森笑了幾聲:“你們難道不覺得,跟近日來的失蹤案很是相近嗎?”
裴寂冷眼瞥他:“你覺得失蹤案與鸞娘有關。”
他用了十分篤定的陳述語氣,青年聽后也并不反駁,聳肩應道:“你們應該就是在查這件事兒吧?這只是我的一己之見,信不信。”
寧寧念及大師姐安危,并不與他廢話:“你是不是覺得……鸞娘很可能是已故的宋纖凝?”
“不然問起換魂是為了什麼?鸞娘又為何能找到這個地方?”
青年抬眼了門外,確定寂靜無人后繼續說:“而且我聽說,鸞娘與曾經的子大相徑庭,可不就是被徹徹底底換了個人嗎!”
許是從未有人與他談論過此事,青年越說越來勁:“要我說啊,事應該是這樣:宋纖凝對城主而不得,恰逢抱恙活不了多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氣之下用了移魂,附在鸞娘上。”
他又喝了口水:“鸞娘正是城主喜歡的長相,然而未修仙,總有容老去的一天,于是宋纖凝又用煉魂之法,試圖永駐容貌、修為進,讓城主越來越迷。”
這一番推理下來,倒也算是有理有據。
寧寧眼底的翳卻始終沒消,沉聲問他:“店家,你可聽說過《紫薇法錄》?”
“宋夫人買過一本,紫薇真人正是邪大能。”
青年似笑非笑:“至于那本書,里面恰好講到了換魂,只不過所談甚淺,沒有太大作用。”
對話進行到這里,似乎許多事豁然開朗,沒有了可以繼續聊下去的話題。
寧寧想起下落不明的鄭薇綺,蹙眉沉聲道:“那煉魂之,究竟應該如何作?”
“很簡單啊,無非是活人、咒法、布陣。”
青年睨一眼,像是想起什麼,再度出了略顯神的表:“煉魂十分有趣,同一時間獻祭的生魂越多,所能得到的回饋也就越大。相同數量的魂魄,一個接一個煉制的效果,遠遠比不上同時獻祭——或許那些失蹤的姑娘還沒死,幕后兇手在等一場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祭。”
這讓寧寧想起浮屠塔里的鵝城。
當年的邪修們也是將全城人的魂魄聚在一起,等待一并煉。如果真如店家所說,離奇消失的孩們尚在人世……
只要他們盡快查明真相,也許就能救下包括鄭薇綺在的所有人。
“二位聽盡興了沒?”
青年怯怯打量一番裴寂的神,抬起右手指了指旁的貨架:“看在我講了這麼久的份上,要不要買點東西?”
=====
玄虛劍派的弟子畢竟也不是惡魔,寧寧和和氣氣向店主道了謝,隨后又選了些或許有用的小玩意,才與裴寂一并離開店鋪。
因為之前那段稀里糊涂的牽手,兩人之間的氛圍一直極為微妙。
之前聽店主侃大山的時候還不覺得,然而這會兒四下靜謐,連自己的腳步與呼吸都能聽見,夜與微融在一起,就更顯出幾分曖昧的意思。
寧寧一邊往客棧方向走,一邊低著腦袋,試圖整理紛的思緒。
宋纖凝為什麼要詢問換魂之事?鸞娘大變,當真與有關聯嗎?以及,之前是真的真的主牽了裴寂的手吧?
最后一個念頭出現得猝不及防,讓腦海里的推測瞬間停滯下來。寧寧有些別扭地了左手指尖,似乎還能到年人手背堅實的,像在做夢一樣。
想不通,為什麼會下意識做出那種作,還有那句“這樣才是牽手”……
也太太太主了一點吧!
從這里去往玄虛派所在的客棧還有一段距離,寧寧為了避免氣氛越來越尷尬,著頭皮向裴寂搭話:“師弟,你怎麼想?”
心下張,這句話口而出,沒經過太多思考。沒想到裴寂并未立刻應答,而是沉默著扭過頭來看。
他很適合夜晚,漆黑的發被晚風吹拂到額前,遠幾顆遙遠點猶如星辰墜落,懸在一雙郁深邃的黑瞳,映出幾分明暗不定的暈,像深潭月影那樣幽幽散開。
寧寧被他這樣一看,心口便不自覺地發悶。
裴寂語氣冷、不容置喙,每個字都咬得格外清晰。雖然刻意裝作并不在意,卻又帶了點遲疑的意味,尾音像是貓咪下垂的尾,漸漸變低:“師姐以前都是我的名字。”
寧寧一哽。
哇,這個人!
牽了手之后開始學會得寸進尺了!可不是心里張,想借由這個稱呼讓自己顯得正經一些嗎!干嘛要這麼直白地說出來啊!稚!
寧寧踹飛面前的一顆石子,有些不服氣:“師弟不也是我‘師姐’嗎?”
把“師弟”兩個字念得格外重。
承影發出一聲幸災樂禍的大笑:“哈哈哈不是吧!裴小寂,你這算是撒嗎?居然被寧寧懟回來了哈哈哈太遜了吧!”
裴寂把頭轉了回去。
寧寧察覺他移開視線,便趁機抬起眼睫,不聲地瞧他一眼。
月讓裴寂棱角分明的廓稍顯和,從的角度看去時,能見到對方繃的下頜。纖長如羽的漆黑長睫垂落在他眼前,襯得目愈發晦暗不明。
看不裴寂此時此刻在想什麼,只知道他皺了眉頭。
然后裴寂微微張了口,似乎想要說些什麼,與此同時偏過腦袋,正好撞上寧寧清亮的目。
兩個人同時把視線挪開。
“我——”
寧寧聽見他低低出了聲,在短短一個字后戛然而止,隨即而來的是淺淺吸氣聲。
裴寂的嗓音像是從腔里悶悶地涌出來,雖然只是短短兩個字,卻被他念得格外生笨拙,每個音韻都在舌尖百轉千回,仿佛不舍得。
所幸他最后還是念了出來。
裴寂說:“寧寧。”
寧寧,得還好聽。
寧寧走在昏暗的小道上,不知怎地,忽然覺得腳步輕快了許多,連帶著一顆心臟也嘩啦啦飛起來,怎麼也抓不住。
“喔。”
抿了斂去邊的笑意,把雙手背在后邁步時,帶了點跳起來的沖,佯裝出一本正經的嚴肅口吻:“裴寂小朋友,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承影一邊捂著笑一邊說:“裴小寂,這是在說你稚。”
頓了頓,又嘿嘿嘿笑得更厲害:“你可不能認輸啊!聽我的,一聲‘寧寧乖寶’或‘寧寧小親親’,嘻嘻嘻嘻絕對不敢再調侃你了。男人就是要主一些,強勢一些嘛!”
若真那般出來,的確是不敢再調侃,他卻跟直接死掉沒兩樣了。
裴寂沉著臉,骨節分明的右手把劍握得更,雖然眼底多了幾縷不耐煩的殺氣,角繃一條直線,把上揚的弧度悄悄下。
原來的名字從自己口中念出來,會是這樣的覺。
單薄的疊音溫和又輕盈,僅僅是念出那個名字……
都會讓他張得心下一,卻也忍不住想要揚起角,開心到無法抑制。
他真是沒救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6 章

花嬌
舒筠一年前與淮陽王世子定親,人人艷羨,她小心翼翼守著這門婚事,兢兢業業討好未婚夫,只求保住婚事,給三房掙一點前程。舒家姑娘誰也不甘心潑天的富貴落在她頭上,一年一度的賞花宴上,堂姐設計與淮陽王世子有染,逼舒筠退婚,舒筠看著那肆意張狂摟著堂姐的未婚夫,眼眶一紅,轉身將定親信物扔至他手裡。她悶悶不樂躲去摘星閣喝酒,醉糊塗了,遇見一高大挺拔的男人,夜色裡,男人嶽峙淵渟,風華內斂,她看得入神,鬼使神差捉住他親了一口。當今聖上裴鉞乃太上皇么子,也是唯一的嫡皇子,太上皇退位後,裴鉞開疆拓土,革新吏治,文治武功有過之而無不及,太上皇帶著上頭幾個兒子醉生夢死,好不歡樂,唯一棘手之事,便是那皇帝年過二十七,至今未娶。滿朝文武與太上皇費盡心思哄著皇帝參加賞花宴,裴鉞去了,卻在摘星閣被個陌生的姑娘給輕薄了,他捏著女孩兒遺留下的手絹,將那無端的旖旎抑在眼底,算了。終於有一日宮宴,裴鉞瞧見那小姑娘眉目熾艷與人說笑,一貫沉湛的眼罕見掀起波瀾。相親對象臨川王世子,引著舒筠來到裴鉞跟前,“筠筠,這是我皇叔。”舒筠笑瞇瞇施禮,“給皇叔請安....”裴鉞捏著打算賜婚的聖旨,瞇起了眼。
20.4萬字8.17 25401 -
完結1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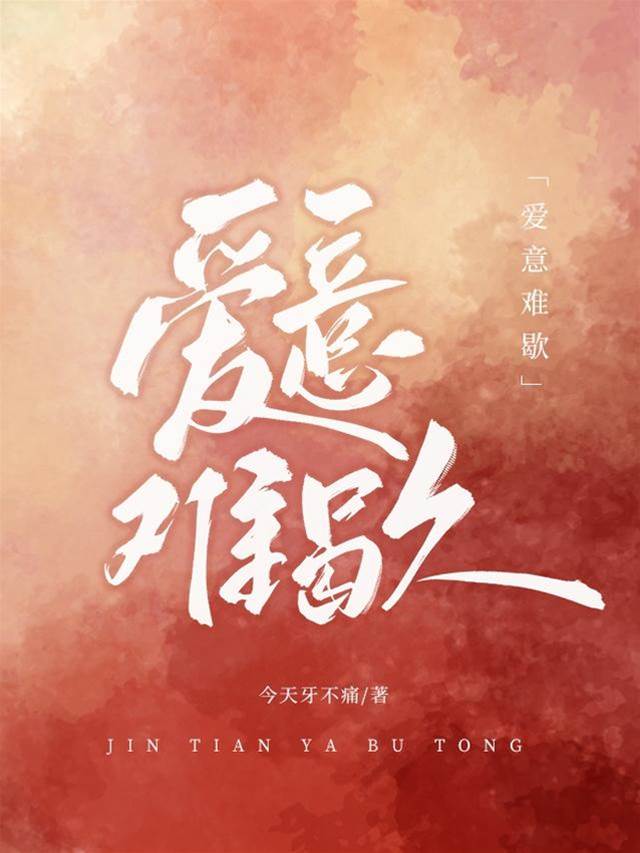
愛意難歇
【校園都市 | 男追女 | 久別重逢 破鏡重圓 | SC | HE】【清冷古典舞女神x京圈太子爺 】【冷顏係軟妹x瘋狗】八月,大一新生入校,一段舞蹈視頻迅速火遍了整個京大校園論壇——少女青絲如瀑,一襲白裙赤足立於地上,水袖舞動,曳曳飄飛,舞姿輕盈如蝴蝶蹁躚,美得不似真人。校花頭銜毫無意外落在了伏鳶頭上。但很快有人崩潰發帖:校花就一冰山美人,到底何方神聖才能入得了她眼?!大家不約而同用“樓聿”二字蓋樓。-樓聿,京大出了名的風雲人物,他生來耀眼,長得夠帥,又是頂級世家的豪門太子爺,無論在哪都是萬眾矚目的存在。但偏其性格冷恣淡漠,清心寡欲,因此又有人在帖下辯駁:冰與雪怎麼可能擦出火花?-後來無人不曉,兩人愛的轟烈注定要走到最後。然而誰也沒想到,戀愛未滿一年,伏鳶就提了分手。-多年後重逢看著女人平靜從他身邊走過,猶如不相識的陌生人,樓聿竭力抑製暴戾情緒。直到那句——“你認錯人了。”..聲音刺耳直穿心髒男人偽裝多年的平靜瞬間分崩離析,他猛地將女人抵在牆上,顫聲問:“伏鳶。”“耍我好玩嗎?”—愛意隨風起,鳶鳶,給你耍著玩,回來我身邊。
26.5萬字8 7996 -
完結91 章

偏偏他在等/春欲暗渡
【商務女翻譯&投資大佬|破鏡重圓|江城一場豪門商宴,賓客滿座,大佬雲集。林霧聲被上司勒令討好南城來的老總,拿下巨額投資。林霧聲舉著酒杯,望向主位矜貴冷漠的男人,怔愣到忘記說話。怎會是他?見她失態,有人調笑:“談總,小姑娘偷看你好幾眼了,你們認識?”男人靠在椅背上,睨著她,眼神淡漠:“不認識。”三個字,刺得她心口一凜。-誰也不知,多年前的春分夜裏,夜風慵懶,暗香浮動。她將談則序攔在暗巷,指尖勾起他一絲不茍的校服,笑說:“尖子生,談戀愛嗎?”他冷漠推開她:“沒興趣。”後來,依舊是那條小巷。風光霽月的談則序神色卑微,拉著她祈求:“可不可以不分手?”-宴會結束,談則序將她拽至角落,他語氣隱忍:“林小姐,這些年你過得安心?”-她和他達成協議關係,各取所需,銀貨兩訖。林霧聲越來越覺得自己掌握不了,想結束一切:“我不玩了。”那晚,本來禁欲清冷的他,將她抵在車裏發狠親吻,禁錮著她說:“你隻許跟我,沒得選。”-是她拉他入春潮,是她棄他於深淵。人不能兩次栽進同一條河,但名為林霧聲的河,他渡無可渡,自甘沉淪。-* 破鏡重圓、協議戀愛、追妻* 都市穿插部分校園回憶,校園時期女追男
19萬字8.18 193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