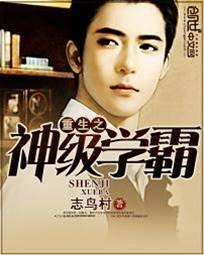《帝臺嬌》 第二十二章
原本熱熱鬧鬧的殿里頓時安靜得不像話,唐灼灼眼看著瓊元帝眼神越來越黯,心里又是著急又是頹然。
甚至都能想象得到等會皇太后臉上失的表。
言貴妃就坐在瓊元帝的下首,離皇后的位置僅有一步之遙,此刻姣好的面容上綴著點點的哀愁和張,溫和地出聲道:“皇上,太子孝心人,這塊帕子定有不一樣的含義,您先聽太子說說吧。”
實則心里也張,這看似蠢笨的法子實則最是湊效,當著這麼多大臣的面,瓊元帝再是喜霍裘,也不得要出言訓斥幾句。
而這幾句,對自己的皇兒而言,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至可以稍加息,不至于被得那麼。
這些人臣,莫不都是捧高踩低的東西,慣是會看皇帝的臉。
可若是被人揭,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就算是不被人發現,瓊元帝心里肯定也有計較,難免存下疑心的種子,帝王生疑可不好消除啊!
言貴妃稍稍了子,看著自己皇兒和劉氏臉上毫不掩飾的笑容,心里更是有些涼。
也不知道這樣做,到底是值還是不值啊!
果不其然,瓊元帝別有深意地過來,言貴妃心下忐忑,卻還是面不改回了一個溫和的笑。
“稟父皇,皇祖母大壽,普天同慶,兒臣欣喜之余也深惶恐,命人請了蘇州上好的繡娘,不分日夜趕了十幾日,才趕在皇祖母大壽時送上。”
霍裘聲線清冷,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神間既不見邀功的急切,也沒有被陷害的憤怒,除了那雙格外深幽些的眼瞳,整個人與平時無異。
唐灼灼驀的松了下,心頭著的一塊大石落地,只能瞧見霍裘高大拔的背影,卻能在心中勾勒出他如月清冷的面龐。
Advertisement
他既然這樣說了,自然能圓過去。
六皇子眼底瘋狂閃爍一陣,而后輕輕嗤笑出聲:“皇兄快別賣關子了,皇弟雖見識比不上皇兄,但還是沒聽過一塊小小的帕子要趕十幾日的。”
底下的大臣坐席里瞬間傳來一陣竊竊私語聲。
瓊元帝冷眼一,了:“老四,你說說。”
霍裘面不改,珍而重之地將那塊帕子展了開來,雪白的帕上針腳細,瞧著倒像是綢一般。
皇太后才瞧清了那上頭的幾個花樣,就直起了子,神有些恍惚。
霍啟見狀同言貴妃對視一眼,強下心底的不安,著自己聽霍裘繼續說下去。
“六弟有所不知,皇祖父所說的話,孤自然是要照做的。”
這話一出來,在座嘩然。
霍裘里的皇祖父就是先皇無疑了,這小小的一塊帕子,難不還涉及到了先皇?
“兒臣時,皇祖父常教兒臣騎,閑暇之余總與兒臣談起早年與皇祖母相遇的景。”
說到這里,霍裘抬起了頭,向眼眶泛紅的皇太后,緩聲道:“孫兒謹遵皇祖父訓言,在蘇州上好的雪帕上繡以裊裊生煙的古屋,潺潺山間清泉,青山綠水常伴。”
“在今日這樣的大好日子,希替皇祖父搏祖母一笑。”
太后邊的嬤嬤走到霍裘邊,端起那方帕子,呈到太后的桌案前。
瓊元帝瞇了瞇眼,又瞧了瞧面惶惶的老六,神莫辯地笑出聲:“老四這心思,倒是難得了。”
霍啟再也笑不出來了,聽著底下眾臣的嘖嘖稱贊,氣得心口泛疼,若不是言貴妃警告的目再三掃過來,他真想不管不顧地出聲質問。
就那麼一塊破布,隨他一張怎麼說,他怎麼就沒聽先皇多說過一句?
Advertisement
但他死死地忍住了,已經無需再問了,瞧了皇太后的神,一切都已經有了答案。
霍裘說的是真的。
可明明他的人已將這帕子換了一條普通的宮帕!
霍啟腦子里的憤怒焚燒了理智,覺得藏在袖子里的那條換下來的帕子了一個明晃晃的笑話。
事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個解釋。
霍裘早就察覺到了他的小作,然后聽之任之恍若未覺,就是為了等著他和母妃自個兒將臉湊上去被他狠狠隔空扇一掌。
他們不惜在帝王眼皮底下耍心機,卻得來了滿朝文武對霍裘的稱頌,太子之位依舊坐得穩穩當當,他們倒是不蝕把米!
比他更驚訝的是是唐灼灼,放在膝頭的雙手還在微微打,目卻凝在霍裘直如松的后背上,不得不贊嘆他的臨機應變。
這樣的死局都能全然,果然不愧是一代千古帝王,沉穩有余足智多謀,比霍啟之流強上太多了。
沒想過那麼多,只以為霍裘是看了那帕子臨場編的,且還正巧撞到皇太后的心坎上去了。
上頭太后拿著那帕子細細一陣,眼角泛了,對著一旁的瓊元帝道:“這是當年你父皇親自繪的圖,哀家以為他是說笑,竟不想是當了真。”
瓊元帝湊過去看了幾眼,也跟著笑:“父皇對母后的意,人人皆知。”
“這事,老四下了功夫,哀家十分歡喜。”
霍裘垂下眼瞼,幽深的眼瞳里泛出一子冰冷的寒氣,榮辱不驚地退到了自己的坐席上,直直地對上唐灼灼晶亮晶亮藏著星海的眸子。
真傻氣。
霍裘才坐下,就不聲地抿了一口杯中的酒,醇香綿長,搭在膝上的左手虎口泛出濃烈的黑紫,他皺了眉,又喝下一口酒下劇痛。
猝不及防一只細的小手過來,輕輕扯了扯他的袖口,霍裘面一,整個左手掌都已疼得麻木,他卻分明到那只手上的溫度,又甜又暖。
“殿下,您是不是早知曉了他們會在壽禮上手腳啊?”唐灼灼端著小巧的玉杯用寬大的袖口掩住了面容,小聲地問。
一陣鉆心的痛從虎口蔓延到整條手臂,霍裘面沉如水,瞥到在玉杯上小小的指骨,道:“嗯。”
唐灼灼驀的松了一口氣,他既然知道了,那自然是將計就計給霍啟和言貴妃迎頭一擊。
笑得瞇了瞇眼睛,才要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就被一只修長的手住了。
唐灼灼偏頭,男人面極冷,薄輕啟寒氣肆意:“你不能喝酒。”
唐灼灼一默,從善如流放下那小巧的酒杯,模樣乖巧。
“好,聽殿下的。”
霍裘手掌些微的抖,他沉沉閉了眸子,這時正到六皇子霍啟獻上自己的壽禮。
霍啟才從被霍裘玩弄的怒氣中掙出來,換上了得的笑,他對自己的壽禮分外得意,連帶著步子都輕快幾分。
言貴妃心底不安,幾乎維持不住臉上的笑意,晦地了一眼巋然不的霍裘,恨得咬牙。
隨之而來的又是深深的頹然。
的皇兒太過急功近利,若沒有自己指點一二,幾乎沒一件事不出錯。
到了這時,又怨起瓊元帝來,若是他一視同仁,將帝王之道也傳授給自己的六皇兒,他們娘兩何至于如此做派?
唐灼灼也不錯眼地盯著霍啟手里的東西,眼里閃過幾興味。
先前不知霍裘對此事知曉幾分,如今得到了他的準信,就越發的心想要看一場好戲。
依照霍裘錙銖必較冷厲風行的子,必然是以牙還牙回去了的。
霍啟將黑布一掀,出里頭的竹簡,淡淡的腥味彌漫開來。
唐灼灼皺眉,側瞧了霍裘一眼,才發現男人額上沁出點點汗珠,雙眸閉,旁人瞧著像是閉目養神的樣子,唐灼灼卻心尖一。
一時之間顧不得霍啟的壽禮,挪了挪子離霍裘近了些,刻意低了聲音問:“殿下可是子不舒服了?”
霍裘緩緩睜了眼,了有些僵的大拇指,道:“無事。”
唐灼灼垂下了眼眸,瞧著男人又閉了眸子,面上十足溫良,纖細的手卻大膽地掀了他膝上的,準地握住了那只寬大的手掌。
霍裘猛的睜開了眸子,里頭像是蘊著兩口無盡的深潭,他手掌使不上力,又不想被瞧見自己的狼狽,只好冷聲命令:“放手。”
唐灼灼這會倒是不怕他了,他些微的力道攥得手指泛白,就用另一只手將他冰冷的手指一掰開,料定了他舍不得對使力。
霍裘凝的臉蛋許久,旋即扯了扯角漠然一笑,那麼丑的東西,要看就讓去看。
左右也不過是更厭惡他幾分罷了。
唐灼灼將男人的手掌拉到的膝上,也不敢有太大的作,只借著余匆匆一瞥,便被自己瞧到的東西嚇到了。
一大片的紫黑如同一朵朵妖異的花,占據了他左手虎口到掌心的位置,且在以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深濃,最后定格在了深濃的黑上。
唐灼灼一張桃花面上的笑意層層瓦解,囁嚅幾下,卻說不出什麼話來。
眼眶有些發紅,好歹克制住了自己沒有當眾掉眼淚,只是臉上得的笑是再也維持不住了。
南疆蠱蟲。
霍裘他是怎麼被蠱蟲了的?疼這樣也不吭一聲,他到底是種蠱多久了?
唐灼灼心尖一,太多的疑問沒人解答,彎彎繞繞的梗在心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霍裘覺到纖細的手心上開始冒了汗,只以為是被嚇到了,手心的劇痛慢慢消弱,他了指尖,回了自己的手。
甚至不敢去看的眼神。
殿里霍啟的目帶著得意,將那竹簡層層鋪開,的小楷麻麻,淡淡的腥味混在殿里的馨香中。
猜你喜歡
-
完結2832 章

嫡女醫妃
前世,她是相府嫡長女,傾盡一切助夫君登上皇位,換來的卻是剖腹奪子被囚暴室! 隱忍三年,以死破局,大仇得報,含笑而終! 一睜眼,回到了她十三歲未嫁這一年。 嫡女歸來,這一世她絕不讓人輕她辱她賤她! 殺刁奴,滅庶妹,杖繼母,戮渣男,神來殺神,佛來殺佛! 她絕色容顏豔殺天下,無雙醫術令人俯首,卻不料惹上冰山鬼王! 鬼王兇煞孤星,權勢滔天,寵妻如命! 她狂妄一笑,既是如此,那便雙煞合璧,權掌天下!
262.8萬字7.65 1068965 -
完結1220 章
末世為王
出生在末世爆發百年後黑暗紀元的秦羽在一次狩獵中死亡,重生到了末世爆發的第一天。一場血雨降臨,死去的人重新站了起來,渴望著鮮美的血肉,生命物種發生變異,兇猛的變異獸肆虐,更有來自異空間的強大異族虎視眈眈。文明毀滅,道德崩喪,人類是否能在殘酷的末世中延續下去?是成為冷酷的惡魔還是仁慈的救世主?進化的極限是天堂還是地獄?這一世終將加冕為王!
234.1萬字8 133247 -
完結139 章

再婚[重生]
溫玖喜歡了賀蘭紹十年,為了他甚至不惜通過聯姻嫁給了他的哥哥賀蘭樞。 十年癡心錯付,真的救了自己的人卻被自己傷的體無完膚。 在項鏈中貼身呆在賀蘭樞身邊四年,看清楚了賀蘭紹的嘴臉和賀蘭樞的真心…… 若是一切能夠重來,多好。 直到睜開眼睛 時間回到他為了幫賀蘭紹而去主動找賀蘭樞復婚的那個雨天 溫玖(愧疚):阿樞,咱們…能復婚嗎 賀蘭樞(澀然笑):好。 內容標籤:重生 甜文 情有獨鍾 豪門世家 搜索關鍵字:主角:溫玖,賀蘭樞
55.3萬字8 10301 -
完結15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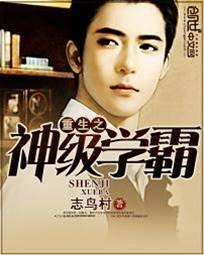
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畢業后失業,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同學們,跟我學…… 畢業分配很教條?來我屋裡我告訴你咋辦…… 國有恙,放學弟! 人有疾,放學妹! 這是一名不純潔的技術員的故事。 志鳥村公眾號:> 志鳥豚群:138068784 58563095
389萬字8 16462 -
連載66 章

雷雨交加夜:選擇繼續當孤兒
前世飽受家人嫌棄,最終年紀輕輕便意外死亡的明宇重生回到了那個雷雨交加的夜晚,他踡縮在門口聽著一聲聲炸雷以及屋內傳出的無情謾罵,回想起前世這一生的遭遇,對家人徹底絕望的他毅然選擇與這個血緣家庭決裂,從此繼續當孤兒……
12萬字8.18 27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