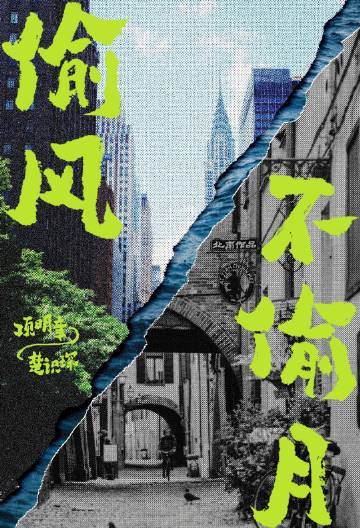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打死不離婚[ABO]》 [打死不離婚[ABO]] - 2
俞抒是很秀氣清冷的長相,除了一雙桃花眼以外,鼻尖上的一顆痣,笑起來之后整個人鋒利又不失和。
鏡子里的臉很悉,俞抒看著自己的臉,抬手了一下鼻尖上的痣。
這顆痣讓俞抒覺得后勁上的傷口又在作痛,還帶著些許麻,不手了一下才手穿服。
“他不喜歡你,還……。”齊舫看俞抒去傷口,忍不住著手不甘心的說:“他憑什麼?!”
俞抒換好服,對著鏡子里的人又看了一眼,努力讓自己出個笑,“齊舫,現在這樣好的。”
徐桓陵不會喜歡那個總不說話不笑的俞抒,鏡子里的笑恰到好。這樣的日子,多讓雙方留下點好的回憶。
外面有人敲門,齊舫走過去打開,換了一休閑裝的徐桓陵站在門外,沉聲說:“父親母親等著了。”
俞抒不敢看徐桓陵,低著頭回答:“就下去了。”
屋里信息素的味道很濃,徐桓陵皺了皺眉說:“戴上頸環。”
齊舫恨不得把徐桓陵的后背盯出個,等徐桓陵走了摔上門就開始抱怨:“裝遭雷劈,徐桓陵這裝得雷都劈不過來!”
俞抒對著鏡子戴上頸環,回頭對著齊舫笑了一下,勸他說:“你不要總因為我的原因針對他,你們家和徐家是世,還有很多生意上的來往。”
齊舫是齊家最寵的Omega,脾氣驕縱,兩人這麼多年的好朋友,在徐桓陵一事上他一直站在俞抒這邊,俞抒怕他和徐家鬧出矛盾影響兩家關系。
但俞抒知道自己勸不住他。
“我知道。”果然齊舫上答應著,依舊不停的抱怨:“徐桓陵有什麼好的,你偏偏要喜歡他。”
“好了,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以后我喜歡徐桓陵的事,你千萬別說出去,我不想別人知道。”俞抒走過去抱了他一下,拍拍他的背說:“你回房間去吧,別跟我下去了。”
Advertisement
徐家的人今天肯定要為難自己,等會兒要是齊舫看見,難免又要為自己出氣,俞抒不想他在徐家鬧事。
“真煩。”齊舫哼了一聲,又幫俞抒拉了下服,才不愿的回了自己的房間。
俞抒也在后面出了門,在門口深吸一口氣整理好心,心無旁騖的下了樓。
客廳已經坐了不人,徐桓陵的父親和繼母坐在主位上,都在等著俞抒。其他的親戚也都各自坐在旁邊,虎視眈眈的看著下樓的俞抒。
俞抒從桌子上端著放茶的托盤走過去,規規矩矩的跪在地上把茶遞過去:“父親,母親請用茶。”
“好。”徐琛點點頭,接過俞抒手上的茶喝了一口。
徐琛和徐桓陵長得很像,特別是眉眼間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只是整個人看上去比徐桓陵和不。
一旁的周琦半天沒有端茶,著手上的一個鉆戒漫不經心的教育俞抒:“俞抒啊,雖然徐家并不歡迎你,但你終歸已經了徐家的人,以后就要守規矩。哪有新婚第一天給父母敬茶就拖拖拉拉不下來的,這麼不尊敬長輩,也不知道你的教養在哪里。”
“就是。”旁邊不知道是誰跟著附和:“昨天典禮不見人,今早又故意拖拉,這俞家的Omega面子真是大。”
俞抒沒有回頭看,從聲音聽出來好像是徐桓陵的小姑,昨天見過一面,一見俞抒就一臉惡心的說:“除了是個Omega,一點兒用都沒有,好話也不會說兩句。”
俞抒當時只是平靜看著,氣得轉就走了,一邊走還一邊罵。
早就料到今天徐家的人會為難自己,俞抒也不說話,低頭安安靜靜的跪著。
徐桓陵就坐在徐琛旁邊,顯然也沒有幫俞抒解圍的意思,反倒幫著周琦教訓俞抒:“我昨晚不是說了記著今天要敬茶嗎?”
Advertisement
“對不起。”俞抒說。
“哥,我和你說了,別答應爺爺和俞抒結婚。”徐桓陵旁邊的徐安菱甩著看似無意的踢了俞抒一下:“他那麼不說話,整天也不和人相,難說有抑郁癥。”
“好了。”徐琛終于拿出一家之主的氣勢,拍著桌子說:“不說話沒人把你們當啞。”
“父親!”徐安菱不愿的扭著,又瞪了俞抒一眼。
徐琛也瞪了他一眼,繼續和俞抒說:“爺爺昨天睡得晚,今天不舒服就沒出來喝你的茶,讓你去他屋里說話,等你母親喝了茶,就去吧。”
“我知道了父親。”俞抒又把手里的茶舉高了點兒,周琦這才不愿的端起茶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回托盤。
俞抒站起來依舊低著頭轉,把托盤放回原位去了一樓拐角的房間。
俞抒剛進屋,徐琛就小聲呵斥客廳里坐的人:“早就說了,讓你們別針對他,如果他告狀,你們就自己去找父親解釋,別讓我去挨罵。”
周琦皺起眉,徐安菱又是不滿的哼了一聲,其他人也都一臉不屑。
徐桓陵倒是全然不在乎,只是皺眉看了徐琛一眼說:“不要刻意為難他,也不必寵著他,當他在這個家不存在就是。”
徐家本來就不屬于俞抒,徐桓陵覺得這樣對他已經足夠公平,畢竟俞抒心機那麼深,心里藏著些什麼惡毒想法誰也不知道。
徐琛對徐桓陵這個想法并不贊,看了他一眼說:“你和他保持好距離,不要因為他是個Omega就心。”
在徐琛心里,俞抒無異于徐之廉的人,對自己是個極大的威脅。
徐桓陵也不滿,看徐琛的臉就知道他在想什麼,皺眉說:“收收你對爺爺的心思,他既然已經把徐家到我手上,我就不會再讓你拿回去。”
徐琛被堵得半天說不出話,徐桓陵冷哼一聲,起來上了樓。
徐之廉不好,剛過五十就把家業給了徐琛,現在孫子當了家,他更是常年臥病在床,連昨天的典禮他都沒有出去見人。
俞抒敲了敲門,徐之廉在里面說進來,他才推開門走進去。
“爺爺。”俞抒笑了一下,在徐之廉床邊坐下。
“好孩子。”徐之廉手拉著俞抒的手讓他在床邊坐下,一臉的慈,“桓陵沒有為難你吧?”
“沒有,爺爺您放心,桓陵哥對我很好。”俞抒說得有些心虛。
剛剛才了為委屈,驟然聽見這樣關心的話,除了心虛,俞抒心里還到一陣酸。
徐家和俞家聯姻是徐之廉的意思,最后讓俞抒進門,也是徐之廉的意思。
在徐家,俞抒只和徐之廉說得上話,也只和他最投緣。俞抒明白徐之廉是真的疼自己,可俞抒卻只能說假話。
“沒有就好。”徐之廉安心的笑笑:“桓陵這孩子心是好的,就是從小慣,所以脾氣不好,固執又霸道,你多順著他點兒,他會喜歡你的。你子安靜,和桓陵應該會很合適,比你哥合適。”
俞抒聽到這話,又抖了一下,低著頭嗯了一聲。
這個世界上,或許只有這麼一個人,覺得俞抒比俞楚好。
“桓陵這孩子要喜歡上一樣東西很難,但是一旦喜歡上,就會視若珍寶,牢牢抓在手里。爺爺希有一天,你們能夠滿,和和睦睦的,這樣就算我立馬走了,也能安心了。”
可惜徐桓陵已經有視若珍寶的東西,就算順著他,也不一定會為他喜歡的東西。
俞抒把這些想法拋在腦后,耐心安徐之廉:“爺爺,您別這麼說,您會好起來的。”
“哈哈哈……。”徐之廉笑得岔了氣,俞抒趕手去幫他拍背,徐之廉擺擺手繼續說:“我看上的Omega,錯不了,你別管周琦的態度。”
俞抒笑了笑沒有回話,據徐之廉這句話,已經猜到周琦和徐安菱為什麼那麼不喜歡自己了。
想必徐桓陵的Omega,周琦是早就選好的,結果被自己中途了一腳,壞了人家的好事。
“我老了,管不了許多事。”徐之廉繼續說:“他們要是欺負你,你也不要一味忍讓,我知道你不是讓人隨意拿的人。”
被人看,俞抒又是討好的笑了一下,心里卻越發難過。
徐之廉看了很多東西,卻沒有看最本質的東西。
比如他不知道自己其實早就喜歡徐桓陵,所以俞抒只能笑。
徐之廉嘆氣瞪了他一眼:“去吧去吧,你們都有自己的小心思,我說不你了。”
“哪有。”俞抒說:“爺我知道您疼我,我會聽話的。”
徐之廉擺擺手,俞抒幫他蓋好被子讓他睡下,出去的時候客廳里只有徐安菱一個人在看電視,俞抒干脆直接上樓去找齊舫。
可齊舫的屋里已經沒了人,俞抒找了一圈不見人,準備回房間找手機給他打電話,結果一推開門就見徐桓陵坐在床上。
剛剛和徐之廉談話好不容易放松下來的心又被提了起來,俞抒站在門口就不敢了。
“找爺爺告狀告得還開心嗎?”徐桓陵抬頭看了一眼俞抒,把床頭柜上的一個相框拿到手上看著。
第3章 你殺了你哥
這個相框昨晚并沒有,應該是徐桓陵剛剛才帶過來的。
俞抒看不清相冊上是誰,只是莫名的察覺到一危機。
“怎麼不說話?”徐桓陵問。
一個人要是認定了你是什麼人,絕對不會輕易改變,俞抒也不想解釋自己并沒有告狀,關上門走過去,換了個話題問徐桓陵:“你找我有事嗎?”
“給你送樣東西。”徐桓陵把相冊放回床頭柜上:“眼嗎?”
俞抒跟著徐桓陵的手看向相框,照片上是一張悉的臉,可是俞抒一眼就看出來那不是自己。
猜你喜歡
-
完結331 章

嫁給前男友他舅舅
一場意外,周凌跟一個男人有了一份為期四年的交易,之后他帶著滿身的傷,揣著肚子的小包子離開。 一年后,為了養兒子,周凌是開店賣花又賣畫的,直到某個跟他兒子長的很像的男人找上門來。 “周先生,你租的這店面,現在歸我們集團開發管理。” 周凌是抱緊了兒子,氣的紅了眼睛,這個人他不是已經有愛人了嗎?怎麼還來為難他! “不過,你要是愿意做樊家的‘少夫人’,不僅這塊地是你的,你手里抱的孩子,還有孩子他爸,也是你的。” CP【腹黑邪氣霸道深情**攻樊塑丞X奶味可愛有點兒自卑周凌受】
92.4萬字8 43943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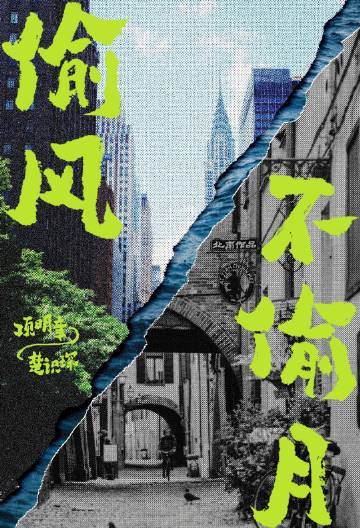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