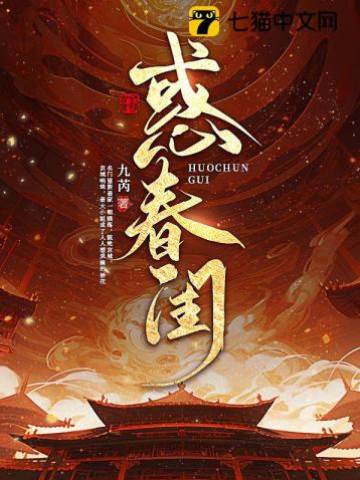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古早文女配改拿爽文劇本》 第139章 第139章
“驕。”衛修一本正經道, “魚百姓用得不對。”
驕好學地問道:“那應該用什麼?”
衛修:“助紂為。”
明白了!驕現學現用:“軍助紂為,殘害忠良。”
“你!”
鄭心的雙手死死地住了窗框。
在驕的上仿佛看到了另一個人的影子——盛兮。
盛兮是生平僅見,最為囂張跋扈之人。
的目慢慢沉淀了下來, 告訴自己不能隨隨便便就被他們給激怒了, 冷臉說道:“這里是京城, 由不得你們放肆。”
“區區舉子, 不過是仗著有了些許功名, 就敢談論朝政, 妄議軍,不好好教教你們,怕是禍到臨頭都還不知分寸。”
鄭心是一副為了他們好的樣子。
可惜的是,能讀書讀到這個份上的,還真沒幾個頭腦簡單到家的,毫沒有領了的“好意”。
衛修聲音里沒有半點起伏,就似在誠述事實,問道:“我們都是有功名的。”
哪怕是衛修, 在衛家遭難前也過了生試。
“太/祖曾有令但凡是有功名的學子,可以談論時政。”
衛修在“功名”加了重音。
這兩個字對吳琪而言極為刺耳,他自覺有人撐腰,揚手指著他,囂張道:“那就讓鄭大人奪了你們的功名!”
蠢貨!
鄭心在心中暗罵了一句。
不過, 有衛修在這里挑撥,自己再去和這些書呆子講道理顯然并不明智,唯有先抓起來, 才能控制局面。
給過他們機會了。
鄭心一揮手,立刻就有四個護衛氣勢洶洶地從樓梯下去,吳琪見狀眼睛一亮:“對對, 抓住他們,奪了他們的功名,趕出京城。”
被奪功名的仇恨,吳琪忘都忘不了,他非要讓池喻也嘗嘗相同的滋味。
Advertisement
學子們徹底沸騰了。
本來他們聽聞鄭心是鄭重明之,多是有些畏懼的,百姓天生畏,一品大員的鄭重明,對他們而言是何等高高在上的人,就算他們中了舉,窮極一生怕是也難以達到這個高度。
然而一聽到吳琪這囂之詞,心中的這份畏懼然無存,早已經在口激的憤怒徹底發了。
學子們大多不愿妄干戈。
可一旦被激怒到極點,了他們的肋,讓他們自覺退無可退時,所有的激憤都會化為力。
池喻適時地來了一句:“我們不能等死!”
“現在不但要啞了我們的口舌,更要奪了我們的功名,這天下難道要姓鄭了不。”
“為了我們的前程,為了大榮!”
護衛們正要沖下來拿人,對于他們而言,百無一用是書生,兒就沒有把這些學子放在眼里,豈料他們還沒來得及手,學子們或是舉起凳子,或是抄起掃把,一涌而上,朝他們當頭打了下去。
護衛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攻擊打得有點懵,不過,他們好歹也是練家子,手上還有武,立刻就從腰間拔劍,向距離最近的一個學子當頭砍去,眼見就要濺當場,就聽“鐺”的一聲,他手上的劍和一把造型古怪的腰刀撞在一起。盛琰搶一步擋在了那個學子的前,又轉頭對著他說道:“往后躲躲。”
這學子死里逃生,嚇得臉都白了,他面憤慨,哀聲道:“軍要殺人了!”
這句話,有如倒了駱駝的最后一稻草,原本還人猶豫不絕,但是現在,不反抗,就代表了坐以待斃。
他們才不管這些人到底是誰,反正是鄭重明的閨吩咐的,就當作是軍好了。
Advertisement
越來越多的學子們站了起來,爭相向鄭護衛們沖了過去,眼見形勢不妙,吳琪又讓他的兩個親兵幫忙,一想在鄭心臉,說不得討了鄭家姑娘的歡喜,他的位還能再進一步。
茶館里作了一團。
鄭家護衛們個個手持武,不過,他們還不敢隨便要人命,都是往肩膀,手臂砍。
對讀書人來說,手是何等的重要,砍手甚至比砍腦袋都更加令他們激憤。
盛琰手敏捷,四相救,讓他們激涕零,偶爾有他兼顧不到的,就會不知從哪兒彈出一塊小石子打斷攻勢。
驕擋在衛修和池喻他們前,一條馬鞭舞得虎虎生威。
衛修默默地拿起桌上茶盅,放在手上惦了惦,又放下,然后,拿起了茶壺,悄悄走到一個正和驕打在一塊兒的護衛后,踮著腳,雙手舉起,向他的后腦勺砸下。
衛修用盡全力的這一砸,護衛直接被砸懵了,他的搖晃了幾下,面朝下倒了下來。
砰!
衛修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沙塵,就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臉淡然從容。
驕:“……”
眼睛一亮,桃花眼神采飛揚,贊道:“衛修,你真厲害。”讓人刮目相看。
衛修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知道他話,驕并不在意,只道:“讓墨七叔在這兒陪你們,我上去把姓鄭的抓下來。”
驕說著,先是看了看四周,覺得人太多有點,就一腳踩上了桌子,然后,又跳上了另一張相鄰的桌子,借著滿地的桌椅,靈活地向樓梯的方向跑去。
手上正拿著一顆小石子,眼觀八路的墨七:“……”他其實只比王爺大一歲,真不用叔!
這把火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倆自然也不能坐在這里干看,衛修抄起一張板凳,就加了戰勢。
學子人多勢眾,盛琰手不凡,再加上有墨七在暗地里相護,局勢很快就呈現出了一面倒的架式。
站在二樓雅座的鄭心俏臉發白,沒有想到,事態會變如今這般。
不過是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杠的廢,原以為靠那四個護衛可以輕易的就把他們給制服。
鄭心并沒有想要奪他們的功名,也沒有這個權力啊,只是想著先把人控制住,讓他們吃點苦頭,知道在這京城,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免得他們總是顛倒黑白,妄議朝政,壞自家爹爹的名聲。
可是……
鄭心了帕子,想讓丫鬟回府里搬救兵,下頭這樣,本就出不去,更不用說是回家求救了。
“心,怎麼辦?”清平郡主眉頭直皺,了方寸。
清平出門帶了侍衛,不過只有區區兩人,剛剛也讓他們下去幫忙,既便如此,也沒能討著好,坐在這里就清楚的看到,一個侍衛被人從背后襲,然后,四五個人一擁而上,在地上拳打腳踢,本無從還手,而另一個侍衛,都找不見人了。
從來不知道,學子們可以這兇這樣。
娘的幾任駙馬,全都是斯斯文文的,在娘面前小意溫存,百般討好,早就看膩了,所以,一直都想找個武將……
沒想到,讀書人中也能有這般?
“他們不敢手的。”鄭心平靜了一下呼吸,斷言道,“別著急。”
話音剛落,雅座的門被人從外頭“砰”的一腳踢開,驕提起馬鞭,笑得可而又無害:“抓到你們了!”
鄭心被這句話驚得心跳慢一拍,偏生又說得這般活潑,就像在玩躲貓貓的孩。
清平怔了怔:“楚驕?!果然是你。”
楚?
鄭心口而出道:“你是楚家人?”
鄭心并未見過驕,清平只在過年朝賀時在宮中見過一回,方才就覺得有些像,因驕穿著男裝,容貌和神采與過年時又有了些區別,沒敢認。
現在一看,果然是!
鄭心蹙眉打量著,說道:“楚大姑娘,你別淌這趟混水,對你沒好。”
驕笑了起來:“喂,你是不是還沒搞清楚啊。”
最不喜彎彎繞繞地說話,抬手一揚馬鞭,指著鄭心說道:“你輸了。”
“抓起來,關進大牢。”
還記得剛剛的話呢!
驕不跟們啰嗦,費力爬到二樓就是為了抓人的。
揚起馬鞭,一鞭子就了下去。
馬鞭在的手上如臂所驅,鞭子打在了們面前的桌子上,手腕一轉,鞭子橫掃而過,把杯碗茶碟盡數掃落,在一連串的乒乓聲后,碎了一地。
鄭心嚇得花容失,哪里想得到,驕這麼野蠻,說打就打。
京城里哪家貴是像這樣的!
驕單手腰道,傲氣十足道:“是要束手就擒,還是我把你們打服?”
大嫂說了,在面對倒的勝利時,可以給對手一個俯首稱臣的機會。
大哥也說了,要是沒打過癮,可以給完再打。
驕是個聽大嫂話的好孩子,給們機會了!
然后,本不給鄭心說話的余地,提著馬鞭就沖了上去。
鄭心也會一些手腳功夫,不過,比起驕這樣認真練武,風雨無阻的,不過是些花拳繡,驕把鞭子往腰上一,拉住了手腕,反手往后一擰,鄭心痛得花容失,失聲大。
的護衛們全都在下頭,丫鬟撲過來想救,驕把手腕在了鄭心的后頸,稍稍用力。
鄭心嚇傻了,生怕瘋起來,真會朝自己的后頸來上一掌,對著丫鬟尖道:“別過來!”
驕又看了看清平。
清平嚇得小臉煞白,想說幾句話的,面對驕的強橫和馬鞭,立刻哭喊求饒道:“我服了。服了。”
驕有些憾,沒有耽擱時間,朝下頭喊道:“抓住了。”
下頭的局勢也基本大定,包括吳琪在的所有人都被制服。
學子們士氣高昂。
池喻抹了一把額頭的汗,趁熱打鐵道:“帶他們去皇城,我們一同請命,去問問,對我們這些學子們殺人滅口,肆意打殺是誰給軍的權力!”
學子們剛逢大捷,正在興頭上,腦子還發燙著,紛紛應是。
有人出去找了幾繩子,把這些人統統捆了起來,然后押解了出去。
鄭心和清平同樣也被捆住了雙手,踉蹌地出了茶館。
們都是京中貴,生慣養,有生以來,都沒有這般丟臉和恥辱過,在被驕推出茶館的時候,鄭心眼底通紅,恨不得在上咬下一口皮。
下意識地朝衛修看了一眼,只見衛修一臉漠然,心里更加復雜。
墨七給了茶館的掌柜一錠銀子,用來賠償茶館的損失,腳步匆匆地跟了上去。
茶館里頭靜鬧得這般大,早就已經引起了街上路人的注意,也有百姓去稟了府,他們出去沒有多久,迎面就有一隊五城兵馬司策馬而來。
一見此形,帶隊的傅君卿不由怔了怔。
“傅君卿!”清平大喜,喊道,“快救我……救我們!"
傅君卿本是在金吾衛,昭王的那件事他雖及時回頭,可擅金吾衛也有罪,蕭朔免了他的死罪后,把他下調到五城兵馬司。
對武將來說,金吾衛和五城兵馬司,簡直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一個是云端,一個就是被貶到塵埃。
傅君卿如今正任東城指揮使,正帶人例行巡邏,聽聞這里鬧事就過來了。
見此形,傅君卿眉峰微皺,問道:“怎麼回事?”
清平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起來,哽咽著告狀道:“是這些學子鬧事……”
池喻拱了拱手,義正言辭道:“我等在茶樓談時論政,軍對我們喊打喊殺,我們不服,想要問問大人,我等學生是否有議政之權,軍能否隨便打殺了我們。軍不去剿匪,反而要取我們無辜大榮百姓命,這是否應該?”
池喻言之鑿鑿。
鄭心聽得簡直怒火中燒,哪有這般顛倒黑白?!
這里哪有軍,哪有!
鄭心強忍著辱,厲聲質問,結果池喻理直氣壯地一指吳琪。
吳琪這職哪怕是買的,哪怕是今天剛拿到的,他也是軍的人!
自己可沒胡說!
池喻理直氣壯道:“如今皇上病重,蕭督主監國,我等想去向蕭督主討一個公道。”
“還大人見諒。”
他的聲音里帶著一種莫名的悲憤,聞者傷心,聽者落淚。
就好像他們已經被到了絕境,才不得不放手一駁。
鄭心的心中有一怒氣在翻滾。
明明被著打的是他們啊!
清平顧不上這麼多了,只向傅君卿道:“你愣著干什麼,把他們抓起來啊。”
學子們全都憤怒地看向了傅君卿,幾乎把他當作是他們一伙的。
清平又了一聲:“快啊!”
傅君卿只淡淡地看了一眼,就對池喻道:“我明白了,既如此,本指揮使親自送你們過去。”
啊?!
清平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口而出道:“傅君卿,你敢!我要跟你解除婚約。”
“那最好不過了。”傅君卿平靜地說道。
然后,他向學子們說道:“你們一眾人會驚憂到百姓,我送你們過去,蕭督主在東廠,不用去皇城,去東華門就是。”
說著,他拉著韁繩,調轉馬頭,還真就領他們去了。
學子們發出歡呼,他們越發覺得自己做得沒錯,自己所行皆是為了天道正義,不然這位大人也不會幫他們!
于是,在五城兵馬司的護送下,京兆府趕來的衙役也被順利打發走了,一眾學子押著幾人到了東廠。
池喻一向是學子們的代表,就由著他向東廠番役說道:“大人,學生等是來向蕭督主請命的,請蕭督主為我們這些來京赴考的學生們做主!”
然后又一五一十地把事大致了一遍。
番役們聽聞后,就有人進去稟告了。
蕭朔正在棋案前,和楚元辰相對而坐,聞言,微微笑了笑。
東廠的暗探遍布京城,茶館發生的事,在半個時辰前就有人稟到了他這里。
從士林手,煽風點火是他們的意思。
從軍中到民間再到士林,一步步地瓦解著這個大榮朝。
不過,能做到這個地步,多還是讓蕭朔有些意外的,他笑著對在楚元辰說道:“驕這丫頭,倒是頗有幾分靜樂郡主的風采。”
不止是驕,衛修的行事也有些意思。鄭重明的兒會出現在那個茶樓里,應當不是巧合。
楚元辰把玩著棋子,頭也不抬地說道:“阿說,有脾氣好。”
驕若是子稍弱一些,以后指不定會被人欺負,心緒難解。
“阿說了,與其被人欺負,不如去欺負別人。”
蕭朔啞然失笑。
蕭朔說道:“就事本座已知,對于士林所請,本座允了,人就暫關東廠誥獄。烏寧。”他吩咐道,“你跑一趟。”
烏寧拱手應是,退了出去。
楚元辰“啪”的一聲落了子,樂呵呵地說道:“鄭重明也該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215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654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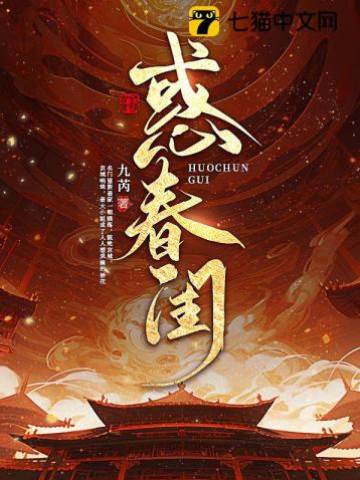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