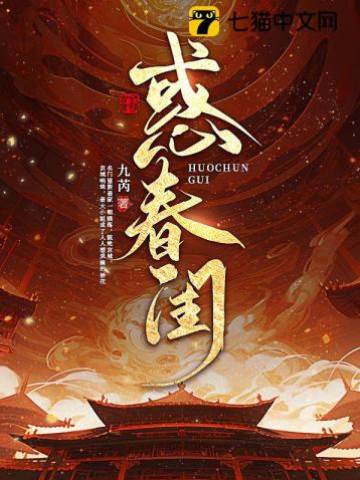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老祖宗她是真的狂》 番外 夢回大慶(2)
“嗚嗚嗚。”
“嗚嗚嗚嗚。”
哭聲凄凄慘慘戚戚,真是讓聞者傷心,除了敬一。
“哧。”
敬一微微側頭,看著某人抓了他的擺眼淚擤鼻涕,眼皮一跳。
宋慈抬起紅腫的雙眼,委委屈屈地和他對視,又順著他的視線看一眼擺,那噠噠的一小片,還帶了點可疑的粘稠。
的手頓時一松,訕訕地開口:“你,你是道長,講究心開闊,不會計較的吧?我不是故意的呢,是難自。”
很好,很茶很立,你高興就好。
敬一收回視線,一言不發。
宋慈有一丟丟的尷尬,再看著前方,一個小小的兒郎被丫鬟婆子小廝簇擁而來,雕玉琢的,長得十分漂亮,可那板著一張小臉故作老的樣子,卻又惹人看了無端發笑。
是的曾長孫呢,宋景禹小朋友。
“這,就是幾年過去了呀。”宋慈眼中帶了一欣。
孩子也長大了。
是的,這一祠堂,看到畫像,看到子子孫孫焚香告,宋慈的記憶就一點點的回籠了。
大慶王朝,來過,整十年。
記起來了。
“既然已經想起了,那就走吧,也不必再問了。”敬一轉。
宋慈一把拉著他,扁起了:“我才來,哪有說走就走的,再待會嘛。”
“伱就不怕魂歸天外,再無回返可能?”敬一低頭看著手臂上的手。
宋慈的手唰地一松,很快就是一副討好的表:“怎麼可能呢,這不是有你在嗎?你堂堂道長,不對,你是敬慧那禿頭,啊,是敬慧那得道高僧,這輩子是和尚,轉世是道長,可謂佛道雙修,佛法道法無邊了吧都?那酆都還不是你橫著走的,就你這樣,眼睜睜看著我魂歸天外,豈不是臉上無?我堅定相信,你一定不會讓這樣沉痛無的事發生的,對不!”
Advertisement
敬一:“……”
相信我,這些高帽壘起來,比黑白無常戴的那頂還要高。
“我們就再走走,玩一下回憶殺?我真的想再看看宋家。”宋慈輕輕的捻了他的擺一角,搖了又搖,整一副小可憐樣。
敬一嘆了一口氣。
佛道讓他來渡一人,大概是他兩世最大的劫數。
他袖子一揮,眼前空間一陣扭曲,轉眼,宋慈跟前又換了一畫面。
盛平四十年,宋慈離開的第十年,宋慈義學已經在大慶境開設了十個分校。
上京是總學,其余的東北,西北,江南,或多或的開了三個或四個,統一以宋慈義學為校名,只是擬了分校的地名點。
這十年來,各義學也培養出無數孤兒,讓他們有所依,能靠著學來的手藝謀生,更有甚者,也是善為善,以綿薄之力去幫助更貧苦的人。
有人謀生,也有人反饋義學,為其中的先生,教導那些世如同自己過去的孤兒。
這是宋慈義學的辦學傳承理念,以德為先,以人為本,傳手藝文化,也傳善心大。
當然了,有人恩,就免不了有人忘恩,此等人,全部被剝奪學籍,舍去名額,不義學承認,哪怕對方已有,只要有心人稍微打聽其品,便不愿與之結甚至被唾棄,漸漸的也就沉沒在暗流中,再無聲息。
今日是總學的校慶,學子統一穿著洗得潔白熨燙整齊的學服,臉上帶著笑容,手里捻了香,向著創辦義學的宋慈金參拜進香。
宋慈的金像,是站著的,供放在義學的善堂,手里執了一本書,臉部微垂,眼神慈祥,笑容溫和,仿佛在跟前看著萬千學子一般。
總學的山長崔十娘帶著激悼念了一番宋慈,亦演講了義學的辦學理念,激澎湃,人心扉。
Advertisement
奏樂起,嗑首三拜,一排排的學子捻著已燃起的檀香在善堂前碩大的四角鹿鼎香爐當中,告這位宋慈這位善人的在天之靈。
檀香寥寥。
宋慈熱淚盈眶,用手背了一下眼角,再抬頭看向屬于自己的金像,角綻出笑容。
上前去,卻見金旁豎了一個銅牌,上面刻寫著塑金的善人名字,很接地氣的名字,什麼馬二張大力連翠花等等合力而塑的金。而這些人,都是從善堂學有所出來謀生后,更有甚者靠著學的手藝為小富人的學子,這金像,是他們的恩回饋。
宋慈手了過去,腳一彈,飄了上去,和金像并排而立,笑意盈盈。
敬一抬頭,眼神微溫,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他能看見,乃至于宋慈側,此時金點點。
那是功德金,是這些人的信仰所加持的,屬于自己個人的。
功德金,只有大善之人才修得來。
義學的校慶,除了舉校同慶,也與民同慶,學子進香后,有心的民眾亦會前來小拜上香,除了這一天,還有宋慈的壽誕冥誕,義學也會開放善堂,供于民眾來上香。
所以宋慈也看到了許多農民樣子的百姓拿了香甚至添了香油,里喃喃有詞,保佑風調雨順,來年收更好。
宋慈:“……”
看向敬一,道:“不是,我辦的義學,這些學子供奉我就算了,老百姓們這是作甚?”
敬一微微一笑:“你聽。”
宋慈看過去,只見兩個已上香的人一邊添香油一邊說著這些年或多或的鬧荒,也虧得早些年宋太夫人種出了土豆這種糧食,產量極高,百姓也多了一個糧食種植的選擇,莊戶人家多都種些,做菜也好做糧食也罷,總能填飽肚子,依靠這些存糧倒熬了過去。
還有大棚菜,部分地區冬天依靠這技種出新鮮的綠葉菜來,也能讓那些富貴人家打牙祭,有的莊稼人依靠這點,自然也多了一分收。
所以宋慈也值得他們來為敬上一柱香。
宋慈輕嘆:“我何德何能。”
“有無德,在于人心。”敬一淡聲道。
宋慈嗯了一聲,好半晌,又憋了一句:“你就沒覺得,我明明活得好好的,卻像是個死人似的正在品香火很有點那個麼?”
敬一沒忍住:“在他們眼里,你已死,香火是對頭!”
哦豁,道長這是在懟我?!
宋慈狠狠瞪了敬一兩眼,對方不為所,目一轉,咦的一聲。
“是洲兒呢!”
宋慈飄到宋令洲邊,抬手了一下已經比高的孫子,好家伙,果然長得高又帥了。
此時,他正在回答兩個學子的問題,什麼車轱轆原理,這什麼鬼?
還有,宋令洲是義學的老師嗎?
待回了學生的問題后,宋令洲看到自己的小廝,笑容一滯。
小廝平安苦著臉過來,道:“四爺,夫人說請您回去溫書,說是準備明年的春闈。”
宋令洲眼神有些落寞,說道:“我不想再考了,我今年二十六,都已經當爹,就是春秋闈都考了三次了,我不想再落榜。”
他不是讀書的料,這個年紀了,考中舉人已是用盡了所有的知識量,還是堪堪考進末名,可接下來,他考了幾次春秋闈都落榜,他真的不想再考。
可他娘呢,孜孜不倦的讓他考,哪怕大伯說可以讓他尋個富庶一點的地方為知縣,也拒絕了。
他知道,他是三房的嫡長子,是頂梁柱,娘不甘心他只是舉人之,尤其三弟年聰慧,而頭上幾個堂哥也是各有所,對比之下,就更不甘了,非要讓他考個進士出來宗耀祖。
可是宋令洲不喜歡讀書,他喜歡鉆研這些墨家的東西,他愿來義學當個先生教這些學生制造那些靈巧的件,也不愿意待在書海里,他也看不進去。
宋慈看孫子一臉無奈又苦的樣子,不心疼壞了,這個魯氏,真是一如既往的癡又蠢,也不怕得孩子郁結早亡。
“不行,我得去點醒,道長,我們走。”
敬一皺眉,還不等他開口,宋慈就飄遠了。
唉。
是夜,魯氏多年來首次被婆婆夢了,可沒等開口問安呢,婆婆就指著喊孽障,跪下,然后劈里啪啦的一頓狂罵,罵宋令洲讀書考進士,如何這般。
隔天,魯氏起來時,渾沉重,后背都了,眼底一片烏青,嚇得周媽媽連聲問是不是做噩夢了?
“可不就是噩夢嗎,我夢見母親了,指著我一頓好罵。”魯氏呆呆的,這夢也太真實了。
這還沒算,第二晚,又來了,連續三晚,魯氏投降了。
“我不他總行了吧?母親您別再來罵我了。”
待得宋令洲來請安時,囁嚅著說不想考了,魯氏有些疲憊和哀涼:“你不想就不考了吧,可昶兒的學習,以后多讓他跟禹兒他們學,跟你大伯學。”
這是什麼意外之喜?
宋令洲:“娘,您這是真的答應了?”
魯氏看他滿臉放,眼神澄亮,不由有些慨,多年沒看到孩子這樣的眼神了,難道自己真的得太了?
母子離心。
婆婆托的夢所暗含的警告,真的嚇了一跳,罷了,也好過母子離心,還是指孫兒才吧。
“你無心考,那就作罷。不過,也不能無所事事,既然你喜歡墨家,又有舉人功名,也別去什麼地方了,不妨找你大伯運作一二,在工部混個末流的職也好,總算是待在京中。”反正在地方混,也得逐步升上來,還得和家里人分開,那還不如在京中謀職。
宋令洲歡喜不已,連聲應下:“我這就去找大伯。”
魯氏看他高興得像孩子一樣,不由也笑了下,心頗有些異樣,像是郁結盡散。
“娘,你怎麼忽然就改了主意了?”宋令洲就很好奇。
“因為你祖母連續幾晚罵我了。”
宋令洲:“……”
魯氏沒多作解釋,只是淺淺地笑,放過他,也放過自己,這是婆婆說的。
對這愚鈍庶子媳婦如此上道,宋慈很滿意,了魯氏敬的香,拂袖走了。
盛平四十一年寒冬,上京飄起了雪花。
楚帝躺在龍床上,邊圍了幾個肱大臣和太子,正在代旨。
沒錯,帝王多命短,他也六十七了,生命卻已走到了盡頭,眼下就是等天召回了。
道盡言,楚帝已是出氣多氣的,揮揮手,讓人都退下,只留下了宋致遠,還有跪在床尾的周公公。
宋致遠著手給他里含了一片參片,眼眶通紅。
楚帝像是老牛一樣著氣,看著跟前的老臣兼一輩子的老友,勉力地扯了扯角:“你個糟老頭,我要比你先行一步了。”
“皇上。”宋致遠跪在床邊,握著他的手,老淚縱橫。
“人終有一死,我沒想到……還是活不到七十。”楚帝笑了一下,眼里卻多帶了一不舍和不甘。
誰想死呢,他也不想,可他卻無力抗天。
他看向宋致遠,道:“宋允之,太子尚年輕,大慶也是外患漸起,我可以信你麼?哪怕我已死!”
宋致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握著他的手,道:“楚域,我必以我畢生之力,輔助太子替你守住這江山。汝之所向,吾之所往,汝之所往,吾亦趨,您,要記好了。還有,走慢一些,等我來。”
楚帝一笑:“好。”
若來世再遇,再攜手攪風云。
帝崩,舉國齊哀。
慈寧宮,汪太后病懨懨的躺在床上,白發人送黑發人,也是傷心絕。
“娘娘。”宋慈坐到了床邊。
汪太后瞇著眼看著眼前人:“阿慈麼,你來了,是來接哀家走麼?你不在了,小域也走了,哀家活著也沒意思了,阿慈呀,你不如也接哀家走吧。”
宋慈輕輕的拍了拍的手:“還沒到接您的時候,您壽數還沒盡呢。您可千萬要保重,別太傷心,他只是回天上侍奉佛祖了。還有您,下一世,我會尋您的。”
汪太后:“你別驢哀家,我會當真的。”
“一定不會。”
汪太后笑了:“那哀家先定個暗號,哀家命格貴不可言,來世必然也是。呀,那哀家就是命轉世,你就記住這暗號來尋我。”
“遵命,我的娘娘。”宋慈莞爾。
“姑姑,娘娘竟是笑了。”守在榻前的宮娥驚呼。
連翹攏著手了一眼,輕聲道:“娘娘大概夢見了此生最重要的人吧。”
或子,或友。
所以在笑,會笑。
(本章完)
7017k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215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556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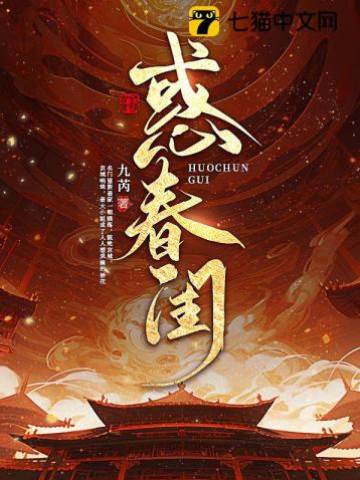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