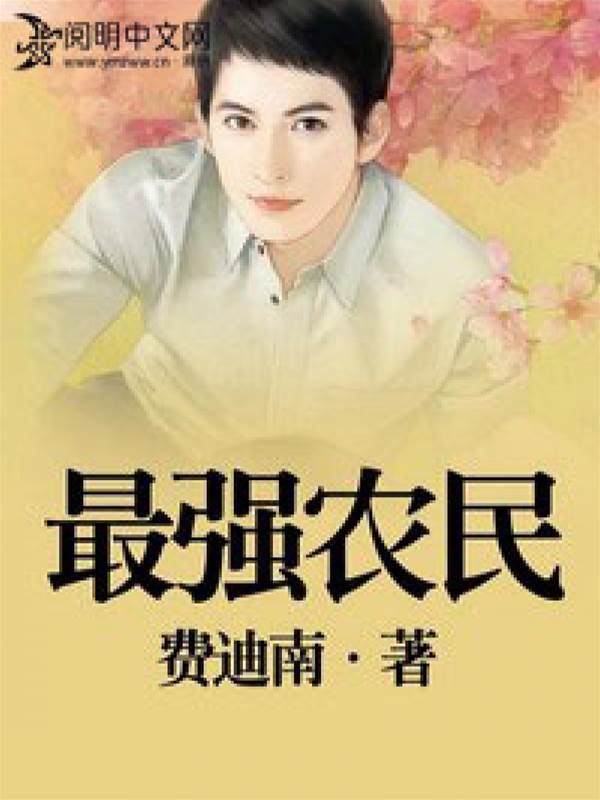《美豔妖婦》 第20章 可我是個幫親不幫理的人
小神槍向著小緩步走去。
小閉上了眼睛。
等死。
這一會兒,風停了,也沒聽見作坊的木欄桿響了。
只有小神槍的腳步聲。
殺氣騰騰。
然而,在小神槍走到我邊的時候,我突然暴起!撲向了小神槍。
毫無防備的小神槍,當即是被我在地上。
他的脖子,也被我的胳膊鎖住了。
“小快跑!”我大吼。
小神槍死命的掙紮,想要擺我的控制。
可我這一蠻力不是白長的,塔山村摔跤比賽三連冠也不是隨便吹的。
還有我這大伯親傳的“鎖頭絞”,就算現在被我制住的,是頭豹子,它也是掙不了!
“放手!”
“不放!”
我和小神槍就這麼僵持了十分鐘,直到我們兩個都是疲力竭。
“好了,你松手吧,那孩早就跑遠了,我追不上了,你再鎖,就要把我勒死了!”小神槍氣若遊的說。
聽了這話,我才是松開了手,躺在一邊,大口的著氣。
小神槍也是掙紮著爬起來,半跪在地上,劇烈的咳嗽著。
“媽的,我真的是想……活活弄死你。”小神槍轉頭,用充滿殺氣的眼神盯著我。
之前我從沒聽他罵過娘,看來這次是真的生氣了。
“那你就弄死我吧。”我張開雙臂。
小神槍並沒有手,而是鬱悶的盤坐在地上。
“我早就說過,這怪比惡鬼還可怕,就是因為這個由頭。”小神槍呢喃著說。
“什麼意思?”我問。
小神槍沒有回答我的話,起拾起了他的花槍。
“人死而不腐,吸月之氣,見氣而撲人。
“知道這種怪是什麼嗎?”小神槍問。
“行。”我回答。
“是,行可怕,只可怕在它啖活人,不死不腐,可它懼火,懼,懼桃木,懼怕很多東西。
“最重要的一點,它們沒有神智,也沒有記憶,三盞命火全滅,只靠這裡凝而不散的一怨氣,驅使著行。”小神槍用花槍的槍尖,指著我的嚨。
然後,小神槍收回了他的花槍,面容前所未有的冷峻,低頭凝視著我。
“那你覺得。
“有了神智和記憶的行,是什麼?
“是怪?
“還是。
“和你一樣的人類?”
我心裡咯噔的一下。
“當然還是怪!”我說。
小神槍戲謔的笑,又問我既然這樣想,那剛才為什麼要攔下他,放走小。
我沉默。
“對於魃來說,不頂,剛才我再來的遲一些,那孩就要喝你的,你怎麼辦?”小神槍問。
我依舊沉默。
小神槍搖了搖頭。
“罷了,我也不怪你,你是幫親不幫理的人,和我師傅一樣。
“可我師傅死了。
“所以,你也當心點。”
然後,小神槍扛起他的花槍,轉離開了。
小神槍走後,我躺在冰冷的地上,好久也沒有起來。
其實我早就想到了。
人死而複生,總會需要些代價,才能活下去。
姐也跟我說過。
不是人,也不是鬼。
我起,雙手狠狠的著臉頰。
我是一筋的人,這個那個的,我不喜歡多想。
我只在意一件事。
我姐們一夥子,到底想幹什麼?
把我們這破村攪的不得安寧,飛狗跳,人心惶惶。
只有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必須找出來。
我不喜歡調查搜集線索啥的,那麼多『』事兒,麻煩!
那就直接問出來。
然後我就去了村公所,去找大伯。
哪怕是用刀架在大伯的脖子上『』他,我也要把事實問出來。
可大伯他們搜山大隊的人,還沒回來。
我看了眼牆上的掛鐘,都快午夜十二點了。
難不他們今晚是想在山上過夜?
我幹坐在村公所的藤椅上,一直等,等到睡著,等到天亮,也沒見他們回來。
我這才是有些心急了。
難道他們在山上出了事?
不至於啊。
這支搜山大隊的人,全部都是村裡的壯勞力,而且除了我之外,村裡所有的獵人都去了。
他們還都是全副武裝,帶了狗和幹糧。
我想著他們大概只是卯了心,必須要找到那些孩子,不然絕不回來。
我出了門,向著塔山的西山坡走去。
找不到大伯,那我就換個知的人劫持『』問。
到了西山坡,我眼看著秦先生蓋的那棟別墅,已經是差不多要竣工了。
別墅很是氣派,中西結合的樣式,外牆被刷的亮白。
“秦先生呢?”我問一個正在幹活的村人。
“走了。”那村人回答。
“走了?他能去哪兒?”
“他說房子快落好了,要去接他的老板來住了。”
“他怎麼出的村?山道明明被堵了!”我皺眉。
“他說他繞遠路,走穿過塔山的那條道。”
我沒有辦法,只能是回去,繼續等大伯他們歸來。
可接連等了兩天,大伯他們還是沒有回來。
這下,不只是我有些慌。
整個塔山村的人,全都慌了!
搜山大隊的人,大概有五十號,全都是青壯年男『』,也就是說,基本上都是他們各自家庭的主心骨。
他們要是真的出事,那村子可就真的要出大事了!
可正如俗話所說,屋偏逢雨,雪上總會加霜。
這兩天,村裡還發生了另外一場悲劇。
住在村西的篾匠馬拐子和潑皮劉大,他們兩家人,全都是死在了飯桌上。
他們兩家是鄰居,昨天晌午湊了一桌,在馬拐子家吃飯。
那頓飯的菜湯裡,被摻了毒鼠強『藥』,桌上的五個人都是中了毒。
劉大臨死前大聲呼救,也有村人及時趕到救助。
可奈何毒鼠強的『藥』效太強,就算第一時間把劉大他們送到小王醫生的診所洗胃,還是沒有來得及。
馬拐子和他的婆娘,還有馬拐子的爹,一家三口都是當場死亡。
劉大也死了。
只有劉大的那個憨傻婆娘,被小王醫生救了回來,可是個癡呆傻子,只會傻笑,不會說話,也沒法告訴別人,到底發生了啥。
村公所的人去勘查,只說還是『自殺』,馬拐子和劉大兩家,都是丟了孩子的家庭,估計是想不開,就一起灌老鼠『藥』了。
這個判案的結果,讓村人都難以信服。
但一個確定的事實。
村裡又添了四口人命。
這天,有人挨家挨戶的通知,說讓全村的人去祠堂集合。
我和爸媽去到後,眼看著祠堂裡,已經了烏的一堆人。
村裡輩分最高的徐老太爺,被他的玄孫攙扶著,背對祠堂牌位,面對著大家。
“今天大家來,就是商討我們塔山村,最近發生的怪事劫難!”徐老太爺說。
隨即,徐老太爺的玄孫,拿出了一張紙,慢慢的讀出了紙上的名字。
李木匠兩口子,還有十幾位高齡老人,以及昨天剛過世的馬拐子等人,一共十九人!皆是死於『自殺』!
劉大家的娃娃,趙三虎家的娃娃,一共十二個小孩子!皆是失蹤!
還有最近,被我大伯帶上塔山的五十多個勞力爺們兒!也皆是失蹤!
聽完這些後,祠堂的村人們,都是一片死寂,沒有一個人說話。
“最難過的,就是喜子他也離奇死亡,震山剛接上喜子的班,也是失蹤下落不明,這些村都沒得了,村公所裡只剩下幾個小娃娃,這個關頭,也只能我這個老鄉賢站出來了,大家沒得意見吧?”徐老太爺說。
村人們此刻都如同無頭蒼蠅一般,當即是說全聽徐老太爺安排。
徐老太爺點頭,說:“村裡這些怪事劫難,有人說是那群戲班子邪人搞的鬼,有人說,是那個秦老板蓋的房子,了村裡的風水。
“甭管到底是咋回事,只有一點可以確定,咱們村,肯定是招惹上啥邪『』的東西了,對吧?”
大家都是應和。
“我的想法,是甭管別的,咱們先驅走這邪『』的東西再說,咱們,辦一場山祭。”徐老太爺說。
山祭,是我們塔山村的傳統,每逢旱災或是疫這樣的災禍,就由全村的獵人一同上山打圍獵,活捉一只猛,視它為災禍之源的邪神,帶回村裡。
之後,全村的人便聚集在一起,用長矛刺死那只猛,象征著殺死邪神,終結災禍。
徐老太爺的這個想法,有不人表示反對,現在又不是舊社會了,沒人信這一套了,往年有災禍的時候辦山祭,也從見災禍終結過。
“那是因為,咱們往年辦的山祭,不是真的山祭。”徐老太爺說。
隨即,徐老太爺像是猶疑了一下。
“這回的山祭,咱們不用猛當祭品了,咱們按照解放前的老規矩……”
“用活人。”
猜你喜歡
-
連載322 章

情欲青春
一位八零後男青年,從青春期走向性成熟期間的情欲往事。從花季少年到三十而立,林青的人生之路,情欲洶湧,百花盛開,春色無邊。一個個的女孩、熟女、少婦,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大學——謹以此文紀念那逝去的青春歲月。
59.7萬字7.59 302000 -
完結221 章
十景緞
這一看可讓文淵的心“蹦”地猛跳一下,燭光照映下,但見華瑄一襲輕軟白衣,羅衫下隱現紅兜,一只手伸入在雙腿之間,底下一片濕漉 漉地,像是花石間滲出緩緩流泉,布裙、床單濕了一大片。那手五指微屈,若有似無地蠕動著,也沾了一片濕,燭火照得有些閃亮。因是側臥 ,右腿壓在左腿上,雙腿稍一磨動,便聽得細小的滑溜聲。
75.6萬字8.33 148484 -
完結100 章
大理寺.卿
光風霽月的大理寺卿蘇陌憶,一向是盛京女子們的春閨夢裡人。如此天人之姿,卻在盛京官場上留下了個神鬼不懼,第一酷吏的兇名。平日裡審案子,蘇陌憶聽得最多的就是那句“大人饒命”。可沒曾想有朝一日,夜深無人處,昏燈羅帳時,有人竟能把這聲“大人饒命”叫得令他酥了骨頭。*十二年女扮男裝,十年寒窗苦讀。林晚卿好容易才走上刑獄之路,一心想為當年冤死的蕭家翻案正名。可是她遇到一個很棘手的男人。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被人下了藥的蘇大人憑借著最後一絲清明,將自己鎖在了大理寺宗案室。然而那一晚,尋找當年蕭家冤案線索的林晚卿恰巧也在那裡。
28.2萬字8.1 673000 -
完結53 章

我的后宮怎麼都性轉了
安牧不慎穿越到了自己曾經玩過的十八禁攻略遊戲中,本來準備窩在新手村一輩子不動彈,直到大結局來臨,但是為什麼可攻略人物接二連三的找上門! 最可怕的是,本來胸大臀翹各有千秋的美人們統統變成了男的啊!男的! 而且一個個如狼似虎的撲上來! 求問,可攻略人物起始好感度太高了怎麼辦!
16.5萬字8 7442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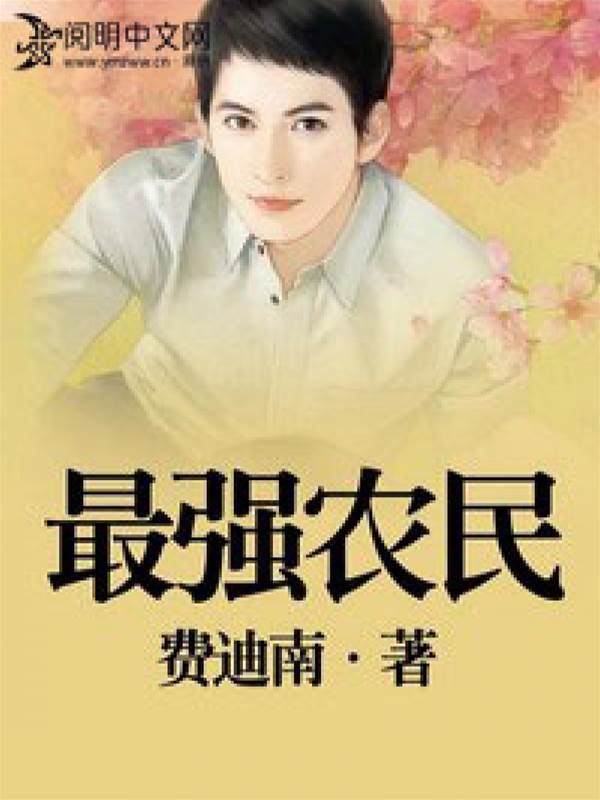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 106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