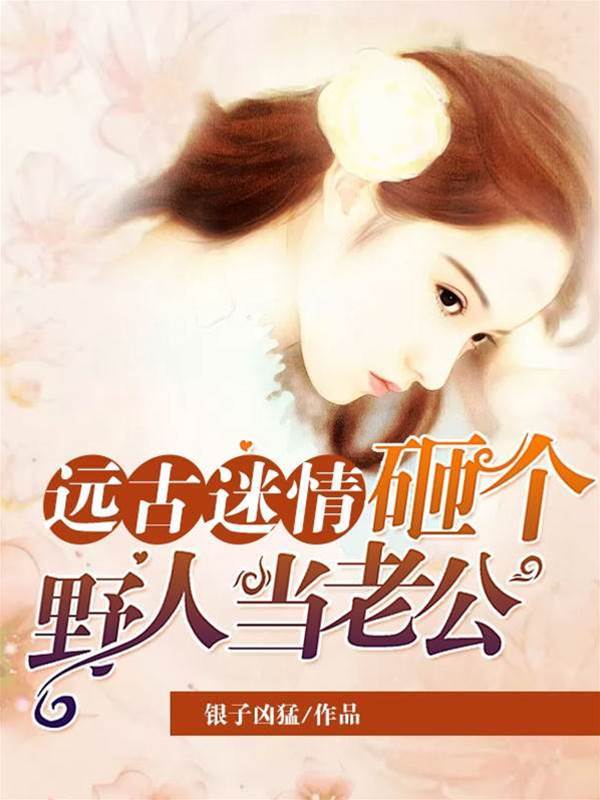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金枝寵后》 第36章 第 36 章
正是下晌, 殿外烈西傾,掛在屋檐邊上,過窗將趙玄的臉照的影撲朔。
信紙著不是單張, 趙玄方才起的惱怒散了些, 點點歡愉在膛漫開。
是個連經文都抄不下去的子,卻寫了如此多的字, 想必是有什麼事耽誤了, 到時候又該來哄自己了。
上次是送了只狗兒,這回改送什麼?
他撕開上了蠟封的信, 往外出時, 一個玉扳指咕嚕嚕從信封里滾落出來,
一連串清脆的聲響連續在木板上,最終認主人一般滾落至趙玄腳邊。
倒是沒摔壞, 李近麟心驚膽的恨不得就此死過去,卻仍要撿起呈到陛下面前。
趙玄對此置若罔聞,看也不看玉扳指一眼, 看起來信件, 翻到最后一張信紙,目落在最后一段。
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以求一別, 各還本道。
瞬時三伏夏日, 殿卻蔓起凜冽寒意。
周遭軍侍都暗道不妙,送信來的鎧衛更是嚇破了膽, 本以為是門好差事,搶著來送呢,如今只恨不得給當初搶信的自己一個耳。
不知寫的什麼, 眾人卻見陛下反手撕毀了信紙,丟去了地上。
陛下立在原地自是巋然不,而后輕笑了聲,再然后竟然出一副倉惶悵然的模樣,盯著被他撕碎丟棄在地上的滿地碎紙看,彎腰想撿起來,卻又止住了。
眾人連忙跪下,止不住抖起來,陛下這是......
“真是可笑......”仿佛方才出窘態的人不是他自己一般,陛下如今冷眼旁觀那一堆廢紙,仿佛神佛一般無悲無喜。
活了這麼多年,今時今日才他會了一回心慌意肝腸寸斷的滋味。
Advertisement
他不信這信中是真,可又怕這其中有一句是真,字字如同萃了毒,猶如利刃一般割在他上。
原來這世上最毒的藥,不是□□,是。
口甜到發膩,卻能人上一刻在云端,下一刻便跌地獄。
他......
如今是被推了地獄——
不,他不信。
如何能信?前日兩人才濃意,今日竟然絕至此?
“陛、陛下”李近麟不知信里寫了什麼,只想要退出殿外,好保一命。
趙玄居高臨下,眼皮都沒抬,神肅穆,忽的拂袖而出,那瞬間仿佛棄了一修行,重新披上了一層瘋魔外。
他要親自問,要當面聽說。
聽親口說。
看還能不能將這封信上的一字一句朝著他說出口。
從紫觀往江都王府,快馬加鞭不過半個時辰。
百名衛守著,一群人嫻馬技,徑直策馬,江都王府沒了主人,只剩一群奴役,何曾見過此等架勢?
皆跪在一嚇的不知所以,連攔都不敢,以犯了什麼抄家滅族的事。
趙玄背立于正堂,一路策馬揚鞭,李近麟下馬后累的氣吁吁,瞧了眼陛下,陛下與他們一道,并未乘坐馬車,他們這群人累這副狗樣,陛下倒是呼吸平穩,半點不見紊。
李近麟和藹的朝奴婢們笑:“別怕,我們是來找大姑娘的,去請大姑娘出來。”
侍們抖如糠篩,不敢再瞞,嚇道:“大、大姑娘不在府里。”
“哦?!那去了何?”
“奴婢們也不知......”
正在此時,有暗衛抖如糠篩,哆哆嗦嗦的過來,噗通一聲跪倒了地上,朝著皇帝的后背開始磕頭:“陛、陛下,臣等看......看過了,大姑娘確實不在府里。”
Advertisement
趙玄早有猜測,聞言只蹙著眉,不知想些什麼。
他一腳掀翻面前跪著的暗衛,怒火滔天。
“吩咐你們盯著,將人盯丟了......都滾出來!”
***
一輛青篷馬車自皇城駛出,趕車的馬夫架勢練,駕著馬兒一路疾行,等出京遠了,了幽州地界,才慢下來。
凡百姓遠離所居地百里之外必須路引,一行人的路引自然是早就備好的。
阿四去城門遞上路引,排隊等了會兒,到他們時,城垣下的兵接過翻了一眼,眼神掃過簾子,問趕馬的馬夫:“里邊是何人?”
趕車的侍衛名喚阿四,江都王取名隨意,邊的侍衛都是按照府的順序排名,阿大,阿二......以此類推。
阿四被派來護送姑娘,自然是親信,雖江都王也沒告訴他為何要他們遮遮掩掩出城,卻還是照辦。
他拱手道:“車是我家姑娘并侍,途經幽州。”
兵揚揚下,道:“車里的下來,檢查。”
阿四詫異,“有了路引還要檢查?”
那兵十分傲氣,嫌棄他們沒見過世面:“這可是幽州,旁邊就是皇城,哪能隨意放過?你們這是出城,要是城,連車簾子上的線,腳底板上的泥,都要出來查。”
天子腳下,哪怕混進去一針都是他們的失職,出城倒是簡單的多,隨意搜查一下,瞧瞧文書就。
一雙玉手掀開車簾,兩名姑娘從青蓬馬車里緩緩走來。
玉照被墜兒攙著,頭戴寬檐幃帽,月白輕紗繞著的子一圈,垂至間,下擺只一截未曾染的黃白絹,與以往的打扮多有不同,樸素的很。
如今掩了容貌,又是一不出彩的夸大打扮,連曼妙姿都遮的嚴嚴實實,倒是無人再多看一眼。
就連那兵也不甚留意,往車搜查了一圈,按上了印便放了們進去。
幽州不比皇都,著古樸氣息。
馬車停靠在一簡樸的客棧旁。
車里墜兒見車停了,連忙問:“阿四,到了嗎?”
“到客棧了,只是這客棧簡陋.......”
玉照曼聲道:“無事,簡陋便簡陋吧。”
出行在外,哪兒能錦玉食。
這天氣一日熱過一日,上出了薄汗,馬車里狹小顛簸,又悶的慌。上的服磨的難,昨夜一路顛簸更是未曾睡,如今哪怕是地上,一躺上去準能立馬睡著。
墜兒去客棧前堂了銀錢,另外多付了一串銅錢,吩咐送來幾桶熱水,姑娘要泡澡。
兩人便上了樓,玉照坐去了床上,渾酸,一頭倒在了床上,哀哀睜眼著床帷。
墜兒也一酸痛,“別說是姑娘您了,便是我也沒做過這麼長時間的馬車。”
京城渡口查得嚴,這路引名稱不對,怕是瞞不過去,是以江都王吩咐們乘著馬車回去。
墜兒一直跟著玉照,倒是心中有數,上次那位在紫觀救了家姑娘的道長,貌似是了不得的大人,家姑娘還招惹到人家了......
玉照有一副極容易招蚊蟲的子,明明是與墜兒一同做馬車,墜兒毫無察覺的憨憨大睡,可偏偏玉照上手背,甚至口上都遭蚊蟲咬了,剛開始毫無所覺,如今起了疹子只覺得又痛又。
正好門外停好馬的阿四回來,順手提了兩桶燒好的熱水上樓,隔著門喊墜兒提進房里。
墜兒那廂倒好了水,才想起一事來,連忙追上阿四。
給了他一些碎銀子,對他道:“你空去尋個藥鋪,買些止的熏蚊蟲的藥膏,多買一些,路途遠,買了指定不夠用。”
這回走的急,許多東西都沒備上。
阿四應了聲,立刻就下了樓打聽藥鋪的位置。
那藥鋪說起來他城時還經過,是以不廢多力氣就找到了。
“老板,被蚊蟲咬了,有止的藥膏賣嗎?”
那老板鋪子臨著街頭而立,鋪子小,東西擺的卻滿滿當當。
聽了忙應和道:“有的,有的,大人且等著,我去給你找找。”
“還有熏蚊蟲的艾草,也給我拿上一些。”
“哎,哎。”老板連忙應了下來。
阿四等了許久,老板終于從一堆雜貨中翻找出來,他接過還沒來得及付錢,南邊城門道上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踏響,他戰場上染過人的都不由的心頭一震。
阿四瞇起了眼睛看過去,塵土飛揚的道上涌出許多駿馬,灰塵太大,里頭人都瞧不清。
駿馬雷霆而出,離得近了阿四瞧出,那馬上立著的人皆是群金甲,腰佩環首刀,□□戰馬竟都穿著金馬鎧!
莫非是明鎧衛?
那不是皇城的軍隊嗎?是八衛三萬余人中挑出來專屬圣人的近護衛,各個千里挑一,為何會出現在此?
阿四面上微變,見那明鎧衛并非只是借過此城的意思,似乎是圍住了城門,不打算走。
“哎?!大人!您銀子還沒給啊!!”
阿四掏出一錠紋銀,丟到了那人臺面上,急忙走了。
藥鋪老板跟小二兩大眼瞪小眼。
店小二低頭看了眼他才打包好的一串艾草包,震驚道:“這人瞧著人模人樣,高大威猛,腰上還挎著刀,我還以為是個當的,是不是腦子有什麼病?銀子給了,藥不拿!”
老板罵他道:“你個死的!沒長不?不會去追?!”
怪不得藥鋪生意差,原是找了個不會看人眼神的店小二。
店小二被罵了一通,不敢反,拎這藥包就去追,可方才人還在眼前,只一轉眼,那位客就不知跑去了何。
倒是他跟來的這街道,不知何時圍滿了高大威猛的兵,急聲厲呵,似乎是在著急尋人。
民怕兵,那是天生的。
小二一見,渾哆嗦,就要走開。
一兇神惡煞的將軍老遠看到他,怒喝道:“你!就你!跑什麼跑?把他帶過來!本問話!”
小二渾抖著被人抬了過去,發現被問話的不止他一人,還有許多人。
他找了一圈沒找著方才那位沒拿藥包的客人,卻找到了他們幽州城里守城的人大老爺,一個個平日里拽的二五八萬,不拿正眼看人,如今跟孫子一般,各個乖乖排隊圍一圈等著將軍問話。
連守城的人大老爺都被來問話?
依稀聽見他們說什麼封城、姑娘———
。。。。。
玉照才在墜兒的伺候下洗了頭發,渾浸在浴桶中,水溫氤氳,升起淺淺霧氣。
眼睫上不知不覺掛上了細碎水霧,蹙著眉在水里著腳踝、手腕。
門外忽的傳來倉促的叩門聲,打斷了的沉思。
“姑娘!京畿來了好多人馬,在城門探問搜查,這里恐怕不安全,不如再往前十多里,便是城中,換間安全的客棧。”
阿四得了江都王命令送姑娘回江都,這一路行蹤蹊蹺就一個丫鬟跟著,阿四直覺自家王爺是為了躲避耳目。
雖不知是什麼事,但謹慎小心些總不出錯。
兵定然不是來抓他們的,但京畿的明鎧衛出來此,定是有重大變故發生。
謀反還是其他的?
除了捉拿反賊,阿四想不出別的理由。若是真有反賊,恐怕就不是一個兩個那麼簡單的了,必有一場戰。
此城簡陋,若真發生,他一人定然護不住姑娘,到時候他萬難辭其咎。
總之,務必立刻送走姑娘。
墜兒匆匆伺候玉照從浴桶中起來,見玉照頭發往下滴水,連忙道:“也不急這一時半會兒,干凈頭發再走罷,免得了氣。”
玉照早就坐立難安,聞言眉頭皺:“不了,頭發不用管它,快些給我穿上裳,現在就走。”
反正寬大的帷幕一遮,誰也不知里邊是怎樣一副景。
阿四去牽馬,兩人匆匆拿著包裹便打算出去乘車,只是不巧,一下樓迎頭便撞上一群搜查坐在客棧正堂的兵。
為首之人著金黃鎧甲,手中持著環首刀,兩只眉頭竟是連了一條線。
他朝玉照主仆兩人看過來,目著打量和探究,在玉照頭上腳下來回巡視。
似乎頗為好奇。
另一人立刻低了聲兒,提醒他:“看什麼看?當心吃不了兜著走!”
玉照墜兒只當做是看不見聽不著,雖不知為何看了自己要吃不了兜著走。
只一門心思低頭前走,想離開這。
那位金甲住二人:“哎?兩位姑娘,可別邁過這道門檻兒去。”
玉照察言觀,立刻斂衽一禮,溫聲道:“我主仆二人在此暫歇,路引什麼的都有,在后堂小廝上,您二位要查便隨我們一同去查,只是我家中有急事,等不及,還請二位大人見諒。”
說完,才看見這可不止兩位大人!
虛掩的門外影子晃,依稀還能聽見馬兒嘶鳴,兵甲鐵刃撞擊,嘈雜紛,依稀聽到有人道:“守好了!一只母蚊子都別放出去!”
這是......什麼況?
“別別別,我等可不起你的禮。”
那將軍見玉照朝自己行禮,嚇了一跳,連忙擺擺手面和善笑意道:“姑娘回房去待著,今個兒誰都不能踏出一步。”
玉照試探:“那我們何時能走?我家有急事,真耽誤不得.......”
另一位聽見這話忍不住笑出了聲,玉照詫異朝他看去,他連忙住了面上笑意,咳了咳擺手道:“快了,你且先回去等等。”
等等那位就到了。
玉照哪怕心中著急也不敢再說什麼,只能重新回了樓上房中,靜靜坐著。
“客棧所有人員分開巡查,不允許同住一間廂房,你們二位,哪位出去去隔壁廂房?”門外甲衛做了個請的手勢,玉照墜兒兩兩相看,皆從對方的眼中看出誠惶誠恐來。
深宅里走出來的姑娘,何曾見過這等仗勢?
玉照卻很快鎮定了下來,左右都知道,大齊治下極為嚴苛,倒是沒聽說過朝中某地發生過士兵來的。
“姑娘.......”墜兒敢離開邊。
“我沒事,”玉照握著墜兒嚇得發涼的手,安:“都是皇都衛兵,紀律嚴明,不敢來的。”
猥婦,會被執行刑或宮刑,最好的下場,也是割了耳朵被流放三千里。
這群人皆是前途明將來封侯拜相之輩,怎會自尋死路呢。
墜兒滿面愁容,無奈走后,玉照關上了門,自己一人待在房里,支起耳朵仔細聽著外邊靜。
外邊原先吵鬧的很,這會兒卻是靜悄悄的,尚且能聽見自己頭發上水珠滴到地上的聲音,方才在下邊是沒覺,這一會兒才覺后背濡了一片。
拆了幃帽,見服前邊后邊都被頭發上的水滲,了一大片。
尋了半天,也沒能找到頭發的帕子,索坐在床上不再管,任由水滴滴落。
方才安墜兒的話也是安自己的話,如今六神無主,心緒不寧。
這等緒,已經困擾了多日,自從那日以后......
玉照想到此心頭酸難忍。
那日,實在是自己太過害怕,如今想起,都仍是害怕。
就像是一只蝸牛,喜歡慢悠悠的拖著殼走,心好來天不怕地不怕,遇到怕的事躲起來就是,丟了殼,如何會同意?
也不知過去了多久,沉浸在思緒里的玉照忽然聽見樓下有馬蹄聲由遠及近。
踏響如雷霆轟隆。
甲胄,鐵劃空,響遏行云,士兵整齊的跪拜之聲。
玉照渾一,慌中想要開窗,去看看樓下,可作慢了一步,已經聽到樓梯傳來腳步聲。
那聲音沉穩、從容。
猜你喜歡
-
完結1987 章
重生之農門嬌女
林家萬傾草地一朵花,孫女孫子都是頂呱呱。偏偏金貴皇子被放逐,可見最是無情帝王家。好在有空間作弊器在手,嬌嬌和八皇子這對兒命定姻緣的小兒女,一路混合雙打,踩小人,鬥BOSS,成長的彪悍又兇險。最終登上帝王寶座,帶領大越奔向現代化,威震四海八荒。
367.6萬字8.46 654046 -
完結1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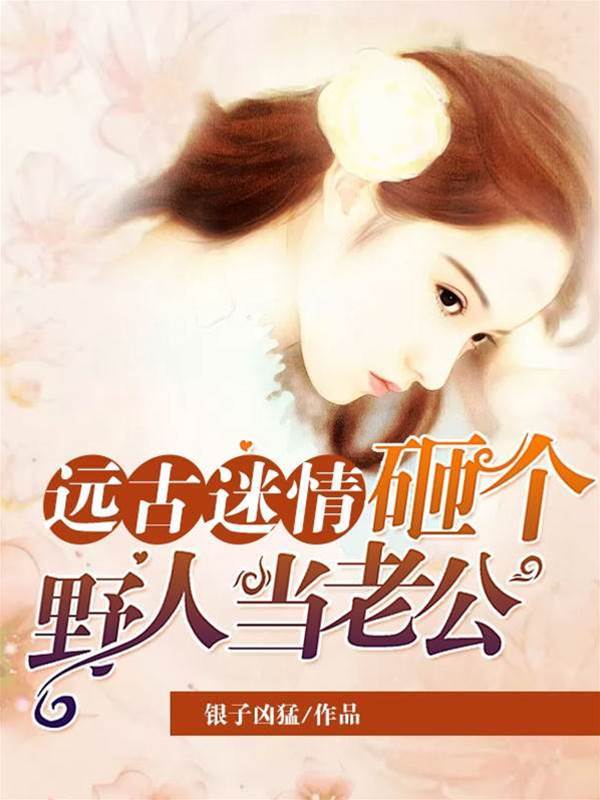
遠古迷情:砸個野人當老公
穿越到原始深林,被野人撿了 野人很好,包吃包喝包住,然而作為代價,她要陪吃陪喝陪睡! 于是見面的第一天,野人就毫不客氣的撕了她的衣服,分開她的雙腿 作為報復,她將野人收集的皮毛割成一塊塊,將他抓來的兔子地鼠放生,生火差點燒了整個山洞 然而野人只是摸摸她的小腦袋,眼神溫柔,似乎在說,寶貝,別鬧了!
41.9萬字8 13082 -
完結161 章

皇家寵媳:帝後嗑CP啦
【傳統古言 宮鬥宅鬥 無穿越無重生 架空曆史 1V1 甜寵 青梅竹馬】 【溫柔堅韌美人VS冷淡沉穩太子殿下】 穆霜吟生母逝後不過三月,穆相娶了續弦。 新夫人帶了雙兒女進府,據說是穆相骨肉,更離奇的是這對龍鳳胎比穆霜吟早出生個把月。遊方道士說,穆霜吟出生時辰不好,穆老夫人信了。 自此令穆霜吟獨居一院,不聞不問。 當今皇後為聖上添了位公主,帝心甚悅,可惜公主沒立住。 皇後思女成疾,病重不起。 帝後情深,聖上聽聞穆相有一女,生辰與公主如出一轍,遂讓人將她帶進宮,以慰皇後思女之心。 皇後鳳體果真漸好,帝大喜,封穆霜吟為昭陽郡主,賜居丹昭宮,養於皇後膝下。 昭陽郡主姿容姣姣,深得帝後寵愛,長到及笄之齡,京城世家勳貴凡有適齡男子者皆蠢蠢欲動。 周明帝:“昭陽郡主明慧柔婉,德行無雙,不乏未來國母風範,太子得此太子妃,乃我大周之幸。” 皇後:“昭陽郡主容色絕俗,至誠至孝,本宮與皇上有此兒媳,太子有此正妃,乃我皇家之幸。” 太子:“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此生得阿吟相伴,別無所求。” 本書又名#太子寵妻日常#ps:有私設
26.4萬字8.18 26413 -
連載773 章

洞房夜,給禁欲殘王治好隱疾后塌了床
穿成丑名在外的廢柴庶女,洞房夜差點被殘疾戰王大卸八塊,人人喊打! 蘇染汐冷笑!關門!扒下戰王褲子!一氣呵成! 蘇染汐:王爺,我治好你的不舉之癥,你許我一紙和離書! 世人欺她,親人辱她,朋友叛她,白蓮花害她……那又如何? 在醫她是起死回生的賽華佗,在朝她是舌戰群臣的女諸葛,在商她是八面玲瓏的女首富,在文她是下筆成章的絕代才女…… 她在哪兒,哪兒就是傳奇!名動天下之際,追求者如過江之卿。 戰王黑著臉將她抱回家,跪下求貼貼:“王妃,何時召本王侍寢?” ...
142.7萬字8.18 132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