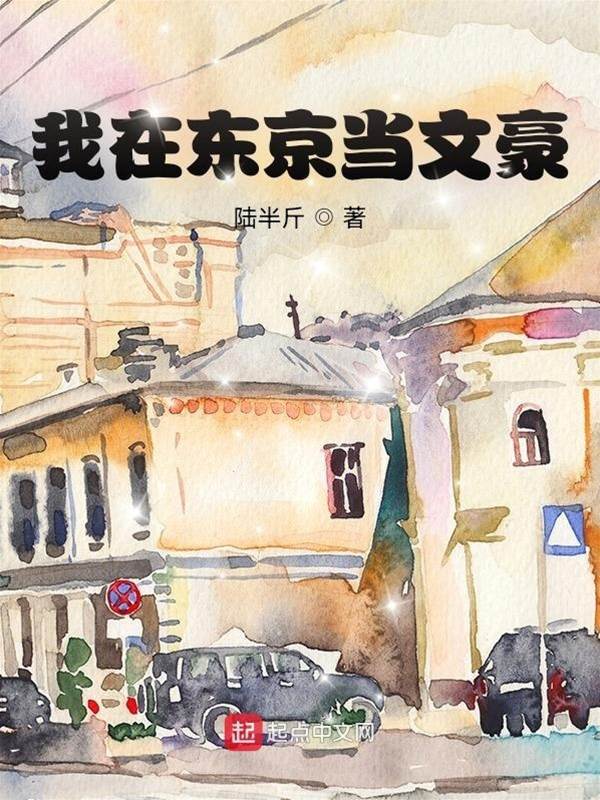《回到明朝當王爺》 第456章 戰端初現
克里葉特部大約有九千多人,在族長的分派下分爲三個大牧區分別放牧牛羊。這一部三千多人,在靠近瓦剌草原的地境遊牧。
快要中午了,日頭到了頭頂,有些刺眼,數百頂營帳散落在草原各。一頂頂營帳上邊冒起了僂僂飲煙,不知飢和疲倦的孩子們仍然三五羣的躲在帳幕的涼摔跤玩耍著。
這時候,遠遠的,草原盡頭出現了一道踽踽移的黑線,一個牧人最先看到了,他立即警覺地撥轉馬頭。扔下羣的牛羊,趕回大帳報信。牧羊犬忠實地替主人執行著守護牛羊的責任,督促著它們仍然留在原地,悠閒的吃著草。
西方,那是與瓦剌部接壤的地方,儘管雙方一直沒有兵戎相見,但是隨著伯部與瓦剌部越來越激烈的廝殺,科爾沁部做爲伯的堅定盟友,早已斷絕了和瓦剌部的往來,從他那邊忽然趕來一支隊伍,牧人們立即警覺起來。
人馬聚集的很快,這些牧民本就是天生的戰士,他們殺起人來,絕不會比用一柄鋒利的小刀屠宰一頭羊慢上半分。
但是很顯然,他們這是虛驚一場。那些大約五百人左右的隊伍走的實在是太慢了,等了好久,牧人們才發現那是一支駝隊,每頭駱駝上都是大包小裹,堆滿了東西。
駝隊兩側是乘馬的騎士,他們穿著各式各樣、各個種族的裳,佩戴的武也是五花八門,那些人裡不但有彬彬有禮的漢人、用韃靼語大聲說笑的蒙人,甚至還有高鼻深目,佩戴著彎月般的烏茲鋼刀的西域人。
悠揚的駝鈴聲靜止了下來,烏恩其欠起屁向那駝隊後方看了看,幾十頭駱駝,還有幾輛大車,烏恩其把佩刀掛回了腰間,臉上出了輕鬆的笑意。
Advertisement
很明顯,這是一支從西方往東方來的商隊,看他們的人種和車隊有意做出的分離,應該是不同的小商隊,在一路東來的過程中漸漸彙集到一起,互相支援,共同對抗沿途的馬賊、強盜。
他們之中有漢人的商賈,有來自天竺、大食、波斯等遙遠地方的商人,南來北往的過程中他們的駱駝始終載滿了各種貨。
商隊在草原上是到歡迎和尊重的,因爲他們在空曠的四野無人的草原上,可以爲牧人們送來急需的各種生活用品,甚至一些奢侈的消費品,滋潤他們常年累月遊弋於草原上的枯燥生活。
不用吩咐,已經有部落的牧人同著韃靼語的商旅熱地談起來。一個穿著條紋長衫,脣上長著兩撇彎曲如鉤的鬍子的男人,在同幾個克里葉特部牧民熱談片刻後,在他們的指引下向烏恩其撥馬走來。
烏恩其是科爾沁領主的遠房侄子,是這支部落的首領之一。那人彬彬有禮地向他施禮,簡潔地說明了自己的來意,他吞彌,是來自天竺的商人,要到更東方的地方去出售他們的商品,併購買東方的貨再運回遙遠的西方。他將在此暫時駐紮,並請求允許經由科爾沁人的領地。
吞彌說完,微笑著向烏恩其獻上了他的禮,一張豪華的波斯長地毯。烏恩其眉開眼笑地答應著,說道:“好吧,你們可以在這裡宿營,在我們科爾沁的草原上,我們將保證你們的安全”。
“謝謝你,慷慨的主人”,吞彌微笑著俯施禮,然後大聲吆喝他們的夥伴們立即就在駐紮休息。烏恩其手下的牧人也散開了,婦人和孩子們也圍攏了來,好奇地打量著這些遠方的商旅,並且小聲地詢問著他們都帶了些什麼商品,希能夠買到自己家裡能用的東西。
Advertisement
烏恩其興沖沖地回到氈包,把那捆地毯給自己的妻子,這才重新趕了出來。他注意到,那些商旅很規矩,他們到了距離烏恩其營盤大約兩裡地外的河邊駐紮,貨都卸放在地上,駱駝悠閒地吃著草、喝著水,休息著長途跋涉有些疲乏的。
那些商賈們則搬出了琳瑯滿目的貨,吸引了大羣的牧人帶著人和孩子趕去易。不時有家資雄厚的貴族被商賈們引進帳蓬,捧出更加珍貴的貨,唾沫橫飛地吹噓著,希科爾沁的貴族老爺們能夠把它們買下來。
一個黑臉膛的牧民縱馬向烏恩其馳來,到了近前一躍下馬。滿面帶笑地道:“嗨,烏恩其大哥”。
烏恩其注意到他是從那些西方商賈的營地裡趕回來,便微笑著問道:“胡魯,買了什麼東西?”
胡魯材不高,但是肩寬膀厚、形沉穩,滿臉的橫,顯得十分彪悍。他哈哈笑道:“給我的人買了兩粒珍珠,還買了一柄烏滋彎刀。”
他說著從懷裡掏出一柄掌大的小彎刀,嚓地一聲刀出鞘,優的弧度、刀刃上有雪花似的漂亮花紋,鋒利的刀刃在下發出凜凜的寒。
烏恩其的目一下子變的熾烈起來。烏茲鋼是天竺特有的一種鋼鐵,是製作刀劍最好的頂級用鋼,這種鋼在鑄造刀劍時表面會有一種特殊的花紋———穆罕默德紋,花紋使刀刃形眼無法分辨的鋸齒,使刀劍更加鋒利。
但是這種鋼刀也太昂貴了,他只見過部落首領有一柄阿拉伯式的烏茲彎刀。出手指,輕輕地拭著刀刃,烏恩其不發出讚歎之聲。
胡魯左右看看,悄聲道:“烏恩其,我看到那些西域胡人,攜帶著無數的寶石,我還看到幾口三尺長的烏滋彎刀,那都是頂尖兒的鋒利寶刀啊。他們只有五百多人,有那麼多貨……”。
胡魯了厚的脣,低聲道:“我們要不要把他們幹掉?很容易的”。
烏恩其子一震,驚訝地看著胡魯。韃靼貴族們有時也會冒充馬賊劫掠過路的商旅,但是這是遭貴族們唾棄的行爲,而且一旦泄了消息,商旅們將不敢來他們的部落做生意,對他們的影響太大。
所以非不得已,他們是不對商旅手的,而且一旦要劫掠商旅,一般都會喬裝改扮,到遠離他們駐地的地方去,而且絕不留活口,無論是婦人孩子還是老人,本不敢留作奴隸,一律統統殺掉,這一點比真正的馬賊還要殘忍。
烏恩其跟著父親和叔父也幹過這樣的事,但是這是在他們自己的牧地,殺死上門來的客人,而且還贈送了他一份貴重的禮,這樣做讓他有些難以接。
胡魯繼續勸說著:“他們五百人,而我們的戰士大約有一千人上下,一千個勇士對付五百個商旅,他們一個都跑不掉。他們有大量的財寶,我們將馬上爲科爾沁最富有的人之一,最重要的是,現在草原上到都在戰鬥,我們不說,有誰證明他們平安地到達了我們的營地?
幹掉他們!搶走他們的財寶,把他們深埋在地上,驅趕著牛羣去踩上兩圈兒,來年,那裡就是一片的草地。這件事不會有人知道,這裡只有我們的族人”。
烏恩其的貪念被他挑撥了起來。他擡眼了河邊的胡人營帳,眼珠轉著,漸漸泛起亮的芒。
“胡魯……”,烏恩其聲音有些沙啞:“吃完了飯還要放牧呢,讓我們的族人都回來,晚上纔可以去易!”
胡魯一怔,不甘心地道:“烏恩其!”
烏恩其看了他一眼,低促地道:“召集我們的人手!”
“好咧!”胡魯大喜過,興沖沖地跳上馬,飛快地去了。
吞彌和兩個漢人打扮的人蹲在河邊,一邊洗著臉,一邊低聲地談著。
“有點兒不對勁兒,他們沒有必要把人和孩子都回去,會不會了我們的念頭,想撕下友好的畫皮準備行搶了?”一個漢人著清澈的河水說道。
另一個漢人用生的漢語道:“他們最多隻有一千名戰士,這種營地作戰不同於草原上廝殺,他們的騎優勢不好發揮,我們人,如果夜間再襲,可能會有許多人逃走,他們自己集中人馬送上門來不是更好?”他是一名高麗刀客,也是阿德妮招攬的部下。
吞彌冷冷笑道:“不要大意,如果他們想提前送死,那我們就打一場仗。我已經大家戒備了。盯他們的舉,馬上衝鋒我們沒辦法和這些天生的戰士相比,如果不能等到我們攻擊他們的營帳,那就把他們引進來。我們每個人都通近技擊之。這一千人,很容易對付”。
河水上游下游突然冒出一羣騎士,他們騎著馬在清澈淺淺的河水中奔跑過來,水珠兒濺得漫天都是,驚起的魚兒不斷地蹦出水面,閃出一道道亮銀的茫。
吞彌笑地站了起來,友好地向那些似乎要飲馬、洗馬的牧人們點著頭,目在他們腰間的佩刀和肩上的弓箭略一逡巡,便移開了去。
他後的兩個人悄然又退了兩步,暗暗握了腰間的兵刃,當吞彌的目再次與河中那領頭的大漢相遇,雙方的眼中好象同時閃過了一抹厲。
摘弓、搭箭、扣弦,作一氣呵,而那個大鬍子吞彌和他的兩個手下作卻更快,他們就象三隻驚的兔子,連蹦帶躥地躍離了河邊,撲到了一頂營帳後去,同時示警的呼聲四起。
馬上的大漢泄氣地怒吼一聲,拔出長刀吶喊一聲,一撥馬頭向岸上衝去,那些桿繩上掛著鮮豔麗的服,那些營帳防雨效果極好,冬天防風保暖也極爲出,他當然看得出來,那些東西馬上就是屬於自己的財產了,他可不捨得破壞掉。
與此同時,陸地的幾個方向,方纔還盛待客的韃靼牧人,就象一羣羣兇猛噬的狼,揮舞著刀劍衝殺過來。能在草原上千萬裡跋涉經商的行賈,就算自己不通武藝,也必然僱傭有兇悍勇猛的護衛,他們的戰鬥力不容小覷。
然而現在他們人數、馬匹、沒有防備,駱駝四散吃著野草,也來不及布駝陣防衛,可以說這些商賈完全信任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犯草原上極大的忌,公開在自己的領地洗劫行商,這爲他們的突然襲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那些支起攤子準備做生意的商賈本來不及反抗,他們驚恐地呼喊著夥伴,飛快地向營區逃去。
韃靼人的營帳,每頂之間至隔著數十丈遠,而這些商賈爲了照顧車馬和貨,那些營帳設立得很近,彼此的間距有限,再加上爲了固定帳蓬斜斜釘立在地一條條繩索,這爲他們周旋逃命提供了機會。
烏恩其豈容他們做出反應,一聲號令,兇悍如虎的戰士們就撥馬衝進了營區。近百頂營帳象一片森林,將雙方不到兩千人的隊伍完全吞沒在其中。絆馬索、陷馬坑、突兀來的冷箭、還有吹箭、飛斧、標槍。
最聽人驚訝的是還有些和他們高大的材相比簡直就是些小挫子的人手裡揮舞著長刀,發出咿呀的怪從營帳中撲出來,還沒衝到面前就一頭栽倒在地,連滾帶爬來的飛快,跟滾地葫蘆似的到了馬下,不是砍斷馬就是刺穿馬腹,帶著一頭一臉的鮮厲鬼似的跳開。
他們怒吼著,騎在馬上了活靶子,到四面八方全方位立式的進攻,而戰馬的優勢本無從發揮,想要撥馬衝出去。廝殺混中命令已經無法下達,他們是來洗劫的,本沒有攜帶旗幟,誰會想到迎來的卻是一場屠,這時想號令上當的部下退出去,已經完全來不及了。
遠遠的,他們的婦人和孩子站在營盤看著自己的父兄英勇地衝進那些商賈的營地,不發出熱烈的歡呼。
他們的眼睛裡放著興的芒。因爲很快的,他們的親人將把他們需要而買不起的傢什、玩、華的綢、昂貴的珠寶、的地毯和鮮豔的袍給他們送回來……
一陣暖風吹來,抰著野草味、花香味、牛糞味、羊糞味,還有……腥味。
這些由各族最兇悍、最殘忍的流浪者組的掠食隊伍,人人兇大盛,就象一隻只擇人而噬的虎狼一般,不擇手段,用盡一切手法毫不手地屠著這些闖者。短兵相接、白刃加的時候,這些馬上的英雄遠非他們的敵手。
上砍人、下砍馬,如泉涌,這羣一見了就兇大發的野原紅著眼睛,發出比韃靼勇士更兇狠、更慘厲的嚎,一個個全都變了渾浴的屠夫。
幸好,吞彌做爲首領,還沒有忘記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在他的命令下,幾個通曉蒙語的部下,開始一面廝殺,一面忘形地用蒙語互相吶喊鼓勁,他們所泄的幾個地名、部落名,乃至首領的名字,已經足以讓這些拼命掙扎著想要逃出死亡陷阱的韃靼相信,這是瓦剌人派來的一羣兇手。
這羣人種組如此複雜的隊伍,也只有領地同西域和極北之地接壤的亦不剌才招募得到,不是麼?
賽馬者衝回來了,那些負責攪他人行進路線的輔助者們已經遠遠的落在了後邊,而且衆目睽睽之下也沒有人再敢做出阻礙他人行進的事。衝在最前邊的人都在快馬加鞭,向著終點的彩旗飛奔著。
崔鶯兒不負重衝在最前面,同樣是千里挑一的駿馬,同樣是萬中無一的騎,重就了決定七十里賽程最終勝利者的必要條件。隨其後的,是封雷、布和、蘇赫魯、真部的哈刺等人。
站在高臺上的白音、阿古達木等人都鬆了一口氣,暫時的勝利不要,真正要決出一個三藝第一的英雄是很難的,衝在最前邊的那位塔卡部的年輕人雖然跑了賽馬第一,但是他過於單薄的想要贏得摔跤比賽那可能麼?
至於箭,他們對自己的子侄也甚有信心,相信最後這些獲得單項勝利的人將不得不再戰一場,一場角逐王的比賽。最後選取一名各項名次皆優異在前的騎士爲王的夫婿,他們還有機會,最後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楊凌欣然站在帳前,看著遠被歡呼的牧民簇擁著紅娘子趕向王的營帳,輕笑了兩聲。銀琦王一直待在帳,陪伴著活佛和練指揮使等貴客品茶飲酒,從來不曾跑到帳外去關注賽事的進行,但是那達慕舉辦了三天,第一項比賽的冠軍出現時,的神間還是不免有些張。
聽到有人高聲稟報比賽的結果,優勝而出的人是楊英時,銀琦的肩頭一塌,明顯從張中鬆馳了下來。那脣角,也不出了一淺淺的笑意。晶亮的眸子微微一轉,瞟了活佛等人一眼,那剛剛綻現的笑便被收起了,可是兩抹彎彎的眉梢兒,還是不經意地抖擻出一片喜氣。
一位步履蹣跚的年高老者,穿著乾淨的蒙袍,走到了紅娘子的馬前,捧著潔白的哈達,唱起了優的讚歌:“廣衆聚集的那達慕,穎而出的這馬,脖頸上繫著龍王的綵帶,骨上打著經師的烙印。大象般的頭顱,魚鱗般的齶紋,蒼狼般的雙耳,明星般的眼睛,彩虹般的尾,絨般的頸鬢。每個關節長滿茸,每茸上鎏金溢彩。這匹天造地設的神駒寶馬喲,把那吉祥聖潔的鮮抹在你的頭上……”。
他對馬的姿,甚至馬的每一個部位都備加讚揚,並舉著一隻漆金小碗蘸著子抹在駿馬的腦門上,最後把馬高高舉起,敬獻給楊英。
紅娘子見他用手指頭蘸著馬在馬上胡塗抹一番,最後還把剩下的馬讓喝掉,不暗暗蹙眉。可這是草原上的風俗。許許多多牧民都在用熱誠、崇敬的目盯著看,而那些敗在手下的勇士們眼地看著手中的小碗,似乎還滿懷嫉妒。
崔鶯兒苦笑一聲,著頭皮舉起碗來,把眼一閉,將那半碗馬生生地灌了下去。草原上沸騰起來了。遠遠近近的牧民圍了一個大大小小的圈子,手拉著手兒載歌載舞,到是一片祥和安樂的氣氛。
綺韻站在帳前,微笑著看著歡樂歌舞的牧人,聽著那音樂的節奏,下微微點著,應和著他們的節奏,似乎也要隨歌而起了。這時一個人悄然走到了的後,低嗓音稟報了幾句。
綺韻肩頭隨著牧人的歌聲輕輕晃著,若無其事地轉過頭,吩咐道:“讓他們手,不要干預。等他們功之後,把艾慎帶回來,其餘的人全部消失”。
“是!”後的人影又悄然離開了。
“韻兒”。
“大人”,綺韻扭過頭,臉上換上了甜甜的笑。
“你怎麼也晃來晃去的,喜歡他們的舞蹈麼?”
“他們的舞蹈歡快灑,別有一番味道,還不錯”。
楊凌走近了來,攬著的腰著那些載歌載舞的牧民,笑道:“我倒更喜歡你跳的舞蹈,比這要好看一百倍”。
“我?”綺韻的眼珠溜溜兒一轉,詫異地道:“我有在大人面前跳過舞麼?我怎麼不記得?”
“怎麼沒有?記的那是你第一次到我府裡,住在書房,纖腰上繫著一條黃金的腰鏈,跳的那天竺舞蹈……,水爲、蛇爲骨,嫵的扭、魅的眼神,好一條要命的狐貍”。楊凌嘿嘿地笑。
綺韻咬著脣,笑盈盈地打了他一下,手掠了掠髮,眼波流盼地聲道:“那……人家今晚再跳給你看,跳給你一個人看,好不好?”
“唔!唔唔……好!”,綺韻忽然發現楊凌放在腰間的手拿開了,他的兩隻眼睛著前方,臉上的表無比的嚴肅,那下還在很認真地點著,好一副和正在談‘公事’的無恥臉。
綺韻會意地移眸橫睇,不出所料,崔鶯兒在封雷、荊佛兒等人的陪同下正從帳前經過,雖然不便過來相見,那雙澄澈如水的眸子可一直盯著這兒瞧呢。
“哼!老爺就只怕!”綺韻忿忿地哼了一聲,一邊若無其事的背起了雙手,一邊把那靴尖兒上了楊凌的腳面,肩膀向前一傾,輾呀,輾呀……
猜你喜歡
-
完結384 章

曹操之女
穿越長到三歲之前,盼盼一直以為自己是沒爹的孩子。 當有一天,一個自稱她爹的男人出現,盼盼下巴都要掉了,鼎鼎大名的奸雄曹操是她爹?!!! 她娘是下堂妻!!!她,她是婚生子呢?還是婚外子?
142.9萬字7.67 25077 -
完結556 章

全家去逃荒,她從懷裏掏出一口泉
特種兵兵王孟青羅解救人質時被壞人一枚炸彈給炸飛上了天。 一睜眼發現自己穿在古代農女孟青蘿身上,還是拖家帶口的逃荒路上。 天道巴巴是想坑死她嗎? 不慌,不慌,空間在身,銀針在手。 養兩個包子,還在話下? 傳說中“短命鬼”燕王世子快馬加鞭追出京城,攔在孟青羅馬車麵前耍賴:阿蘿,要走也要帶上我。 滾! 我會給阿蘿端茶捏背洗腳暖床…… 馬車廂內齊刷刷的伸出兩個小腦袋:幼稚! 以為耍賴他們
102.1萬字8.18 107515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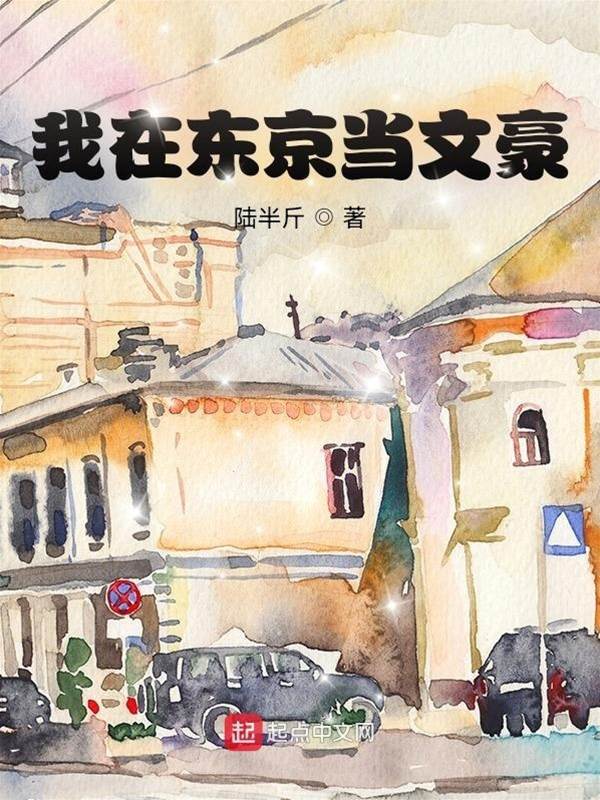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