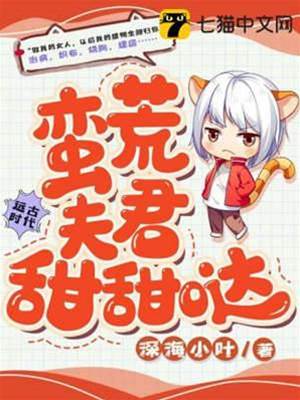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紅樓之挽天傾》 第八十三章 賈府奔走
秦可卿看著笑而不語的年,芳心之中泛起一喜。
比自家夫君還要大一二歲,但從婚前婚后的接來看,自家夫君老持重,喜怒不形于,言談舉止,待人接,完全不像個年郎。
說來,甚至覺得自家夫君,臉上似乎永遠不會有生氣、憤怒的負面緒,這種氣度雖然讓人心折,但也覺得和自己,恍若有著一層看不見的隔閡。
賈珩目溫煦看著垂眸思索的麗人,不得不說,自家這個妻子,雍容華如一株盛開的牡丹,初為人婦之后,一顰一笑,艷冶、人的風已初現端倪。
忽然也有些賈珍為何如失心瘋了一樣,竟然勾結賊寇,也要擄掠可卿。
迷心竅罷了。
賈珩目漸漸幽遠,世將臨之時,諸般好,如無權勢在,他也保不住。
更不要說江山如畫,權人。
見賈珩眉宇之間,重又蒙上一層凝重思緒,秦可卿輕笑了笑,纖聲道:“夫君,午飯時候了。”
恰在這時,蔡嬸笑著進廂房,喚賈珩和秦可卿用飯菜。
賈珩點了點頭,笑了笑,說道:“可卿,等吃罷飯,我再去寫些稿子。”
如果加班加點寫稿子,后天應該就能稿。
三國書稿,需得盡快刊行于世了,初步獲得名氣后,他已經想好了一個以白丁之,聞達于天子的計劃。
不過,這二日,還需搜集一些資料,以及實地考察京營諸軍,最近他應該都會很忙碌,至于除籍一事,再看賈家那邊的向。
秦可卿點了點頭,似能到自家丈夫心中的某種時不我待的緒,主出纖纖荑,握住了那放在幾案之上的手,道:“夫君,吃午飯罷。”
Advertisement
夫妻二人,同桌共食完午飯,業已是午后時分,秋日日煦,穿過稀疏的竹葉,窗而過,微風徐來,竹影搖曳。
秦可卿眉眼、溫寧,嫻靜而坐在屏風之畔,拿著一套賈珩平時所穿的青衫,在丫鬟寶珠和瑞珠的幫助下,以布尺丈量著尺寸。
時近深秋,一場秋雨一場寒,打算給夫君親手制一件長袍。
而木制書柜之前,賈珩坐在靠背椅上,姿筆直,微微垂首,手提筆,在黃表紙之上,凝神寫著稿子。
如非前世練槍,輒吊磚個把小時,他未必有這樣的耐心。
“用木炭筆,書寫就要快一些,當然再怎麼快,也比不上鍵盤,十指齊飛,日更過萬……前世追過的一位網文作者,甚至憤然雙開,說來都是為了養家糊口。”這些思緒在賈珩心中一閃而過。
在賈珩這邊趕稿之時,賈府中的爺們兒、太太,都在為賈珍一事上下奔走。
賈赦去尋了北靜王水溶。
賈政去尋京兆府的通判傅試。
而王夫人則是去了王子騰府上。
賈璉同樣帶上小廝昭兒、旺兒,前往京兆衙門,打探消息,試圖進大牢中聯絡賈珍。
皇城·宮苑
當天下午未時與申時之,換上誥命大狀的賈母,坐上賈府的馬車,在宮城前遞上牌子,而后在宮人引領下,步九重帝闕深宮。
長樂宮——這座陳漢定都西京之后,按著古圖復原而來的宮殿,修建得軒峻高大,巍巍壯麗,雕梁畫棟,朱檐碧甍。
此刻澄瑩如水的地板上,倒映著宮、監的影,幃幔及地的梁柱之后,銅鶴宮燈雕以花紋,薰籠之中,冰綃與沉香化而裊裊青煙,其香馥郁。
大漢皇太后——馮太后坐在一方錦緞云榻上,陳漢晉長公主、咸寧公主、清河郡主以及宮中諸太妃,陪同左右。
Advertisement
馮太后年過六旬,頭發花白,但臉頰白凈、紅潤,一雙略顯凌厲的狹長細眸,著下方的賈母,聽著其絮絮叨叨敘完,淡漠面容上,就有著幾分疏離之,清聲說道:“賈史氏,賈珍之罪,皇帝已降旨意,令有司審訊,本宮豈好改易?”
太上皇在重華宮榮養,還未駕崩,馮太后自不會開口稱什麼哀家。
賈母哀痛道:“臣婦……子侄不,辜負圣上信任,如今坐罪下獄,臣婦并無話說,但祖宗爵位丟了,臣婦百年之后,有何面見榮寧二公,還請太后娘娘恩典。”
一旁的晉長公主,秀端麗的臉蛋兒上,現出一抹玩味之。
這幾日,吩咐夏侯瑩去查賈珩,已搜集到一些訊息,匯總下來,那位小賈先生,已經定了親事,方是工部營膳清吏司郎中秦業之。
賈珩既已娶了妻,尚郡主自是不用提了。
“嬋月這孩子……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啊。”看著一旁自家兒,正拿著一面銅鏡,映照在軒窗之上的,反向大殿梁柱,玩得不亦樂乎,晉長公主撇了撇,嫣然明眸中滿是寵溺與無奈。
此刻,李嬋月拿著銅鏡,一雙明眸中滿是好奇之,似在疑為何鏡子能借得太芒,反到房梁的暗影。
看著老淚縱橫的賈母,馮太后容頓了下,道:“皇帝褫奪賈珍之爵,并未說襲爵之人,你賈家倒是可另擇……”
賈母仰起頭,蒼老目中帶著期冀之。
“母后,此事關涉朝廷法度,皇兄已有決斷,又剛剛下了旨意,母后……”晉長公主艷麗的玉容上,笑意嫣然,眨了眨眼,聲說道。
賈母:“……”
馮太后面頓了下,清聲道:“也是此理,賈珍其罪,既有司推鞠,詳定其罪,那爵位一事,還需再看賈珍究竟犯了何罪,如不是什麼大逆不道之罪,想來也不會牽連寧國之爵。”
說完,心底輕輕嘆了一口氣。
兒轉圜和自家兒子關系的好意,豈會不知?
只是煦兒剛強,待下峻刻,因不法之事而除寧國之爵,不知上下如何議論,還有重華宮中的……
一旁的咸寧公主,清冷玉容上現出一抹異,看了一眼自家姑母,暗道,怪不得父皇對姑母禮讓三分。
祖母從來都是強勢之人,從小到大,連這個正派孫兒,都不敢親近,但在姑母面前,卻如春風化雨,歡聲笑語不斷。
至于母后,除卻晨昏定高樂宮都不讓多待。
賈母臉黯然,看了一眼晉公主,心底有些惱怒,覺得求錯了地方,或許應該去求一求重華宮的太上皇?
榮禧堂中,燈火如晝,人影闌珊,丫鬟、仆役侍立左右,連大氣都不敢,唯恐被遷怒到。
下午之時,大老爺從外間回來,一個不長眼的小廝,沖撞了下,就讓人捆縛了下去,當場打得半死。
此刻,賈母、賈赦等人再次濟濟一堂。
賈赦急聲道:“母親,太上皇和皇太后怎麼說?”
賈母嘆了一口氣,長吁短嘆道:“要看珍哥兒的罪過大小,如果不是謀逆之罪,”
賈政道:“聽傅試說,京兆尹的許德清,是鐵了心要辦珍侄兒的案子,珍侄兒已招供了。”
賈珍何時過大牢,住了一夜,只覺五如焚,又驚又懼,又加之許廬將崇平帝降旨除爵一事宣告于賈珍,而后即刻用刑。
刑方列,賈珍就全撂出來。
“招供了?”賈赦氣得將手中的茶盞仍在地上,怒道:“珍侄兒怎麼這般糊涂!”
賈母道:“這是怎麼?”
賈赦憤憤道:“母親,我們被誆了,那許廬也沒有直接證據,說是珍侄兒勾結的賊寇,只要將事全推至賴升那狗奴才頭上,珍侄兒未必不能全而退!”
似乎擔心賈母不信,道:“這是王爺所言,那許德清,酷吏而已,仰仗圣眷胡作非為,屈打招,只要珍侄兒抵死不認,我們再反辦他一個用法峻刻,”
這是北靜王水溶給他分析過的,他深以為然。
賈政嘆了一口氣,說道:“圣上已知其惡,再是掩耳盜鈴,又有何用?”
賈母、王夫人、賈赦:“……”
賈赦輕哼一聲,說道:“若是傅試疏通獄卒,傳遞有無,珍侄兒何至于在獄牢中無而招供?那傅試為京兆尹通判,連這些手段都沒有嗎?”
這就是在晦地指責賈政了。
“夠了!”賈母一拄拐杖,蒼老面容上涌怒,道:“咱們自家人知自家事兒,珍哥兒先前就和賈珩有爭執,兩個人鬧得風風雨雨,瞞過誰去?圣上都降了旨意,再抵死不認,難道要欺君嗎?”
圣上金口一下,定下賈珍有罪,革爵待罪,然后你抵死不認,還要讓圣上收回旨意?
這時代,并不講什麼程序正義,縱然是后世推崇程序正義,在證據裁判規則上,也是自由心證。
有罪無罪的證明標準,自然是排除合理懷疑,嚴格排除非法證據,可這樣的刑訴程序,哪怕是后世,也沒有得到完全貫徹,遑論如今的陳漢?
圣心獨斷,到天上都到頭兒,哪還有什麼反復?
賈赦臉一白,目閃了閃,狐疑道:“可是王爺……”
北靜王水溶總不可能要坑他賈家吧?
不會……
一旁的賈璉,輕聲道:“想來王爺認為此事還有罪的余地,珍大哥還能救出來,但圣旨措辭嚴厲,圣上龍震怒。”
北靜王是賈家,當然不會害賈家,只是理方式不同,而且北靜王已經到一來自崇平帝的惡意。
賈赦面帶憂,問道:“母親,現在當如何?”
賈母嘆了一口氣,說道:“不管如何,都要保住爵位。”
賈珍犯了罪過,已經不見容于天子,但祖宗傳下來的爵位不能丟,寧國還有子嗣可以承爵。
榮禧堂中,賈政、王夫人,邢夫人,姐聞言,都是面微。
說來也奇,東府承爵之人賈蓉、尤氏此刻俱不在,畢竟,一個不更事,一個小門小戶出,在外有鋸葫蘆之稱。
賈母讓二人回去謹守門戶,反而是西府里的人著急忙慌在奔走。
賈母看向王夫人,急聲問道:“寶玉他舅舅怎麼說?”
王夫人默然了下,凝聲道:“舅老爺明日陛辭圣上,說會向圣上提東府之事。”
賈赦聞言,心下松了一口氣,說道:“由舅老爺出言,北靜王爺再從中說,道想來東府里的爵位應能保得住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85 章

邪情少主
收女將,俘美人,建後宮!他穿越異世成為名門中唯一的男人,身負"傳宗接代"的任務!獨守空閨的王妃,他毫不猶豫的下手;刁蠻潑辣的蘿莉,他奮勇直前的追求!我本邪情少主,笑看福豔雙至。運籌帷幄馬踏乾坤,縱橫四海所向披靡。且看現世邪少異世打造極品後宮的傳奇故事……
193.5萬字8 28349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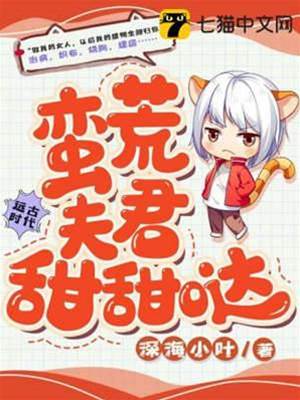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6273 -
完結753 章

帝尊嬌寵:妖孽娘親鎮九天
楚千離,堂堂時空管理局退休大佬,卻一朝穿越成為了臭名昭著的相府廢物嫡女,被未婚夫和妹妹聯手陷害,毀掉容貌、與人茍合、名聲喪盡。楚千離冷冷一笑,退休后,她是一心想要當咸魚,可誰在成為咸魚之前,還不是個深海巨鯊?容貌丑陋?退卻傷疤、除掉胎記,絕世容貌驚艷天下!廢物粗鄙?手持金針、醫毒雙絕,技能點滿深不見底!未婚生子?帝...
132.1萬字8.18 198709 -
完結1045 章

徒兒,為師真的不會修仙
沈天穿越到星辰大陆,却无法修行。 砰... 一声轻爆声。 擅闯进沈天屋里的大修士死掉。 众徒弟惊呼:“师傅!还说你不会修仙?” 沈天懵逼的看着死掉的大修士,无奈道: “徒弟,为师真的不会修仙!”
195.1萬字8 186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