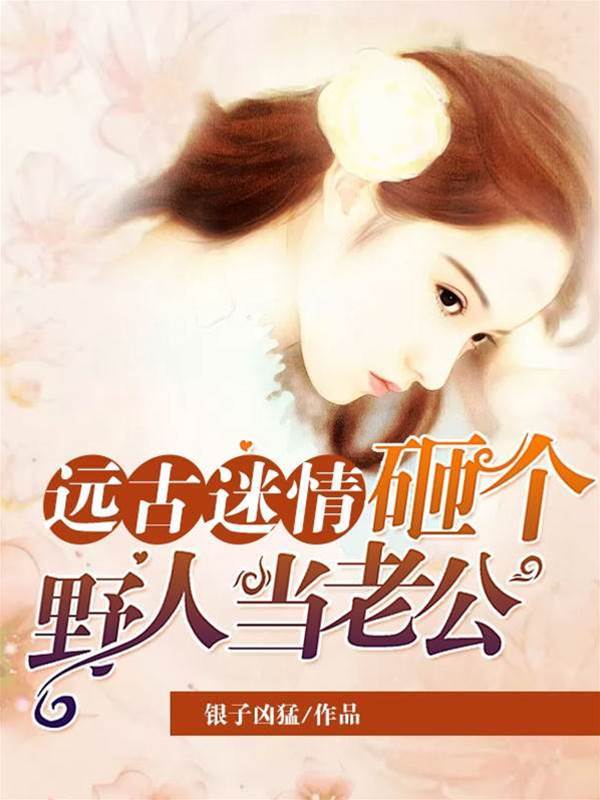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榜下貴婿》 第41章 歸家(修)
崇明堂燈火通明, 三皇子趙景然、尚書令陸文瀚連同剛到松靈書院的開封府尹,三人同時夜審張松,陸徜、宋清沼與明舒三人同堂回話。
人贓俱獲的張松無可抵賴, 頹然萎頓在地, 因為上被剝得只剩下一件薄薄的染里, 他凍得雙手環瑟瑟發抖, 牙關打戰地回答堂上三人的審問。
大致的犯案過程與陸徜三人所猜差不多。張松先以給三皇子獻詩為由誆騙楊子書,楊子書果然上當,同意他的計謀。在今日天未亮時,楊子書趁著無人潛環濤館,并將門窗關閉,藏在館中等待, 而張松則去與眾人一起去山門前迎接三皇子等人,直到三皇子從崇明堂出來, 帶著眾書生走到千書樓外, 他的殺人時機到了。
“他們滯停在千書樓外, 注意力都在三殿下上。我先假裝腹疼,走到樓外的石塊上坐下, 以此造前面人的錯覺, 讓他們覺得我在,只是沒有站在正后方, 而是坐在附近。我再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 溜進千書樓和聽月閣間的暗巷。”張松眼神木然地說著經過。
他進暗巷就開始,將外袍與中全都下后藏在窗外, 而后開窗翻進環濤館, 拿著預先到的袖箭箭筒下手。
“袖箭是前一天夜里, 我和彭國跟著楊子書去找唐離時, 趁著他們爭執之間悄悄到手的。我把箭筒與箭簡分離,預先把箭筒扔在竹林里,造兇手從竹林逃離案發現聲的假相,嫁禍謝熙,而我則用箭簡扎在楊子書的頸間……一下……兩下……噴得到都是。”張松說著說著,眼神變得郁瘋狂,仿佛上干痼的染到眼里,手也抬起落下,仿佛在環濤館,他一手捂著楊子書的,把人按在桌上,一手把箭往楊子松脖頸狠狠扎下。他的力氣從沒那麼大過,他心里也從沒那麼痛快過。
Advertisement
殺完人,他順手抓起書案旁邊的手稿拭手上臉上的跡,而后小心翼翼翻出窗戶,一邊套上下的裳,一邊飛快按原路跑回千書樓外。
早春尚冷,他特意穿得比別人都厚實,兩件夾棉中一件厚外袍,而山中風大,出的一點腥味,被風吹吹就散了,他又站在最后,其他人都不搭理他,沒人注意到他的異常,他回到千書樓的時候,前面那人甚至沒發現他的消失。
“他們都不理我……因為我是楊子書的爪牙……幫著楊子書欺凌他們,但我也不想這樣,是楊子書我的。”張松說著說著,又嗚咽而哭。
他本只是松靈書院普通的學生,家境平平,父母砸鍋賣鐵供他從小讀書,所幸他頗為爭氣,苦讀數年考了松靈書院,本以為苦盡甘來,再等兩年也秋闈春闈殿試金榜題名,他也能出人頭地,卻不幸遇上楊子書。楊子書為人囂張,在院中橫行霸道,尤其喜歡挑家境差的學子下手,張松被他打過罵過辱過,一開始眾人還同張松,可是后來,為了逃避楊子書的欺凌,張松選擇為楊子書的爪牙,以換取平安。
可即便這樣,楊子書平日里也沒打罵他,而書院里的其他學子又因為此事,對他的同漸漸變憎恨,全部疏遠了他,他孤立無援,飽痛苦。
恨意,就在這樣的日子里逐漸滋生。
代完一切后,張松掩面伏地而泣。
“他既如此作惡,你們何不向書院師長們陳?”待張松緒稍緩,陸文瀚方開口問道。
“我們說過了,然而沒用,楊子書家里有錢,買通了平時管教我們的幾位先生,先生們對他的惡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們出貧微,靠著書院資助在這里學習,又怎敢得罪他們?”張松垂頭道。
Advertisement
松靈書院并非學,能考進來的學生多憑本事,很多都出寒門,像宋清沼這樣世家出卻也憑真材實學考的,之又。
趙景然聽完因果后,沉默良久,方道:“此案吾會如實上奏父皇,包括書院結私貪腐之事,一并徹查。百年松靈,為國培育良才,本該是一方凈土,卻地獄。還有你,張松,雖說你有千般苦衷,但也不是你殺人嫁禍的理由。家有家規,國有國法,法不容,不論殺人亦或做偽證,皆國法。各位,引以為戒。”
他落下結語,揮袖出了崇明堂,將余事給開封府。
明舒聽完張松所言心百味雜陳,正想喊陸徜一起離開,卻聽陸徜忽又開口:“張松,你不是第一次下手殺楊子書吧?”
張松緩緩抬頭,出一迷。
“明禮堂。”陸徜提醒道。
他迷的目方出了然:“是啊,明禮堂本可借那塊匾額神不知鬼不覺砸死楊子書,可惜,被你破壞了。”
明舒詫異地睜大眼眸向陸徜。
陸徜便向解釋:“那天楊子書經過匾額時,被他住了。”這是他最初就懷疑張松的直接原因。
“原來如此。”明舒恍然大悟,又隨口問張松,“可你又怎麼知道匾額要掉落的?”
張松卻閉上,眼里現出三分迷茫,很快竟笑了:“無意間……聽人說的。”
那個“人”字發音他咬得古怪。
明舒下意識問他:“是誰?”
“忘了。”張松這次卻想也沒想就回答,跟著閉上眼,拒絕再回答他們的問題。
明舒蹙起眉來,總覺得哪里有些說不出的古怪,但開封府的捕快卻已將人押下,而陸徜也催離開。
“我想單獨見見謝熙與唐離,可以嗎?”明舒向宋清沼,他和三皇子,也許能幫上忙。
但還同到宋清沼回答,正好和開封府尹并肩出來的陸文瀚就開口了:“你見他們做甚?”
“陸大人,民想替人問他們幾句話,和這樁案子無關。”明舒道。
唐離和謝熙因為做偽證,如今也被單獨收押在崇明堂的房間中。
陸文瀚似乎對特別寬容溫和,也沒細究原因,朝開封府尹說了兩句話,便有衙役前來帶明舒去見二人,陸徜知道要做什麼,便在崇明堂上等著,被陸文瀚抓著說話。
————
明舒先見謝熙。
他被關在小小的靜室,室中無榻,只有簡單的桌椅,桌上點著盞燈,他坐在桌前發怔。
明舒向開門的守衛道過謝,這才進屋。
聽到聲音,謝熙已經知道來人是誰,他已經冷靜,也聽說陸徜、宋清沼與陸明舒三人抓到真兇,替他與唐離洗清嫌疑了。
“謝謝。”他靜道。
明舒發現,只要不牽涉唐離,他就仍表現得像個謙謙君子。
“不必言謝,我不是為了幫你才查的案子。”明舒站在門前問道,并不往房走。
“都一樣,終究是為我和阿璃洗刷嫌疑。”謝熙緩緩起,面無表地作揖,“多謝。”
明舒隨他行禮,直接問道:“你喜歡唐離?”
謝熙頓了頓,目落在桌面的斑上。
“是。”
終于可以不必藏著掖著了。
“我與阿璃很小就認識了,如果蘇家沒有倒,與我定親的子,應該是阿璃。蘇家被抄,阿璃被牙發賣,我本以為此生再見不到,誰曾想竟在松靈書院遇上了。”
謝熙緩緩開口。
做為罪臣兒,蘇棠璃被判牙發賣,因蘇父與徐山長私甚好,流放前曾懇求徐山長救,徐山長便讓人暗地里將蘇棠璃買下,又怕人發現后詬病,就命蘇棠璃改作男裝,當男孩收養在膝下。
山長與師娘曾經有過一個兒子,六歲左右不幸早夭,后來便再沒有過孩子,師娘見了扮男裝的小棠璃,惻之心大,時棠璃又乖巧可憐,十分討師娘喜歡,因此夫婦二人才瞞過眾人,把蘇棠璃放在邊教養十年,也給了謝熙與重逢的機會。
“我第一眼就認出了。因為的世,我替瞞著眾人,偶爾遇到難,我能幫就幫,就這麼和識了。”
最初,也只是朋友那般相著,抵不住時悠悠,謝熙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心的,發現時已經晚了。
“可你和縣主也很早就定親了。”明舒問他。
“我知道。我和阿璃不可能,我們間清清白白,能和像朋友這般相下去,對我來說就夠了。”
“清清白白?朋友?”明舒微笑,含嘲帶諷,“你心已越軌,談何清白?況且你真分得清朋友與人間那條線嗎?”
以友為名,行之舉,哪里清白了?
“那你想要我如何?我會娶聞安,一輩子尊敬,還不夠嗎?這樁婚事兩家長輩安排,我與聞安并無,有些東西,我控制不了。”謝熙道。
“你不止對縣主沒有,我恐怕你連最基本的尊敬,也做不到。但凡你心中為聞安,為你的父母家人想過半分,你都做不出替唐離頂罪的荒唐事來,如今卻還對我說會一輩子尊敬?”
明舒慢條斯理道,質問的每個字都清晰落他耳中。
謝熙無言以回。當時頂罪確實沖,那日早晨他與唐離并未見過面,但由于此前和楊子書發生的種種矛盾,再加上那只袖箭,他也懷疑是唐離下的手,又聽陸大人提議刑,這才失去冷靜。
“謝熙,你心中明白,縣主愿意嫁你,并非只因兩家關系,也喜歡了你十年。你既不能快刀斬麻斷去你與唐離意,又無法排除萬難爭取你與唐離的婚事,卻只能踐踏縣主之,拿著所謂尊敬的可笑謊言,騙一世幸福。我……瞧不起你。”
明舒言盡于此,轉離去。
來見謝熙,是想替縣主最后再問謝熙一次,問他可有苦衷,然而,什麼都沒有。
————
唐離關的房間就在謝熙對面,同樣是一桌一椅一盞燈。
燈火微弱,照著桌前清秀的臉龐。
明舒進來時,唐離也正看著燈發呆,雙眉微擰的模樣似乎滿心愁緒。
“唐……蘇娘子。”明舒剛開口就想起的真名,馬上換了稱呼。
“我唐離吧,這名字聽了十年,我習慣了。”唐離轉過頭,仍是男子的舉止,除了面對謝熙,似乎很出兒的模樣。
明舒對的第一印象,是向寡言且小心翼翼的年。
“你可知謝熙已與縣主定親?”明舒問道。
“我知道。”唐離點點頭,苦笑解釋,“我與世子之間,并無私,你們誤會了。”
“可滿堂都看到謝熙為你頂罪,這沒有私?他為了你手毆打楊子書,這沒有私?你別告訴我你心中什麼都不知道。”明舒又問。
唐離沉默了,良久才道:“有如何,無又如何?我與世子終究不能在一起,說這些又有何意義?”
語畢抬頭,雙眸通紅,淚水將落,真真可憐至極。
明舒蹙蹙眉——并沒為難唐離的打算,只是想替聞安會會。
以聞安縣主的脾氣,恐怕會很想知道自己的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但從今晚來看,這唐離似乎只是個膽小懦弱的人。
明舒剛剛和謝熙說了一番話,心里正煩,不愿再費舌,便搖著頭打算離開。
轉之際,忽然想起剛才陸徜問張松的問題。
匾額損壞之事,是誰告訴張松的?張松沒回答。
林大娘提過,匾額去歲已經報修,卻因寒冬歲末而遲遲沒有工匠來修,按說如果匾額有砸落的風險,那麼即便一時半會修不了,也該將匾額取下,以防萬一,但是松靈書院并沒有這麼做。
這是何故?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報修的登記出了問題。
明舒記得,唐離幫師娘做些文書登記謄抄的活計,是可以接到書院破損品的報修記錄,匾額掉下時,亦在旁邊……
思及此,明舒眉頭頓皺,霍然轉。
后,唐離正半垂頭對著桌案上的燭臺,出食指與拇指燭上火苗。并沒直接掐滅火苗,完松開,再,如此往復著,屋里火便明明暗暗,照得的臉也虛虛實實。
那張臉上沒有表,但看得出很輕松,游刃有余的玩火,與先前楚楚可憐的模樣判若兩人。
“匾額之事,是你告訴張松的?”明舒被自己突如其來的想法震驚。
“你說什麼,我不懂。”唐離聽到的聲音轉過頭,角勾起一弧度,帶著些微挑釁,像毒蛇輕吐的舌信。
明舒卻順著這思路往下,又道:“袖箭……是不是你故意讓張松盜走的?”
唐離的笑又大一些,出幾顆潔白的牙:“有證據嗎?有證據你可以告訴三殿下。”
“你也不謝熙對嗎?”明舒卻繼續問道。
按這個思路推下去,唐離早已知道兇手是誰,可在堂上面對謝熙的頂罪時卻什麼也沒說,只利用他逃避刑罰,本不謝熙。
這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如果你一定要問我對世子的,我當然是鐘于他的。”唐離一反常態地輕松,仿佛在逗著明舒。
“蘇棠璃,你到底想做什麼?”明舒走近,冷道。
如果只是與楊子書有仇想借刀殺人,那說得通,但似乎的目的并非如此簡單。
“這話應該是我問陸娘子才對,你到底想要我承認什麼?”唐離反問。
明舒攥攥拳——一切只是的猜測,一點證據都沒有,連也不知道要唐離承認什麼。
看唐離的反應,再問下去也沒意義,明舒轉就走,只是臨出門之時,唐離陡然掐滅燭火,室陷黑暗,整個人也遁其中。
只有聲音,從黑暗中幽幽響來:“陸娘子,你可試過家破人亡的滋味?如果你被害得家破人亡,你報不報仇呢?”
“家破人亡”四字,仿如一桿長箭,陡然穿心。
明舒只覺口一痛,似乎被說中了什麼,腦中乍然全空,木然踏出門去。
唐離最后那句話,沒聽到。
“我們,京城再見吧。”
————
陸徜正在外邊等明舒,一邊等一邊回答陸文瀚源源不絕的問題,宋清沼也沒走,正借故留在崇明堂,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明舒出來時,陸文瀚新的問題剛剛出口,陸徜還不及作答,就見明舒木木地出來,與進去時大不相同,他蹙眉看了兩眼,連陸文瀚的問題都顧不上回答。
“罷了,也折騰了整日,帶你妹妹回去休息。”陸文瀚見他失神并沒怪罪,反揮手讓他離開。
陸徜告罪后快步走到明舒邊,那邊宋清沼也跟了過來,想和打個招呼。
猜你喜歡
-
完結158 章
歡天喜帝
泱泱亂世下,一場王與王之間的征戰與愛。他是東喜帝,她是西歡王。他叫她妖精,她稱他妖孽。他是她的眼中釘,她是他的肉中刺。他心狠手辣霸氣橫溢,她算無遺策豔光四射。相鬥十年,相見一面,相知一場,相愛一瞬。是他拱手山河博卿歡,還是她棄國舍地討君喜?世間本有情,但求歡來但尋喜。
43.2萬字8 8887 -
完結407 章

重生后成了皇帝的嬌軟白月光
(重生1V1)論如何從身份低微的丫鬟,獨得帝王寵愛,甚至於讓其解散後宮,成為東宮皇后,自此獨佔帝王幾十年,盛寵不衰。於瀾:“給陛下生個孩子就成,若是不行,那就在生一個。”反正她是已經躺贏了,長公主是她生的,太子是她生的,二皇子也是她生的,等以後兒子繼位她就是太后了。至於孩子爹。“對了,孩子爹呢?”慶淵帝:“……”這是才想起他。朕不要面子的嗎? ————於瀾身份低微,從沒有過攀龍附鳳的心,她的想法就是能吃飽穿暖,然後攢夠銀子贖身回家。可,她被人打死了,一屍兩命那種,雖然那個孩子父親是誰她也不知道。好在上天又給了她一次重來的機會。既然身份低微,就只能落得上輩子的下場,那她是否能換個活法。於瀾瞄上了帝都來的那位大人,矜貴俊美,就是冷冰冰的不愛說話。聽說他權利很大,於瀾想著跟了他也算是有了靠山。直到她終於坐在了那位大人腿上,被他圈在懷裡時。看著那跪了一地高呼萬歲的人,眼前一黑暈了。她只是想找個靠山而已,可也沒想著要去靠這天底下最硬的那座山……完結文《權臣大佬和我領了個證》《向隔壁許先生撒個嬌》
59.5萬字8 278254 -
完結1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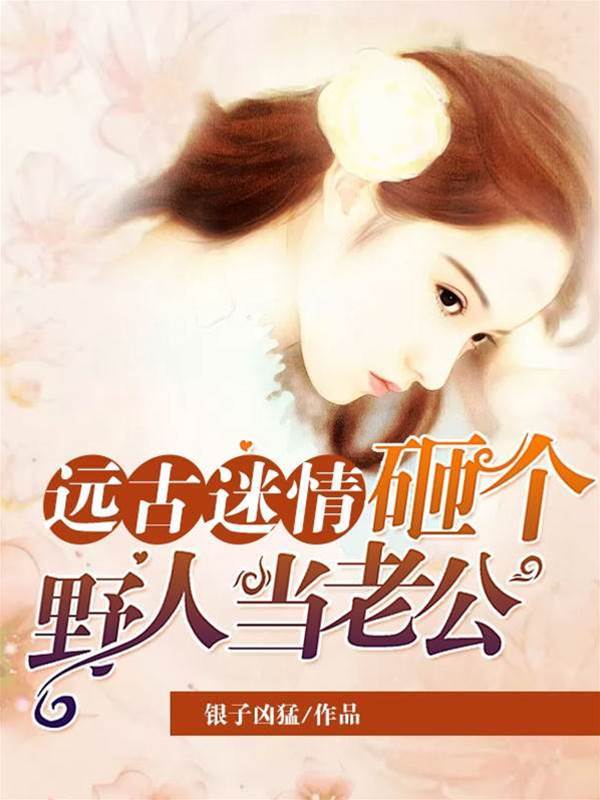
遠古迷情:砸個野人當老公
穿越到原始深林,被野人撿了 野人很好,包吃包喝包住,然而作為代價,她要陪吃陪喝陪睡! 于是見面的第一天,野人就毫不客氣的撕了她的衣服,分開她的雙腿 作為報復,她將野人收集的皮毛割成一塊塊,將他抓來的兔子地鼠放生,生火差點燒了整個山洞 然而野人只是摸摸她的小腦袋,眼神溫柔,似乎在說,寶貝,別鬧了!
41.9萬字8 13085 -
完結889 章
嫁給渣男死對頭
前世,沈鸞那寒門出身的渣男夫君給她喂過兩碗藥,一碗將她送上了權傾天下的當朝大都督秦戈的床,一碗在她有孕時親手灌下,將她送上了西天,一尸兩命。兩眼一睜,她竟回到了待字閨中的十五歲,祖母疼,兄長愛,還有個有錢任性的豪橫繼母拼命往她身上堆銀子。沈鸞表示歲月雖靜好,但前世仇怨她也是不敢忘的!她要折辱過她的那些人,血債血償!
167.1萬字8.18 78062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515 -
連載573 章
侯府雙嫁
葉家心狠,為了朝政權謀,將家中兩位庶女,嫁與衰敗侯府劣跡斑斑的兩個兒子。葉秋漓與妹妹同日嫁入侯府。沉穩溫柔的她,被許給狠戾陰鷙高冷漠然的庶長子;嫵媚冷艷的妹妹,被許給體弱多病心思詭譎的嫡次子;肅昌侯府深宅大院,盤根錯節,利益糾葛,人心叵測,好在妹妹與她同心同德,比誰都明白身為庶女的不易,她們連枝同氣,花開并蒂,在舉步維艱勾心斗角的侯府,殺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最后,連帶著不待見她們二人的夫君,目光也變得黏膩炙熱。陸清旭“漓兒,今夜,我們努努力,再要個囡囡吧。”陸清衍“寒霜,晚上稍稍輕些,你夫君我總歸是羸弱之身。”
100萬字8 3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