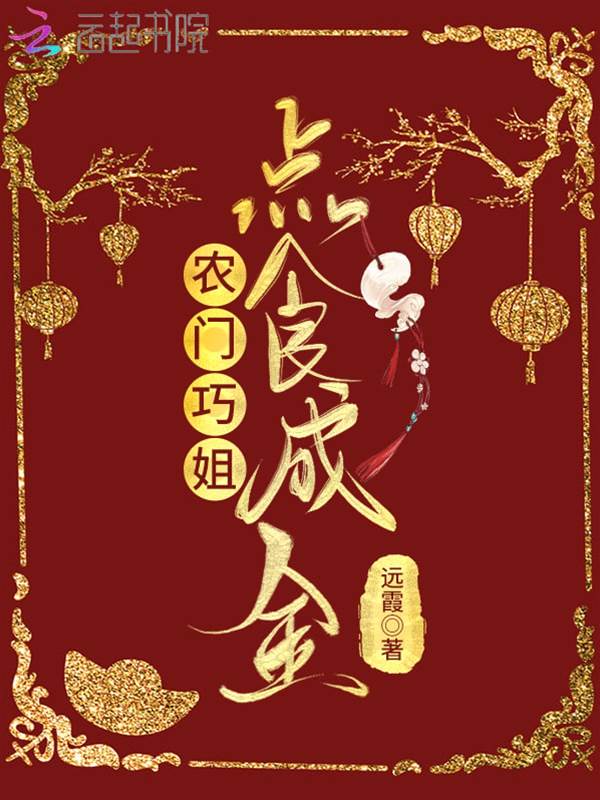《邊關小廚娘》 第106章 第 106 章
且說安夫人被安永元一路扛上了馬車, 他臂力驚人,在軍中也就封朔能與之一戰,安夫人哪里掙得了。
多日的委屈和心酸一腦發出來, 安夫人在他肩頭哽咽得不能自已。
等上了馬車,安夫人頭一句話便是:“將軍既不信我,也不愿再看到我,今日還來這一遭作甚?不若讓我死在這湖里,還安家門楣一個干凈!”
安永元一手按著, 是一個完全不允掙扎的姿勢, 下頜線繃得死, 似在強忍著怒氣, 沉聲吩咐車夫:“回府。”
兩位主子還在斗氣,安夫人的丫鬟也不敢到里邊去, 就跟車夫一道坐在了馬車外邊。
馬車在一片泥濘的道上走遠。
安夫人還想掙扎, 安永元輕易就將人鉗制住,他臉上那道疤看著本就兇悍,眼底有浮現, 更人不敢與之直視,他說:“莫鬧。”
安夫人看著這張悉的面孔, 眼淚簌簌直掉:“將軍以為我是在做戲麼?您不想看到我, 連祖母生辰都不愿回來。我這輩子,出生沒得選,為戲子沒得選, 被人買走也沒得選, 將軍若是當初沒有救我,任我一刀結果了自己,這輩子也就一了百了。”
“將軍于我有恩, 我這輩子都念著將軍的好。您若只是厭棄了我,我自知份低賤,萬不敢怨將軍,可我當真沒做過對不起將軍的事。您罵我不知足也好,不知也罷,我是真的想跟將軍好好過下去,我唯一跟陸家有過往來的只有那封信,我想跟陸家徹底劃清界限啊……”
安夫人說著這些掏心子的話,一刻也不敢停,生怕安永元厭惡聽這些,不等說完就走人,“我是個活生生的人,我知道誰對我好,我也會貪心,想一輩子跟著將軍,相夫教子……”
Advertisement
想起那個未出世的孩子,安夫人下意識了平攤的腹部,眼淚流得更兇,
“我知道今日是我胡鬧了,可將軍您也只有今日才會回來,過了今日,我便是想見你一面都難。一開始我只是想用這個法子見您一面,跟您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可站在雁湖邊上的時候,我就想,直接跳下去好了,我嫁給將軍后,的清福已經夠多了,該知足的。待我去后,將軍另娶佳婦,日子必然也過得和和……唔……”
安夫人話還沒說完,就被人用力捂住了,安永元手勁兒大,捂得安夫人口鼻生疼。
他眼中的比起先前更多了些,一眼看去只覺他雙目猩紅,恍若一頭惡。
安夫人說的那些話,每一句都像刀子般在他凌遲著他的心。
安永元說:“我若早知道你是陸家的人,你從山賊窩里出來要自縊,我絕不會攔你。”
安夫人聽他這般說,雙肩著,哭得無聲,眼底已全然黯淡了下去,只剩一片死灰般的絕。
——他終究是不肯原諒,也不信,覺得當初遇上山賊,也是為了跟他有集而故意安排的。
安夫人心口痛得有些麻木了,安永元替一點點干凈臉上的淚痕,他指腹糲,還有皸裂的大口子,硌得面頰有些疼,但一句話沒說,只是眼淚跟斷了線的珠子般一直往下掉。
迄今還記得,被他從山賊手中救下,險些辱要尋短見時,他攔下,怕再輕生,故意說:“安某貌丑,求妻不易,姑娘若不介意,可嫁安某為妻。”
如今看來,這一切錯誤的源頭,便是從那時開始的吧。
安夫人哭得太久,雙眼紅腫得厲害,勉強咧了咧角,出一個苦笑:“是妾對不住您。”
Advertisement
安永元抱抱得很,臉上那道疤因為繃而顯得有些猙獰:“可這世間沒有早知道,蕓娘,你現在是我安永元的妻。”
安夫人眼睛已經干得流不出淚來了,聽見那句“是我安永元的妻”,卻還是哽咽出聲。
安永元拂去眼角的淚珠:“從前是我不對,但往后的日子還長,蕓娘,我們好好過。”
***
姜言意一行人擔心出什麼意外,趕著馬車去追安家的車,到了一路口,卻瞧見了安夫人的丫鬟。
丫鬟在路邊被凍得直跺腳,看到們的馬車,瞬間笑逐開:“楚姑娘,可等到你們了!”
姜言意聞聲開車簾問:“你怎一人在此?你家夫人呢?”
丫鬟雖被凍得瑟瑟發抖,可臉上的笑就沒收起來:“將軍接夫人回府去了,特地讓我在這里等您,說今日多謝您,改日再登門拜訪。”
楚淑寶和楚嘉寶原本也有些擔心,聽見丫鬟的話,瞬間從車簾子底下出腦袋來,問那丫鬟:“你家夫人跟你家將軍和好了?”
丫鬟樂得直咧,用力點了點頭。
楚淑寶趕雙手合十念叨:“真是菩薩保佑,皆大歡喜皆大歡喜!”
姜言意得到這個答案也松了一口氣,對那丫鬟道:“你上車來,我們載你回城。”
丫鬟忙說不用,“多謝楚姑娘好意,我去前邊路口攔個牛車回去就。”
楚淑寶道:“這冰天雪地的,到雁湖這邊來的人,你攔牛車還不知要等多久呢,上來吧,反正也就順路的事。”
丫鬟連連道謝,這才上了馬車。
*
如意樓開張第一天,雖有幾場意外,但好在結果都不錯,生意也紅火得很。
從前姜言意只知道花錢如流水,接下來幾天的好生意還是頭一遭讓會到什麼“賺錢如流水”。一樓的大堂專門用來辦酒席,就沒空出來的時候,隨著酒樓名氣越來越大,接待尋常客人的二樓桌椅都不夠用了。
姜言意又定了一批桌椅,把閑置的三樓也辟出一塊地方,用于生意好時臨時待客。
安夫人在西州沒什麼閨中友,因為上次姜言意幫的事,同姜言意親近,得閑就來如意樓找姜言意。
姜言意從口中得知,安永元趁著安夫人養病,把府上家仆里里外外都整頓了一通,給提拔了不心腹,現在整個安家的下人都看清了主子的態度,沒人再敢輕慢安夫人。
只是安夫人時不時又故意刁難兒媳,甚至大冷天的非要安夫人用冷水給洗褥子。
安夫人子是,但也有自己的小聰明,洗完褥子當天就大病一場。
安永元回家見發妻臥病不起,發了好大一通脾氣,不僅以安夫人曾落水寒、傷了要調養為由,不讓安夫人再去安夫人跟前伺候,連晨昏定省的請安都免了,倒是把安夫人氣得夠嗆。
楚淑寶姐妹聽著這些家長里短的事,偶爾也會慨一兩句,說安永元看著兇神惡煞,卻是個會疼人的,只盼著將來挑夫郎也能挑到這樣的。
轉眼就是臘八,俗話說“過了臘八就是年”,街頭巷尾賣年貨的多了起來。
西州府衙放出風聲,從臘八節開始,一直到年后元宵節,每天都會在城南施三大桶粥。
姜言意之前想的法子奏了效,有了一個贊揚封朔的人,就有第二個,從南邊逃難過來的人,把南邊的慘烈一說,再對比西州城窮苦百姓還能領府的粥喝,普通人也能安安心心過個好年,對封朔的贊揚聲很快就在民間掀起軒然大波。
只不過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逃荒的百姓,哪怕西州城嚴進嚴出,城百姓還是日漸增多。
西州糧草本就艱難,全靠著從渝州走水路運過來。樊威和信王起了訌,現在南邊牽制不了朝廷太多兵馬,朝廷開始集中火力攻打渝州和渝州下游的糧道。
西州城還沒有任何征兆,但姜言意明顯覺到戰事在一步步。
封朔每天都和幕僚們商議到深夜,姜言意記不清自己有多久沒見過他了。
如意樓的生意步上正軌,面坊的生意也超乎了姜言意的想象。
方便面在關外的商隊中賣得極好,邴紹甚至提議姜言意得擴建面坊,只不過被姜言意否決了。
楚昌平給姜言意了風聲,不久后府會嚴格管控糧食的進出,城的糧食只能賣給城百姓,不能再外銷。
現在西州的僵局在于,西州是靠封朔的另外兩塊封地禹州和衡州供起來的,糧草是西州的一大命脈,銀子也是。
戰事耗得越久,銀子的花銷就越多。
以三大州府同整個大宣朝的國庫耗,肯定耗不過,所以封朔反了之后,才一直盤踞西州,沒直接同朝廷拼。
信王和樊威不要名聲,沒錢沒糧了打到哪兒搶到哪兒,封朔卻不能。
姜言意冥思苦想了好幾天,還是沒能想出個盡快賺大錢的法子。
郭大嬸見愁得厲害,寬:“打仗的事自有王爺邊的幕僚們出主意,東家別愁壞了自個兒的子。”
姜言意嘆了口氣:“面坊的生意不能往外邊做,接不了大單子,也賺不了幾個錢。嬸子,您說西州做什麼生意能賺出個金山銀山來?”
郭大嬸好笑道:“這地方種莊稼莊稼不好,養牛羊,牛羊冬也缺草,您要想賺金山銀山,除非有人肯買這地里的泥。”
這話可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姜言意一改之前的頹態,拿起桌上一個上釉漂亮的瓷碗,喜不自:“對啊,西州有瓷窯,糧食生意不能往外邊做,瓷可以!”
往南邊不好賣,也可以買到關外的小國,用這些小國形一條經濟鏈,錢糧都能通過貿易從這些小國換取,西州便可離禹州和衡州獨自支撐,朝廷對渝州和渝州下方的糧道鉗制就不起作用了。
姜言意當天就去找了封朔,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
封朔桌前堆著高高一摞公文,他近日顯然是沒好好歇息過,眉宇間能看到明顯的疲態。
“法子不錯,但時間來不及。”封朔背靠太師椅,難得出幾分閑散,門路拉過姜言意,把人抱到了自己膝上。
書房的門沒有掩好,姜言意頻頻抬頭往外看:“你別不正經,我是來跟你說正事的。”
封朔把頭埋在肩頸,用鼻尖輕輕蹭了蹭白的脖子:“就抱一會兒,怎麼不正經了?”
他鼻子涼涼的,姜言意脖頸的又敏,當即瑟了一下,手抓了他的襟:“你別。”
封朔看這反應,眼神瞬間暗了下去,手不自覺掐了腰肢,啞著嗓音道:“出息。”
猜你喜歡
-
完結738 章

農門福妻醫傾天下
手握靈泉空間的神醫季婈,一朝穿越,成了大山腳下農門謝家13歲的童養媳。多了一個痞氣長工夫君、軟弱婆婆、包子大嫂、聖母二嫂、鐵憨憨大伯子、木訥二伯子、一心攀附權貴的大姑姐,還有隨時能咳斷氣的公公,外加幾個瘦骨嶙峋卻蠢萌蠢萌的侄子侄女們。日常高能預警:清粥照人......影,破衫裹瘦骨,漏屋連綿雨,囊無一錢守,腹作千雷鳴……窮哈哈的一家子還有時不時上門順東西的極品親戚。季婈咬咬牙,決定甩膀子努力賺錢。“等有了錢,滿漢全席開兩桌,吃一桌看一桌。”“等有了錢,紫檀馬車買兩輛,坐一輛拖一輛。”“等有了錢,五進宅子蓋兩座,住一座養豬一座。”“等有了錢,夫君養兩個……”“咳咳——娘子,想好了再說。”
180.3萬字8 37656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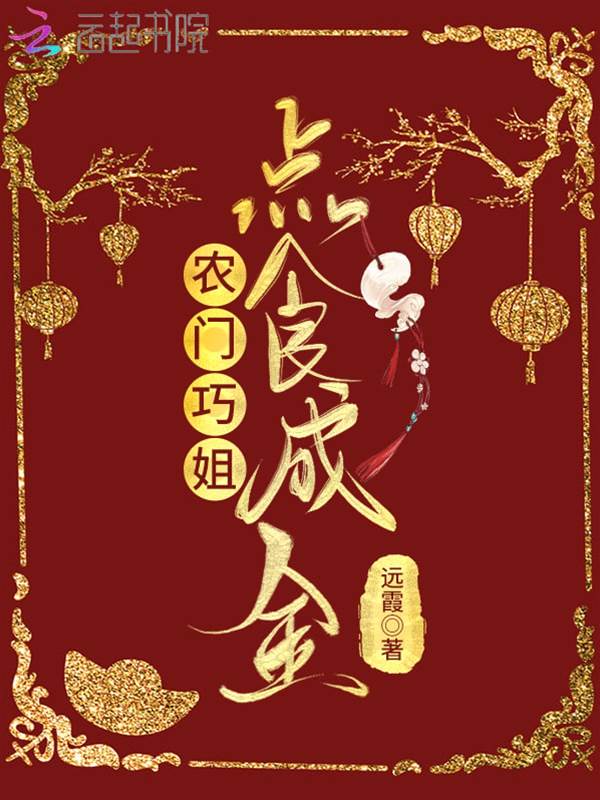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38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