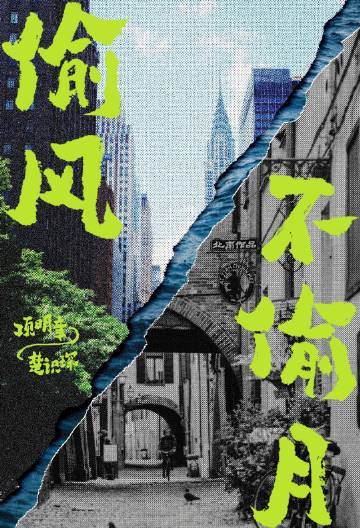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豺狼虎狽.第一部》 第39章
清醒
“……”似乎遲疑了下,承悅皺著眉將他的浴袍從肩膀拉了下來,男人吃了一驚,卻無法制止本就鬆垮的浴袍被人從上拉開,直至出了大半的,上面的青紫痕跡再無遮掩……
“承悅?”忐忑不安的男人吃力的轉過看著對方,下意識就想拉過服掩蓋上的痕跡,但手卻已經被按住。
承悅不由低頭打量男人的,臉上漸漸顯出震驚的神,顯然男人上的痕跡已遠遠超出他所預料的。
“你……是被人施暴了麼?”遲疑著問出聲來,承悅抬眼看著男人。
因為逆著,男人一時無法看清他的表,而僅僅那雙清澈的雙眼就讓他有種被看的覺。一時只能微微張著,啞然以對。
“……誰幹的?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程振全只是搖頭,示意對方別問了。
“那個醫生麼?還是金斐陵?還是……”
“承悅! ”男人蒼白著臉倉促地喝止,手指也反過來死死抓住對方,聲音幾近悲慘地,“別問……什麼都別問……。”
他害怕,害怕對方的裡接下來會說出某個人的名字,這種事,若是被人發現,他連活下去的尊嚴也沒有。
父子倫 ,是這四個字,就足以讓他跌到地獄。
“……程叔……”看著渾抖,在崩潰邊緣狀態的男人,承悅不由得放了的語氣,不敢再刺激他,只是彎下,輕輕的擁住男人,輕聲的安:“放鬆一些……都過去了……”
“……”男人疲憊的閉著眼睛,深深地吸氣,似乎也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失態。
“先休息吧,時間不早了……”過了好一會,覺到男人的呼吸已經平穩,承悅起拉開了兩人的距離,一邊為男人係好服,一邊低聲的說道。
Advertisement
程振全默默的點了點頭,疲倦的側過子,這時,床上有種屬於承悅的,淡淡的溫暖氣息,提醒著他某些東西。
這裡,是承悅的房間,承悅的床……
一旦清楚的意識到這點,男人就覺得怎麼也無法再躺下去……
“那個,我還是去睡沙發吧。”男人吃力的坐起來,有些不好意思的看著對方。
“嗯?”承悅微微疑的看著他“怎麼了?”
“……”男人似乎正醞釀著措詞,一時也沒有回答。
“你現在不好,怎麼能睡那裡。”雖然跟很多朋友關係很好,但他素來都沒有在家裡接待客人的習慣,所以家裡並沒有客房……
男人看了看承悅,沉默了片刻,才有些沙啞的道:“你知道,我喜歡男人,這樣其實……”
“……嗯?”
“不太方便……”說著,男人下意識的將視線挪向地板,勉強的笑了笑:“而且,你也會很噁心吧……”
“……”承悅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看著程振全。
“……”對方的沉默讓男人的笑變得有些僵,了,繼續看著地板,只是說出的話已經有些混:“一般人都會這樣,我知道的,也可以理解……同是很噁心,也很變態。換是我,我也會不了,那裡還會敢靠近…可你卻還是這樣照顧我……真的……已經很謝了……”
說著說著,腦子裡浮現出一幕幕自己極力想忘的難堪。
被綁在大街上,寫著死同,任路人指點厭惡嘲諷的景,以及事後被同學們的排跟攻擊,都如同錐尖般刺著他的心臟,令他疼得有些窒息……
“程叔,是有人跟你說過這種話麼?”承悅微微皺眉,聲音沉靜,一雙清澈的眼睛盯住男人。
Advertisement
“那些人對你很重要?還是說你對他們有什麼責任和義務?如果都沒有,那你本不需要因為他們的意見而有力。是私人的,別人無權過問。你沒有傷害誰,誰都沒有資格和立場指責你。評頭論足是他們的自由,不予理睬也是你的自由。”
“……”男人怔怔的著眼前這張俊絕倫的年輕面孔,一時無言,只是覺那紮著心臟的刺,好像一瞬間都化了般。
承悅看著男人的反映,忽然輕聲笑道:“你那麼介意睡這裡,莫非是怕半夜要忍不住襲我嗎?”
“啊?”男人一愣,一時反映不過來,隨後,臉紅得幾乎冒煙,慌地連連否認。
承悅再度笑了笑,漂亮的雙眼瞇了極好看的弧度,隨後,用手扶著男人讓他躺下:“好了,睡吧,我知道你累了……”
“……”男人臉紅的點點頭,老實躺下,閉著眼睛也不敢看。待承悅轉去洗澡,總算平靜下來的心裡卻又泛起一陣酸。
別那麼溫,承悅。
別那麼溫……
你這樣對我,我不了的……
會開始奢一些,永遠不可能的東西……
或許是因為實在太累的緣故,又或許是對方那令人心安的溫暖氣息,讓他不一會就已經沉沉的睡去,腦子裡難得的平靜安寧,什麼也沒想。
那些擾人的煩惱跟難堪的記憶,都彷彿已經消失了一般,讓他整個人都放鬆平息了下來。
程振全雖然睡得很安心,可的創傷,還是讓他半夜發了些低燒,也做了噩夢。
渾的力氣都好像流失了,上昏沉而燥熱。尤其是嚨,更是如火在燒,讓他輾轉難眠,反復醒來又昏沉過去。
意識昏之中,約覺自己正被人作輕地扶起,直到一清涼的緩緩流口中,那燥熱的覺才稍微緩解。
額上的汗水似乎也被人細心乾,他勉強睜眼去看,眼前的人好像是承悅,這令他心安了不,迷迷糊糊的吃了些藥,又昏睡了過去……
直到第二天中午,程振全才緩緩的醒來,他深吸了口氣,覺整個人已經輕鬆不,昨天那頭腦發漲發疼的覺,也已經緩解了很多。
下意識的轉頭朝旁邊看去,發現承悅正靜靜的趴在床邊。閉著眼似乎正在沉睡。呼吸淺而平穩。在的映下就如同讓人不敢的靈般,俊得讓人窒息,尤其是那略帶明的淺睫,每一都染著的黃金調。
只是那睫下的淡淡黑眼圈,讓程振全不由一陣心疼,視線無意識地轉向對方那修長而勻稱的手指。
雖然他昨天幾乎沒什麼知覺,可也能清楚的覺到,就是這雙手,整整照顧了他一個晚上,為他不斷的汗,換巾,以及替換汗的。
這個孩子……真的是……
這時,似乎覺到了什麼,承悅的睫了,隨即抬頭看向正盯著他的程振全,隨後,角微微勾起了一抹淡笑:“程叔,好點了嗎?”
“嗯……”程振全微笑的點點頭,滿心激,剛想說什麼,下忽然被對方住,接著那張俊的臉蛋在自己眼前無限的放大,而後伴著一清談的氣息抵上了他的額頭。
“嗯,燒基本上退了。”對上男人慌的雙眼,承悅的角不微微勾起。帶了點惡作劇的意味,反而更湊近幾分,直至兩人的雙幾乎就要上。“程叔,你在害嗎?”
“……”男人雙微微抖,卻半天都說不出一個字來,只能僵著看著對方,腦子更是因為承悅那撲在臉上的溫暖氣息,而了一團。
半餉後,似乎覺到男人的張已經到了極限,承悅才笑著移開了臉。
“了吧,我去弄點粥給你吃。”
隨後便起離開了房間,留下心跳失衡的男人揪著被子坐在床上發呆。
接下來的兩天,程振全覺得自己就如同在做夢一般。因為他的上的損傷,承悅幾乎無微不至地在照顧他,甚至不顧他的勸阻跟學校請了幾天的假。
也毫沒有因為他的向而對他有所忌憚,晚上甚至挨著他睡在一起,一切是那樣的自然而親近。那溫暖軀以及淡淡的氣息,都讓他幾乎徹夜難眠。
尤其是早上醒來那一刻,睜眼看到對方那沉靜的睡臉,簡直好得幾近不真實。
他甚至不由會去想,對方是否,有一的喜歡他呢?
雖然這個荒唐的猜測立刻被他自己否認,然而一旦曾這樣想過,那念頭就怎麼也殺不死,遏制不住,時不時就要冒出頭來,令他尷尬而慚。
這天晚上,程振全在床上翻覆到大半夜也無法眠,終於不得不鼓起勇氣,對著睡在自己旁邊的承悅小聲問道:“那個……明天,你有時間能陪我去一躺醫院麼?”
在不自不覺中,他竟對比自己小了近十多歲的孩子,有了一超越年齡的依賴。
他無法一個人去面對自己的兒子,但若承悅在的話,他想,他應該做得到。
對於他的出言請求,承悅似乎有些驚訝,但隨即便溫笑道:“好。我會陪你。”
程振全微微鬆了口氣,低聲說:“謝謝你。”
第二天程振全起得很早,得到允諾和支持,讓他額外地有了力氣,心也莫名明朗了。兩人在客廳吃著他準備的早點,對話簡單而輕鬆,只是這樣就讓他前所未有地滿足和心安。
門鈴響起的時候,承悅放下碗筷,笑著起去開門,程振全自然而然地目就隨著他而移。不知什麼時候起,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在粘在年上的視線了。
“悅悅!早哦~~”的聲帶著撒的鼻音從門外傳來。程振全只一愣,幾乎是猝不及防地,就看著那個甜的輕盈地撲到承悅的懷裡,然後極其自然的摟著年的脖子就是一記熱深吻。
那吻是火熱的,而他只覺得當頭被淋了一盆涼水一般,整個人都從恍惚的幻想裡清醒過來。
雖然只見過這個孩一次,他也已經能輕易認出對方的份來。
是承悅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三嫁鹹魚
林清羽十八歲那年嫁入侯門沖喜,成為病秧子小侯爺的男妻。新婚之夜,小侯爺懶洋洋地側躺在喜床上,說︰“美人,說實話我真不想宅鬥,隻想混吃等死,當一條鹹魚。”一年後,小侯爺病重,拉著林清羽的手嘆氣︰“老婆,我要涼了,但我覺得我還能繼續穿。為了日後你我好相認,我們定一個暗號吧。”小侯爺死後,林清羽做好了一輩子守寡的準備,不料隻守了小半年,戰功赫赫的大將軍居然登門提親了。林清羽
42.5萬字8 13569 -
完結126 章
禁宮男後
他百般折磨那個狗奴才,逼他扮作女子,雌伏身下,為的不過是給慘死的白月光報仇。一朝白月光歸來,誤會解開,他狠心踹開他,卻未曾想早已動心。當真相浮出水麵,他才得知狗奴才纔是他苦苦找尋的白月光。可這時,狗奴才身邊已有良人陪伴,還徹底忘了他……
27.3萬字8 6400 -
完結114 章

貌合神離
你有朱砂痣,我有白月光。陰鬱神經病金主攻 喬幸與金主溫長榮結婚四年。 四年裏,溫長榮喝得爛醉,喬幸去接,溫長榮摘了路邊的野花,喬幸去善後,若是溫長榮將野花帶到家裏來,喬幸還要把戰場打掃幹淨。 後來,溫長榮讓他搬出去住,喬幸亦毫無怨言照辦。 人人都說溫長榮真是養了條好狗,溫長榮不言全作默認,喬幸微笑點頭說謝謝誇獎。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這樣走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溫長榮的朱砂痣回來了,喬幸的白月光也回來了。
32.8萬字8 9088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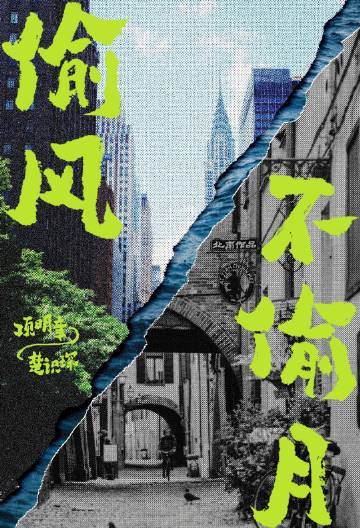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