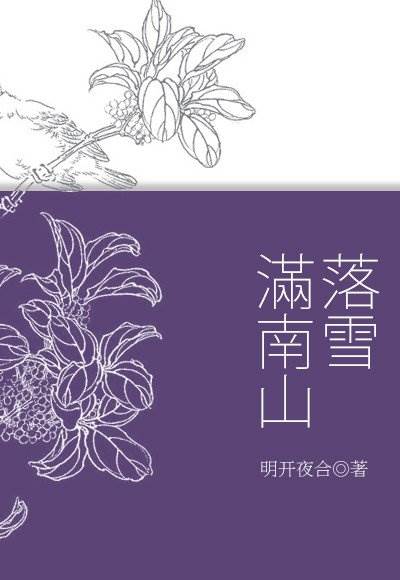《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第12章 第十二章
“哥、不不不我不是,我什麼都沒做啊。”顧俢禮被那一眼嚇得渾一激靈,手足無措跟在顧修義后解釋。
顧修義徑直踏過一地碎玻璃來到紀阮邊,紀阮仰頭看了他一眼,又倏而忍地偏過頭,水汪汪的大眼睛唰地掉下幾顆淚珠子。
好一場我見猶憐的哭戲。
顧修義眼里全是紀阮漉漉的眼尾和泛紅的鼻尖,大腦空白了兩秒,才蹲下來檢查紀阮腳踝的傷。
不嚴重,很淺的一道口子,但可能是紀阮過于細皮的緣故,仍然有幾顆珠往外滲,要掉不掉地掛在傷口,又久久不能凝固。
“大哥……”顧俢禮還在后面小聲地試圖解釋:“你相信我啊……”
“你去把醫藥箱拿來。”顧修義沉聲道。
“什麼?”顧俢禮像沒聽懂,指了指自己:“我?”
“還有誰?”顧修義手肘搭著膝蓋,回頭看他:“順便拿一把掃把,把地上的東西掃干凈。”
顧俢禮睜大眼睛連連后退幾步,不可置信:“你讓我干下人的活?!”
紀阮眼淚儲備告急,哭不下去了,撐著琴蓋拿手捂著臉,悄悄虛了條看戲。
顧修義起,面冷峻:“什麼下人?不都是人嗎?他們干得你干不得了?”
他指尖隨意點了點地面的狼藉:“掃干凈,一丁點碎渣都不許留。”
“哥!”顧俢禮還想反駁,眼見著要哭,被顧修義冷冰冰的目一掃,又只能打碎了咽回去。
顧修義的形對他們來說都太高大,站在那里什麼都不做,凌厲的氣場也足以得他膽戰心驚。
顧俢禮拳頭,用力咬了咬小跑出去。
等到方蘭察覺不對趕過來時,琴房里燈火通明,紀阮靠在鋼琴上被顧修義摟著輕聲哄,而他自己的兒子卻拿著掃帚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掃地。
Advertisement
這一幕也像在往方蘭臉上扇掌,一把奪過兒子手里的掃帚,僵地堆起笑朝顧修義走近兩步:“修義,你這是做什麼呢?”
顧修義忙著哄紀阮,頭也不抬:“哦,沒什麼,小禮犯了錯我罰他一下。”
“他!”方蘭深呼吸道:“他犯什麼錯了?”
顧修義冷冷回視一眼:“他把我家孩子弄傷了。”
方蘭視線立刻下移,落到紀阮白凈的小上,那里的腳踝了個白創口。
小小一塊!
看上去再晚點理就要痊愈的傷!
方蘭氣得太突突跳。
“媽!本就不是我弄的!”顧俢禮聲淚俱下地拉著方蘭的手臂喊冤:“是他自己摔的相框,我只是想和他道歉搞好關系,是他!是他不分青紅皂白就罵人,他還摔東西!”
“住!”方蘭一把甩開兒子的手,竭力維持賢惠的模樣:“修義啊,你也聽到了,小禮說他是冤枉的,你不能不信自己的弟弟啊!”
“這樣啊……”顧修義若有所思點點頭,挑起紀阮的下:“他說的是真的嗎?”
紀阮沒回答,紅腫的雙眼卻微微怔愣一瞬,像是沒想到自己會被質問,好幾秒后才極度失地垂下眼,咬著下忍眼淚。
顧修義立即抱住紀阮,他的后腦勺低聲哄:“好了好了不哭了,我知道了。”
他扭頭瞧了眼那母子倆:“你們也看到了,沒冤枉小禮。”
“大哥!”顧俢禮緒都失控了:“怎麼他說什麼你就信什麼啊!不是……他還什麼都沒說呢,我是你親弟弟啊!”
“好了小禮!”方蘭死死拉住顧俢禮,維持最后的理智:“修義啊……是、是,就算小禮犯了錯了,我替他道歉好不好?可你也不能這麼罰他啊……”
Advertisement
顧修義詫異:“我怎麼罰他了?”
方蘭浸著眼淚,像了莫大的屈辱:“你不能、不能讓他下人的活兒啊,他是顧家二爺!”
“唉,”顧修義頗為頭疼地嘆了口氣:“方姨,封建余孽在你這兒殘留太重了,都什麼年代了還一口一個下人?你這麼教育,難怪小禮不懂事。”
方蘭原本氣得不行,聽到顧修義這麼說,忽然琢磨出了點別的味兒:“你……什麼意思?”
顧修義笑了笑:“小禮不是大學快畢業了嗎,出國深造一下怎麼樣?”
“那怎麼行!”方蘭失聲,一直維持的假象在這一刻破裂:“他畢業了是要進公司的!”
“這事兒不急,”顧修義淡淡道:“小禮自己也說能力不夠,我送他出國也是為他好。”
“不、不行啊!”方蘭聲音抖:“小禮他從來沒自己出過遠門,那國外多啊……”
顧修義漫不經心:“不,我留學那麼多年不也好好回來了嗎,再說他是我顧家的兒子,出去還能委屈不?”
“就這樣吧,”他直接抱起紀阮往外走:“我會讓書整理各類大學的資料,小禮應該很快就能出國繼續學習了。”
顧俢禮已經徹底僵在了原地。
方蘭小跑幾步扯住顧修義的袖子:“你有點欺人太甚了,就算、就算要送小禮出國,也該由你爸來決定!”
顧修義看著方蘭窮途末路的樣子,角的笑很平靜:“如果你覺得告訴顧兆旭就能有用的話,請便。”
說罷再也不看那母子倆的表,抱著紀阮神清氣爽地大步離開。
手里的料驀地被空,方蘭踉蹌兩步,被顧俢禮扶住。
顧修義著前方的走廊,目空:“媽……所以我真的要被送出國了嗎?”
方蘭閉著眼,地著氣不說話。
顧俢禮腦子像被空了一樣:“我們告訴爸吧,爸一定不會讓我走的!”
方蘭緩緩直起子:“你覺得顧修義現在還會在乎你爸嗎?”
“可他、他總也有點話語權啊!”顧俢禮急切道。
“沒用的,”方蘭看向自己兒子:“他早就想好了。”
“什、什麼?”
方蘭眼窩深陷,像瞬間老了很多:“顧修義早就想送你出去了,放你進公司對他就是個威脅,今天只不過是借了那個小賤人的事索挑明了。”
推開顧俢禮的手,搖搖晃晃走出去:“就算不是現在,明天、后天、下個月,他還是會找借口送你出國的……”
·
“其實你早就想好了吧。”
回到家,紀阮洗過澡躺在床上,拿冰袋敷眼睛,一邊慢悠悠地說。
“什麼?”
顧修義坐在床頭,正用紗布按紀阮腳踝的傷口。
“我說,你早就想把你那便宜弟弟弄出去了,是吧?”紀阮戲謔道:“說是幫我出頭,其實你心思也不。”
顧修義輕笑一聲:“我想送他走隨時都可以。”
“但不能像今天這樣一邊罵人一邊把人弄走吧?”
紀阮拿掉冰袋坐起來,撐著下看顧修義:“如果換平常,按你后媽的難纏勁兒,你不得裝著假笑和他們虛與委蛇半天才能搞定?哪有今天這麼痛快?”
顧修義扯了扯角,不答話。
可他要是不答,紀阮就能一直盯著他,把他盯穿。
顧修義嘆息:“那你怎麼想的?”
紀阮不腦子,隨口道:“我覺得好啊,其實按他的智商,就算進了公司也翻不出什麼浪,主要就是膈應吧,討厭的人天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誰不惡心啊?”
顧修義被紀阮的用詞逗笑,豎起食指在他白的小上敲了敲:“用詞魯。”
他手指長,只用一食指拍打紀阮的小,莫名帶上了些說不清的暗示意味。
紀阮下意識往后了,被顧修義相當自然地握著腳踝拉住。
“咳,”紀阮撓撓鼻尖:“其實我還有一點擔心的……”
顧修義抬眸,示意他繼續。
“就是吧……”紀阮言又止:“要是那母子倆以為你是忌憚那小蹄子的才華才要弄走他的,不是更惡心了嗎?”
顧修義手一頓,下頜猛地了,看上去是真被惡心到了。
他那個后媽估計確實這麼想的,寧愿相信全天下男人都死了,也不會愿意承認自己兒子不聰明。
“不說這個了,”顧修義呼出口氣,看著紀阮的腳踝神嚴肅了些:“你這傷口不太對,怎麼止不住?”
紀阮長脖子看了眼,顧修義已經用掉了好幾張小紗布,出量和傷口的深淺比起來確實有點夸張,但也不算很多。
“沒事,”紀阮撇撇,“應該是我當時洗澡的時候又弄破了,個創口就行。”
顧修義不置可否,又仔細觀察了下那道傷口,確實很小很淺,應該就只是紀阮自己質不行,愈合得慢。
“雖說是為了出氣,你也不該弄傷自己。”顧修義一邊創口一邊說。
“這真是個意外,”紀阮抱著玩偶熊說:“我本來是往你弟那個方向砸的,砸得還遠,誰知道那碎玻璃怎麼飛過來的。”
他長嘆一聲:“可能就是害人終害己吧,果然以后還是不能作惡,不能當壞人。”
“覺悟還高。”顧修義抱著胳膊靠在床尾的木桌上:“不過是他們先作的惡,你算什麼壞人啊小朋友?”
他說著湊近些,打量紀阮在玩偶熊肚子上的臉蛋,調笑地彎起角:
“你——充其量算個倒霉蛋。”
猜你喜歡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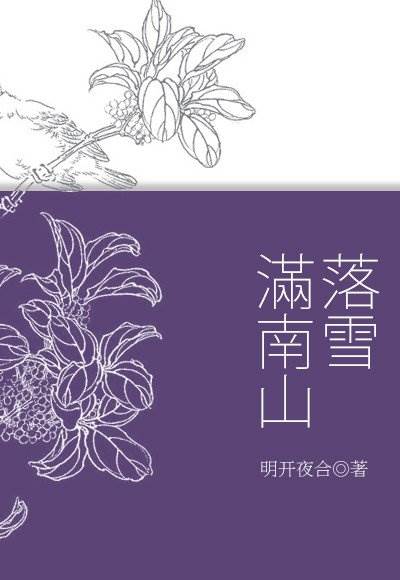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285 -
完結116 章

奈何她致命甜誘!
【雙潔 甜寵 青梅竹馬】大作家蘇亦有個隱藏筆名,筆名隻寫了一本書,書中的渣男與大明星君宸同名,長得極像,被主角虐得嗷嗷的。終於有一天,當她坐在電腦前準備日常虐君宸時,敲門聲傳來,大明星君宸的俊臉出現在她麵前……“你和別人說你前夫死了?”將人按在牆壁,君宸額上青筋在跳。蘇亦慫了,瘋狂搖頭。“沒有沒有!”君宸俯下身在她唇上狠狠咬了下:“聽說寡婦的味道更好,不如試試?!”
20.2萬字8 19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