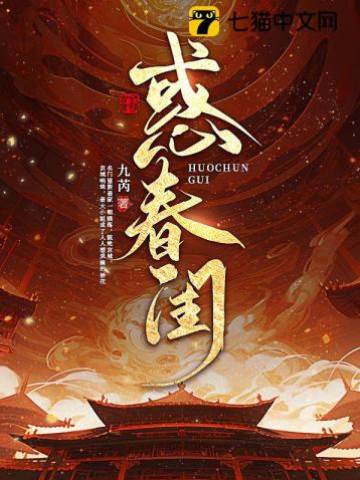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細腰美人寵冠六宮》 第85章 第八十五章
虞姝睡意不深, 但今晚不知怎的,很快就懨懨睡,按理說, 即將出宮離開京都,這本是一樁不小的事,可虞姝躺下沒多久, 就在封衡懷里睡了過去。
薄紗凌紋幔帳輕錘,一豆熹微燭火之中, 封衡睜開眼來,幽眸深沉如海, 凝視著懷中人。
封衡沒什麼舍不下的東西,哪怕是他的命也不例外。
時倒是喜歡極了一只雪長耳兔, 那只兔子被先帝殺之后,他也親手捅死了先帝的座椅,報仇之后,他一邊凈手,洗去手上漬, 一邊笑了笑,談不上舍不得那只兔子, 甚至還有些暢快。
而今,封衡自知已有了牽掛, 他和虞姝三年前就見過,但也不算結識太久, 可這割舍不下的心思卻是如此強烈。
若非封奕奕那個狗賊即將手,封衡會等到虞姝生產之后, 再做其他決定。
虞姝必須送出去。
封衡不能冒險讓留在京都。
腹中是自己的骨, 若是落封奕奕手里, 后果不堪設想。
封衡不喜任何人拿他的肋。
人一旦有了肋,要不就藏得嚴嚴實實,要不就自己足夠強大,否則,肋遲早會為自己天大的弱點。
封衡看了一會,又在虞姝眉目之間落下輕輕一吻,這便放開了,自行下榻。
知書聽見靜,去案臺前,掐滅了景泰藍三足象鼻香爐里的安神香。
封衡來到外間,知書和墨畫本就是封衡的人,已跪地準備聽從圣諭。十五和十七也在場。
封衡掃了一眼,嗓音清冷低沉,像從遙遠深夜傳來,“知書、墨畫,你二人不會武功,明日不必跟從修儀出宮。十五、十七,屆時跟在修儀邊仔細伺候著。若有任何閃失,提頭來見朕!”
Advertisement
知書和墨畫當即紅了眼眶,人都是有的,這陣子與虞姝相,已經出主仆誼了。只盼著修儀娘娘能夠安然歸來。
十五和十七立刻磕頭應下,“是,皇上!奴婢定誓死保護修儀娘娘!”
封衡走出重華宮,外面月影橫斜,再有一個時辰就要天明了。
封衡周俱是深秋寒氣,他眼底是要吞噬一切的深沉,在重華宮外站了好片刻,這才離開。
回到帝王寢宮,他濃曲長的睫上沾了濃,線下,顯得眼底一片潤,王權只一眼就愣了一下,還以為皇上哭了。
這……
必然不可能的!
他從皇上一出生就伺候在皇上側,皇上自從一歲過后就幾乎不曾哭過。哪怕是疼到極致,傷心到極致,也是握拳頭,咬牙過去。
封衡一記冷凝目掃過來,王權立刻垂下頭去。
王權勸了一句,“皇上,時辰尚早,要不要再歇息一會?”
封衡揮袖,“不了。”
他在龍椅上落座,抬手掐著眉心,只闔眸假寐,在腦子里又將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一切過了一遍。
任何細節、關鍵、轉折點,都沒有放過。
他好像輸不起了。
這一次,無論如何,都不能失敗。
封衡絕對是有仇必報的子,封奕奕在他眼里已經算是個死人了。
不!
是比死人的下場還要慘!
其實,封奕奕起初在封衡心里不過就是一顆棋子。
封衡知道,世家士族會利用封奕奕卷土重來,而封衡又何嘗不是呢?
暗瘡只有腐爛到了本,才能徹底清楚。
可封奕奕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擾了他妻兒的安寧!
封衡再度睜開眼來,“宣北狄長公主覲見。”
慕容毓這個人,也該派上用場了。
Advertisement
*
翌日,虞姝早早就將“書”寫好了。
昨日就想了諸多事。
封衡將送出京都,大概是因著腹中的孩子,對方不是沖著而來,而是腹中龍嗣。
想來,娘在將軍府應該無礙。
至于父親和虞家諸人,不在意。
和封衡待在一起久了,也逐漸開始變得冷無了起來。
虞若蘭“暴斃”之后,只字未提,也不詢問封衡,就仿佛虞若蘭這個人從未存在過一般。
封衡過來時,已經是午后。
秋日日和煦,比盛暑烈溫潤了不,男人下了轎輦,邁開大步而來,芒打在他上,襯得量頎秀,他足蹬石青靴,腰束紫玉帶,隨著他的靠近,虞姝還聞到了一清雅冷松香。
“昭昭,今日怎麼出來了?也不怕外面風涼。”封衡語氣之間盡是責備,可口吻又格外溺寵。
虞姝仰面著男人,反駁說,“可醫說,有孕的婦人需得偶爾曬曬太,對孩兒有好。”
封衡微擰眉,“朕自是知曉,你靠著窗戶曬即可。”
說著,又把虞姝拉了殿,仿佛很害怕拋頭面。
虞姝回頭了一眼秋意甚濃的后宮,有些狐疑:難道當真這般危險了麼?
也是了。
那日北地長公主宮,便有人在宮廷對出暗箭,若非是封衡,只怕已經是一尸兩命了。
虞姝將書給了封衡。
封衡也沒打開看,就揣了袖中。
今日即將別離,他也沒甚代,虞姝更是沒有詢問為何要讓辰王護送。
想來,皇上做事必然有他的道理。
“昭昭,陪朕看會書。”封衡拉著人,兩人坐在靠窗的小幾旁。
清茶沁香,秋斜,日打在人臉上,照亮了面頰上細小的小絨,像了七分的桃,封衡抬眼看向虞姝,凸起的結滾了滾。
虞姝察覺到了封衡的視線,可氣氛有些怪異,佯裝沒發現,索就不抬頭。
兩人便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時間轉瞬而逝,日暮降臨之后,封衡親手給虞姝穿上了斗篷,把送上了從皇宮北門出去的馬車上。
離別之際,他突然附耳,在虞姝耳畔低語了一句。
虞姝面一怔,隨即又漲紅了臉,憤憤道:“皇上!”
封衡輕笑一聲,嗓音格外低醇磁,將虞姝抱上馬車時,薄涼的在額頭一而過。
幔帳落下,隔開了兩人的視線。
以避開宮中眼線,封衡并未親自護送,而是直接轉回書房。王權跟在帝王后,一路小跑,也沒跟上。
到了書房,封衡一直在批閱奏折,任誰都不見,半晌都沒喝茶,王權亦不敢吱聲。
皇上越是不聲,只怕就越是在意啊。
*
十三與沈卿言護送馬車到了城門口。
辰王已經靜等多時,看見一輛極為尋常,且不起眼的青帷馬車,辰王握著韁繩的手了,那雙溫潤的眸映著月華冷,似有千言萬語。
沈卿言對辰王抱了抱拳,“王爺,盡快出城吧,今日雖是我的人值守,但以防夜長夢多。”
沈卿言其實很納悶,為何辰王不留下來奪位?
皇上是如何說服了辰王?
沈卿言當然不會懷疑封衡的眼和決策。
要知道,迄今為止,封衡的每一個決定,都不曾出過岔子。
辰王頷首示意,“好。”一言至此,他看了一眼馬車,這才調轉馬頭,帶著一行人,以及青帷馬車,駛出京都城城門。
在無人看見的地方,辰王眼中重新墜了星子,那是一片希翼。
沈卿言坐在馬背上,愣在原地,十三也在目送馬車走遠。
此時,銀月當空,秋風瑟瑟,月華如練,此此景,不免讓人詩興大起。
沈卿言不會作詩,倒是廢話一籮筐,“十三,你說,皇上到底是怎麼想的?這萬一辰王倒戈了封奕奕,那皇上豈不是將自己的肋到了敵人手里?那位可是辰王呀,曾經還慕過修儀娘娘呢。我著實想不通,十三,你能尋思明白麼?”
十三面無表,他緩緩抬手,捂住了自己的雙耳,朝著沈卿言遞了一個“我不聽我不聽”的眼神。
皇上的私事,哪里是他能隨便置喙的?
這個沈大人,話真的多啊!
十三又向夜蒼茫,確定馬車走遠,他調轉馬車,踢了馬腹直接離開,打算以最快的速度回宮復命。
沈卿言頓時覺得好生無趣。
皇上和十三,都嫌棄他了。
還是他家阿香姑娘好!
只可惜,阿香姑娘已經跟著恒慶王夫婦回冀州去了。
沈卿言心中略有埋怨和委屈。
他的大婚之日即將到來,可為了皇上的大計,他可以延緩婚事,恒慶王夫婦回冀州也是皇上的安排。
就在沈卿言黯然失神,正暗暗慨人生寂寞如斯時,馬蹄聲從不遠的長街“噠、噠、噠”傳來。
沈卿言渾一。
不多時,就看見梳著高高馬尾的紅子逐漸靠近,在月之中,沖著他燦然一笑。
沈卿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又頓時覺得,人生是驚喜,“阿香姑娘!你……你怎麼又回來了?”
楚香生怕他多想,立刻道:“我可不是為了你!我、我是為了兄長代給我的任務才留在京都。”
楚香知道,即將有一場巨大變故要發生。
總覺得,得陪在沈卿言側,不能讓這個呆子一人去承擔。
他和已經是未婚夫妻了,不是麼?
沈卿言撓撓頭,咧出一整齊的白牙,“你能留下來就好。”
阿香姑娘在側,他頓時覺得渾都是勁,對未來頗有期許。
*
皇宮,書房。
十三稟報過后,封衡握筆的作一滯,墨滴落,染了半邊奏折。
安靜了許久,封衡的嗓音才淡淡響起,“朕知道了。”
王權和林深幾人大氣也不敢一下。
皇上好像又回到了從前,不茍言笑、沉無溫。
整個皇宮仿佛陷了巨大的沉寂之中。
小公主原先養在重華宮,虞姝臨走之前不太放心,反復代了封衡,讓他善待小公主。
封衡掐了掐眉心,不知怎的,良心發現,下令道:“重華宮的那個小不點,送到太后邊去吧。”
王權愣了一下,這才明白皇上指的是誰。
“是,皇上,老奴這就去辦。”
真是造孽啊。
可憐見的孩子,又有什麼過錯呢。
要怪就怪太后幾人。
貪心不足蛇吞象。
*
城外,馬車十分平穩的行駛在道上。
雖是不起眼的青帷馬車,但里面鋪了上好的絨毯,溫好的羊,制了丸子的補藥,各種金瘡藥,干糧果脯……應有盡有。
羊角宮燈發出熹微的束,虞姝自是毫無睡意,但也談不上心忐忑,對封衡有一種超乎尋常的信任,總覺得一切都能順遂。
十五和十七騎馬跟在馬車后面。
虞姝掀開簾子往外看了一眼,就見除卻十五十七之外,還有幾個穿勁裝的男子,又往隊伍前面看去,正好撞見了辰王回過頭來的視線。
隔著數丈之遠,兩人也恰能四目相對,辰王言又止,虞姝對他輕輕點了點頭。
辰王也笑了笑。
還得繼續趕路,沒有徹底遠離京都之前,辰王不敢停下腳步。
他向前方,著韁繩的手又了幾分,他欠虞姝一條命,總算得了機會回報了。
當然,那日在書房和封衡商榷了近一個時辰,封衡也答應了他一些事。
只不過……
辰王眸忽然一凜。
既是能徹底遠離朝堂,擺皇氏,他又為何要回去?!
在無人看見的地方,辰王眸中略過一抹異,當即踢了馬腹,稍微加快了速度。
*
五日后,是本朝每年一度的皇家秋狝之日。
這一日,帝王會攜重之臣,前去東城的皇家獵場,進行長達三日的涉獵活。
本朝文武兼崇,開/國/皇帝便是在馬背上打下來的江山。
秋狝被本朝而言,意義非凡。
若是一任帝王不能參加秋狝,那便意味著,他離著退位不遠了。
這一天,帝王的扈從隊伍從皇宮中華門出發,浩浩上千人,帝王車攆后面跟著年輕一輩的新任員、衛軍,以及世家士族的年輕才俊們。
帝王著一玄長袍,玉帶束腰,墨發用了玉簪固定,如此穿扮倒是顯得年輕氣盛、鋒芒畢。
他全程不茍言笑,一張冷峻無溫的臉,完到宛若是用刀斧雕刻而,氣度清冷卓然。
若問九天之上的神仙是何姿態?大抵便是如此了吧。
沿街的百姓紛紛跪地,大膽些的子抬頭向帝王,頓時又是一腔芳心澎湃。
此時,茶樓雅間,一披著狐裘斗篷的男子哂笑一聲,過臨街的窗戶往下去,問道:“本王與皇上,孰更?”
正跪地給他捶膝的婢,立刻答話,“自是王爺更。”
封奕奕著一只茶甌,淺噙了一口,看著封衡颯氣凌然之態,又不免想到三年前他被封衡退雍州之事。
封奕奕眸之中,目一沉。
“哼!這個臭小子!本王此前倒是小瞧了他!但姜還是老的辣。先帝都不是本王的對手,又何況是他!”
封奕奕忿忿不平。
三年前,他從皇宮逃離的姿態,著實不雅致。
等到他再度奪下皇宮,定要將那的狗徹底封死了!
知人已全部被他死,世上再無人記住三年前那日的奇恥大辱!
封奕奕擱置下茶甌,將雙足抬起,遞給了婢。
婢了解他的習,立刻給他噴了花,這又穿上了一雙描金邊的烏皮靴。
婢做好這一切,封奕奕這才站起,朝著臨街的窗戶了個懶腰,一心認為,這一次封衡輸定了。
先帝不在了,他這個當叔叔的,自是要好生“調/教”晚輩!
“本王,也該出發了。”
*
獵場,秋風蕭瑟,皂靴踩在林中,發出枯枝敗葉被碾碎的聲響。
號角聲響徹天際,狩獵開始了。
封衡的勁/腰/上掛著一張/弓,手持一把三尺長劍,這把劍在殺人時,仿佛會發出低低嗚鳴,當初封衡為了盜取墓地錢財購置兵馬糧草時,無意中得來的一把寶劍,名“赤霄”。
這赤霄劍重達數十斤,尋常男子本拿不,但落封衡手里卻是意外的合適。
仿佛是為了他量打造而。
沈卿言、十三等人早已高度戒備,楚香一直被沈卿言圈在側,他二人近日來倒是無比親,十三時不時故意遠離他二人,免得瞧見什麼令人耳紅的畫面。
涉獵已經開始了片刻,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用不了多久就必然會有意外發生。
就在這時,數箭/鏃從暗齊齊了過來,就像是有人發出了信號,弓/弩/手早已在暗準備就緒。
十三大喊,“不好!護駕!”
封衡狹長的眸頓時一凜,手中赤霄揮出,足有三尺多長的長劍如在半空揮舞,眼看不見劍,只能看見刀劍影,以及刺耳的銳利聲響。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137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2748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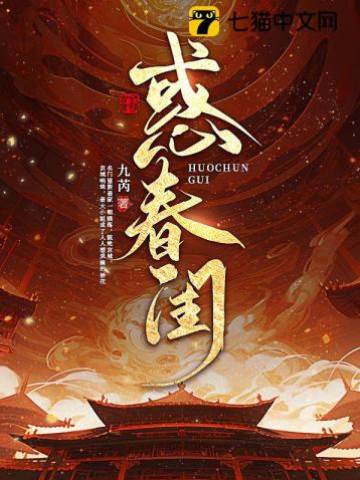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6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