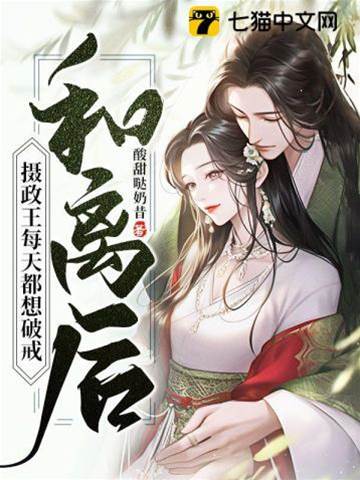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雪滿長空(嫁給廢太子沖喜)》 第 159 章 番外二
番外二前世,HE(六)
晨間醒來,錦帳里還都是溫暖意。
溫印覺得很暖和,也不冷。
微微睜眼時,見李裕抱著,人沒醒,致的五和廓猶如鐫刻一般,比年時多了說不出的和魄力……
他沒醒,溫印手,一點點,輕輕上他臉頰。
小狗長了……
沉穩,斂,而且,也真的相貌堂堂了。
黎媽果然沒說錯。
溫印似是沒看夠,目繼續停留,看得仔細,好像將早前沒看的都補回來一般。
稍許,李裕實在是也不好再裝了,他也不知道溫印看他看這麼久,李裕沒睜眼,卻輕聲道,“夫人,早。”
溫印還是嚇一跳。
李裕笑了笑,睜眼親,溫出聲,“不多睡會兒?”
“醒了。”輕聲。
“哦。”
他口中的哦字說完,兩人似是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久別重逢,翌日就新婚房……
雖然早前他噼里啪啦說了一大通,但都是當時場景,眼下,其實兩人都有些斂和怯。
四目相視中,李裕重新吻上。
不知道說什麼的時候,親就對了。
新婚燕好,原本親近也不需要理由,只是他比早前夢里親時更穩重,不好意思像十九歲的李裕那樣一直鬧騰。
昨晚太好……
就是,夢里有夢里鬧騰的好,昨晚有昨晚真實的好。
不一樣……
但都甘之若飴,永生難忘。
溫印坐起,李裕蹲下,仰首替穿。
“我自己來吧……”溫印輕聲,也有些不好意思,從里到外,都是李裕穿的。
李裕溫聲道,“讓我做些事。”
溫印沒出聲了。
穿,描新眉,就似所有尋常夫妻一樣,在描眉的時候,他年心起,在臉上畫,溫印追著他鬧,像年時候一樣,但溫印一跑就會咳嗽,李裕歉意,“我忘了……”
Advertisement
溫印笑道,“沒事,我也忘了。”
稍許,劉大夫端了藥來。
新婚翌日也要喝藥——這了劉大夫的最新名句。
昨日的拜堂劉大夫也在,年時候告訴溫印,哎呀呀,從來沒見過劉大夫這麼笑,臉都要笑列了……
但溫印見他的時候,還是一幅溫印欠他很多銀子,且永遠還不了的模樣。
溫印笑了笑,知曉他就是喜歡同互懟,他要是忽然和善了,還不習慣呢。
喝藥的時候,彭鼎匆匆上前,“主家,夫人,何相的信。”
李裕這趟南巡出來的時日有些久,后來這月余又借著在東山郡王府的名義,實則是來繁城尋溫印了,何相找他,應當是朝中要事。
李裕拆信。
一側,溫印還在一面喝藥,一面與年說著話。
李裕很快閱完,是何相催他回京了,是賦稅改革的事,何相需要同他商議,他也確實離京有些時候了。
年見李裕折回,知曉他們有話要說,機靈道,“我去拿幾個橘子。”
溫印點頭。
正好溫印喝完藥,端起一側的水盅漱口。
李裕蹲下,仰首看,“阿茵,我出來有些時日了,朝中有事,我要趕回京中了,你同我一道走,還是晚些回來?”
溫印放下水盅,他繼續道,“要是同我一道,會走得快些,怕路上顛簸;你如果晚些走,可以慢慢回,我讓彭鼎跟你一道,不用跟著我一道。”
溫印笑了笑,沒有穿。
他要是真想晚些走,就不會特意問了……
溫印溫聲道,“我同你一道。”
李裕果真眸間清亮,“那走水路,沒那麼顛簸,我記得你不暈船,等這一段過去,再換馬車也平坦了。要是路上顛簸厲害,你躺我懷里。”
Advertisement
溫印頷首。
李裕笑若清風霽月,溫印才放下茶盅,李裕抱起,忽得高出他兩頭,溫印嚇一跳。
李裕笑開。
***
何相催得急,他們又要走水路,提早兩日走,可以將水路的時間省出來,于是李裕和溫印下午就,福旺幾日留下收拾溫印的東西。
繁城有碼頭,只是長風國中河流很,所以碼頭同蒼月和朔城和南順的慈州相比,不算發達,但也人來人往,絡繹不絕。
“風大嗎?”李裕怕著涼。
溫印搖頭,即便病著,這些年沒四走,這些還是習慣的。
“主家。”利安上前,有事同他說。
“等我。”李裕待了聲,便同利安一道去了一側。
溫印在繁城碼頭看著眼前的忙碌景象,安心在照看一旁的商船,正好有批貨要北上,安心今日也正好在碼頭。
安心上船的時候,正好前方有腳夫不穩,東西落下,整個通道都晃了晃,安心險些摔下船去,是側的人扶穩了。
安心轉眸,彭鼎提醒,“小心些。”
安心沒出聲。
彭鼎看了看,若無其事道,“這景真。”
安心還是沒出聲。
彭鼎嘆道,“我就是襯托下氣氛。”
確定他沒話說了,安心才道,“松手。”
彭鼎才反應過來,一直握著胳膊。
“走了,彭將軍,日后見。”安心辭別。
彭鼎還想說什麼,但安心已經上船了,兩人不是一條船,也不是一個方向,彭鼎只能眼看著離開,有些喪氣。
這也不好使啊……
年這家伙,什麼餿主意啊,說讓人腳夫佯裝拿不穩,上船路上顛簸,他手扶住,然后安心撞在他懷中,這說得天花墜,好像沒什麼用。
彭鼎唏噓。
正好安心轉頭,看他一幅惱火,且撓頭的模樣,
安心笑了笑。
常年看蒼月和繁城一帶的生意,最悉的就是碼頭,剛才的腳夫走著走著就佯裝沒拿穩重的模樣,一眼就能看出,然后彭鼎又這麼是時候的出現……
其實,有些拙劣。
方才沒拆穿罷了。
當下,彭鼎正懊惱著,安心折回,遞了水囊給他。
他接過。
“一路平安。”安心說完轉。
“嗯,你也是。”彭鼎翹首看著,然后低頭看著手中的水囊,好像無價之寶一般,然后喝了一口。
神清氣爽,清甜啊……
開船了,安心在甲板出遠遠看他,順子上前,“安管事。”
安心莞爾,“方才瀉藥的事,多謝你了。”
順子尷尬道,“沒有沒有,這種事,安管事你一個姑娘家不好說,我去做就好。”
安心沒有說旁的,只是在甲板上,遠遠看到彭鼎方才還好好的,眼下忽然捂了肚子,慌張東張西著。
安心好笑,二傻子……
只是安心抬頭時,二傻子應當是也看到了,知道他都要憋不住了,但還是停下,朝揮手。
忽然間,安心沒說話了,也斂了笑意。
想起了安潤。
每次遠門,安潤就是這樣的。
安心看向彭鼎,彭鼎朗聲,“一路平安。”
安心心底微暖,低眉笑笑,再抬頭時,彭鼎又捂著肚子到找地方去了。
安心笑開。
***
另一側,利安剛同李裕說完話,李裕頷首,叮囑了幾句,利安趕去做,李裕正好轉,回頭剛好看到角落的烏篷船。
李裕目微頓,烏篷船外的人正上船,也恰好看到李裕,對方明顯僵住,不寒而栗的時候,李裕又看了他一眼,竟然當做沒看見一般,轉離開。
貴平愣住,他沒想到會在這里見到李裕。但更沒想到,李裕明明認出他,卻沒有吱聲……
——朕要留下來見李裕,朕同他之間,始終要有了結。
——你走吧,朕邊什麼人都沒了,我想你活著……替我活著。
——岳東籬,從今晚后,這世上再沒有貴平,走!
……
思緒涌上心頭,貴平眸間微滯,一直楞在原。
“岳公子,開船嗎?”船家見他出神許久,但后面的烏篷船到了,不好一直占著位置,船家小聲問起。
貴平回過神來,“走吧。”
簾櫳放下,烏篷船慢慢駛離碼頭,又有新的烏篷船頂上。
烏篷船上只有船家和貴平兩人,船家是個健談的,“岳公子很來繁城吧,您看,繁城偏南,雖然雪照下,但是江河都是不結冰的,這才剛開始下雪呢,等再下一陣子,就能見到船在江中走,船篷覆白雪的景致。”
貴平笑道,“是嗎,我倒是不曾見過。”
“那您得看看了。”船家一面劃船,一面說道。
貴平又起簾櫳,朝方才的方向看去。
下雪了,溫印正好撐傘來尋李裕。
李裕心中還在想貴平的事,他剛才沒看錯,是貴平,但他也知曉,在婁府,最后救溫印的人是貴平……
“你怎麼來了?”他看向溫印。
溫印披著狐貍披風,但迎風還是有些咳嗽,“雪下大了,我來找你。”
李裕笑了笑,下上的大氅披在上,然后在的目下,給系好。
大氅帶著溫,暖暖的,驅散了寒意。
李裕從手中接過傘,過指尖的時候,李裕微怔,好涼……
李裕一手撐傘,另一只手握住的手,暖意傳來。
溫印仰首看他。
他溫聲道,“等等,馬上就暖和了,自己也不將息著。”
溫印:“……”
他繼續道,“我會心疼的。”
溫印莫名臉紅。
雪下大了,李裕牽著,朝另一條船走去。
貴平略有失神,好似早前的幕幕都似走馬燈一般在腦海中轉著,回過神來時,兩人的背影在大雪中漸漸淡去,宛若一對璧人,貴平淡淡笑了笑,放下簾櫳,朝船家道,“是好景致。”
船家朗聲笑起來。
小船悠悠,轉眼間,繁城就在后。
漸行漸遠……
***
時一晃便是兩年,兩年都如白駒過隙一般。
“今日生辰,許什麼愿?”溫印笑著看他,“第三個不要說出來,說出來就不靈了。”
李裕啟,吻上間,“許完了。”
——如果有機會,他想來得及回到從前,他希一直平安順遂,希他們一直琴瑟和鳴,所有的事都給他……
李裕眸間淡淡笑意。
溫印想說什麼,但又咳了兩聲。其實這一兩日,一共就咳了這兩聲。這兩年來一直在將養,子真的慢慢好了很多,臉上也有了紅潤,不似早前清瘦了。
李裕抱起,“阿茵,好像真的好了。”
溫印笑,“許是,天蓮草的藥效好?”
李裕附和,“是啊,下次一定好好謝謝漣卿。上次陳修遠還怪氣說我把他滿苑子的天蓮草都拔了。”
溫印湊近,“真的拔了?”
李裕想了想,認真道,“好像,還留了點。”
溫印笑逐開。
李裕看著,腦海里想起早前。
“劉大夫,無論什麼代價,什麼藥材,要什麼,你都告訴我……”彼時,他是這麼同劉大夫說起的。
劉大夫看他,“你是什麼人?”
李裕沉聲,“是我發妻,因為病重,一直躲著我。”
劉大夫怔住,稍許,才低聲道,“我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只能好好用藥,安心靜養,旁的聽天由命。不好的是,病了這麼久,一直在拖,所以留了些病,你也看到,咳嗽,雨天就腹痛;但好的是,我也沒想到到眼下還活著,比旁的男子都堅韌,心里有念頭,就一直在堅持……”
“那就讓一直有念頭。”李裕垂眸。
劉大夫垂眸。
李裕抬眸看他,“不管天山雪蓮也好,千年靈芝也好,編一個,讓覺得自己會好。”
“這……”劉大夫詫異。
李裕看他,“剩下的給我。”
劉大夫會意,但也輕嘆,“明,未必會信。”
李裕篤定,“會信。”
劉大夫凝眸看他。
他繼續道,“哪怕萬分之一的機會,我也要陪一道;哪怕一年,兩年,我都陪一道。”
劉大夫愣了良久,“好。”
……
李裕收起思緒,溫印撒,“我想吃豬蹄了。”
李裕笑著喚了聲,“利安!”
利安,“陛下。”
“有人要吃豬蹄了。”李裕開口,利安便會意,趕吩咐膳房去做。
東暖閣,溫印躺在他懷中一面翻書冊,一面等著豬蹄來。
李裕也看著折子,像這兩年來最平凡和普通的一日一樣,兩人在一,他忙碌,也做自己的事。
但他余看向,是真的一日日好起來了,承蒙上天眷顧……
“下下,別鬧,你就不能學學臘初嗎?”口中念念有詞,李裕角微微勾了勾。
“陛下,娘娘,永安侯世子和大小姐來了。”利安通傳。
瑞哥兒和小鹿……
“傳。”李裕放下折子。
溫印剛想起,李裕制止,“躺會兒吧,他們又不是沒見過。”
李裕知曉正躺得舒服,不想起,李裕這麼說,溫印也心安理得。
“姑姑,姑父!”遠遠就聽到兩人的聲音。
一轉眼,龍胎都十四五歲了。
“姑父,生辰快樂!”瑞哥兒問候。
“我們想姑父和姑姑了,就宮來看看。”小鹿甜。
李裕和溫印都跟著笑起來。
瑞哥兒和小鹿見溫印躺在李裕懷中,知曉他們兩人很好。這些年姑姑病著,姑父一直在照顧,后宮也沒有旁人,有時候恍然一想,好像還在離院時一樣,沒變過。
“去取小鹿喜歡的點心來。”李裕吩咐。
利安照做。
“謝謝姑父。”小鹿剛說完,李裕又喚了聲,“瑞哥兒。”
“姑父!”瑞哥兒笑。
“最近有沒有好好看書?”到瑞哥兒這,李裕瞬間變嚴肅臉。
不好,瑞哥兒心中一咯噔,還是斬釘截鐵,“有!”
“哦。”李裕頷首,也沒穿,“背《五目記》給朕聽聽。”
瑞哥兒苦瓜臉:“……”
小鹿笑開。
溫□□中清楚,哥哥不在了,李裕對小鹿和瑞哥兒比旁人都更上心。
瑞哥兒和小鹿在宮中玩了些時候,又一道用了晚飯才回了侯府。溫印有些困,黃昏前后就躺在東暖閣小榻上睡著了。
溫印近來嗜睡,也沒什麼神,雖然沒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但他怕好容易病才好……
“讓薛寧來一趟。”李裕擔心。
薛寧診脈很久,再三確認,才朝李裕道,“恭喜陛下,娘娘懷了龍嗣。”
天子后宮只有中宮一人,現如今膝下子嗣凋零,中宮有孕,薛寧原本是想天子定會龍大悅,但薛寧說完,卻不見天子像想象中的高興。
“薛寧。”李裕沉聲。
“陛下?”薛寧意外。
“你隨朕來,還有,中宮有孕的事,不要聲張。”李裕叮囑完,薛寧趕應聲。
……
等溫印醒來,都是夜里了,李裕坐在側。
猜你喜歡
-
完結410 章

寡人有喜了
重生之前,青離的日常是吃喝玩樂打打殺殺順便賺點“小”錢,重生之后,青離的任務是勤政愛民興國安邦外加搞定霸道冷酷攝政王。情敵三千?當朝太后、嬌弱庶女、心機小白花?青離冷笑,寡人可是皇帝耶!…
71.6萬字8 24930 -
完結598 章
宮女奮斗日常
凌歡冰肌玉骨貌若天仙,卻無心權勢,一心想著出宮。最終母子二人皆不得善終。重來一次,她的目標是養好崽崽自己當太后。大女主宮斗文。女主心狠手辣智商在線。情節很爽。
87.7萬字8.18 59257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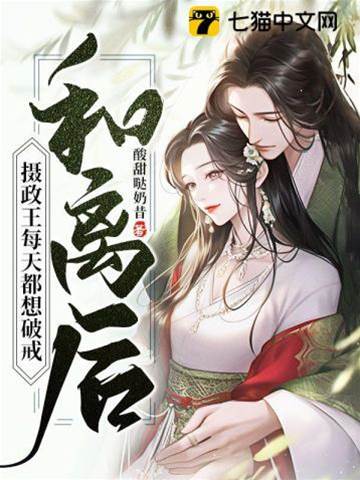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206 -
完結719 章

熾野纏情
【雙潔 花式撩夫 逗逼 甜寵爽文】沐雲姝剛穿越就是新婚夜與人私通被抓的修羅場,新郎還是瘋批戰神王爺容九思!救命!她捏著他橫在她脖子上的刀卑微求饒:“王爺,我醫術高明,貌美如花,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留我一命血賺不虧!”他:“你溫柔體貼?”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很兇殘!”容九思最初留沐雲姝一條狗命是閑著無聊看她作妖解悶,後麵發現,她的妖風一刮就能橫掃全京城,不但能解悶,還解饞,刺激的很!
126萬字8 42993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