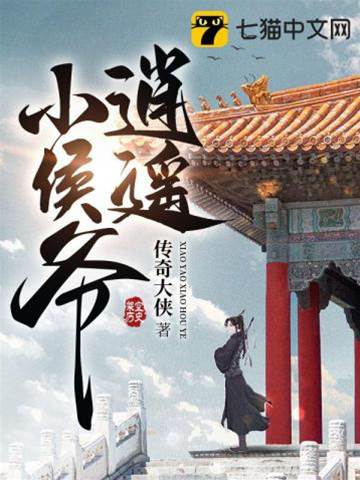《穿成亡國太子妃》 第50章 亡國第五十天(捉蟲)
當天下午秦箏就為了修索橋一事做起了準備工作, 尋了幾條繩索,拼接起來足足有八十丈長。
又用尺子比著,在繩索上每隔一尺系一條細線, 隔一丈系一條線,以此來作為簡易的大型測量工。
傍晚楚承稷練兵回來瞧見坐在桌前, 手拿著一把尺子, 量一下系一條繩,腳下已經堆了一大圈卷起來的繩索。
他進門后也不見秦箏抬頭, 某人依舊專注地搗鼓自己手中的繩索,里還時不時含糊嘀咕幾聲,像是在說給自己記的數字。
烏發挽起, 從楚承稷的視角看過去能清晰地瞧見那截白的脖頸,起了念,就容易生念, 他眸暗了一瞬, 但秦箏只顧完自己的繩尺, 自始至終都沒給楚承稷一個眼神。
楚承稷只覺這樣認真的模樣倒是怪招人疼的。
他靜靜看了一會兒,好笑問:“這是做什麼?”
“明天測量兩山崖之間的寬度。”秦箏因為回答這一句, 記混了自己已經量了多尺,垂著腦袋,眉糾結得直打架:“你先別跟我說話, 我這快完工了, 若是記混了還得重來。”
看慣了明的模樣, 迷糊倒是第一次瞧見。
楚承稷沒忍住在發頂了兩下,拿過手中的竹尺, “一尺系一條小繩是麼?我來。”
竹尺和繩索都被楚承稷拿過去了, 秦箏終于抬起頭來, 了酸痛的脖頸:“滿十丈就告訴我,得做個記號。”
這麼一說,楚承稷也注意到繩索上有幾還系了不同線捻的細繩,想來這就是說的記號了。
他道:“測個山崖間的寬度需要這麼麻煩?”
秦箏給自己倒了杯茶咕嚕嚕喝下后才道:“以后再有別的工事,有這麼一條度量的繩子,能省不事。”
Advertisement
這個時代最長的尺子不過也才一丈長,若以后每次修建大型工程都得拿個尺子去量,可不得累死,秦箏覺得自己自制的“繩尺”便利得多。
楚承稷聽了的解釋,倒是不可置否。
他低頭制繩尺,秦箏一開始是盯著他手上的作的,但不知怎的,視線順著他的修長俊秀的大手上移,慢慢就落到了他臉上。
他專注做事的時候,眉宇間那清愈重了些,夕從大開的門外灑進來,落在他半張臉上,恍惚間他臉上的廓也和了幾分,院外槐樹上的槐花紛紛揚揚落下來,像是一下了雪。
秦箏看著他出了一會兒神。
“好了。”楚承稷抬眸朝看來時,忘了收回視線,就這麼撞了他清淺的眸子里。
像是原本平靜的湖水里投了一顆小石子,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他形狀極其好看的在夕下仿佛涂了一層,秦箏鬼使神差地說了句:“相公,我能親你一下嗎?”
楚承稷沒說話,但整個人往后往竹椅上一靠,頗有幾分“任君采擷”的意思。
秦箏有點慫,但膽上頭,又覺得他那方面有殘缺,可能在這些事上的確不好主,那自己主一點也沒什麼。
慢吞吞湊了過去,一只手有些張地抓住了楚承稷坐的那張竹椅的扶手,雖然努力表現得自己很淡定,可還是張得咽了咽口水。
楚承稷平靜地垂眸著,幽涼深邃的一雙眸子里,全是人捉不的神。
他哪怕坐著,也比秦箏高出很多,垂眼看,莫名帶著幾分居高臨下的迫。
秦箏被他看得不自在,遲疑片刻,抬手覆在了他眼前,緩聲問:“可以嗎?”
嗓音本就好聽,眼下刻意放了幾分,只讓人覺得耳廓似被羽輕輕拂過,整顆心都了起來。
Advertisement
“嗯。”
楚承稷在掌下,順從閉上了眼。
秦箏覺到了,卻還是沒膽子把手拿開,仿佛是怕他下一刻就會睜開眼。
西山日薄,那縷從門外照進來的夕下移,落在了他半個下頜和脖頸那一片,冷白的被染了金,秦箏注意到他結了。
看了一眼被自己捂住雙眼后,雙手放在膝前,顯得格外乖巧任為所謂的楚承稷,緩緩靠近,卻又在僅距他瓣一指距離時停了下來。
楚承稷自然也覺到了,停下了,他便安靜等著。
淺淺的呼吸噴灑在他面頰,帶著上那特有的冷香,不過一指的距離,他對的一切知都再清晰不過。
但和他的距離慢慢拉遠了,似乎是怯弱退了回去,楚承稷搭在膝前的指尖剛一下,猛然間整個人都僵住了。
秦箏,吻上了他的結。
輕輕著他脖頸上凸起的那片骨,秦箏覺自己心跳也有些快,捂在楚承稷眼前的那只手都在輕,好在另一只手撐著竹椅的扶手能借力。
他的看起來很適合接吻,但秦箏更想親他的結,最好是能輕輕咬一下。
在自己擂鼓般的心跳里,閉上眼,試探地出舌尖了,那一瞬間,明顯覺到楚承稷整個人僵得更厲害了。
原本還想咬一下的,因為慫,松開捂著他眼的手后就退了回去。
楚承稷果然是在松手的瞬間就睜開了雙眼,眸暗沉得人心驚,秦箏還沒坐回原位,就被他扯住胳膊一把拽了過去。
幾乎是整個人都跌進了楚承稷懷里,一只手撐著他膛才能找到支撐點。
他一只手著下顎,另一只手扣在后頸,整個人強勢又危險,偏偏說話時又是一副好商量的語氣:“我親回來了?”
秦箏長睫輕,被他暗沉的視線注視著,都不知自己是怎麼點的頭。
楚承稷薄過來的時候,還安自己沒什麼好怕的,上次不也親過了嗎?
但很快秦箏就覺自己頭皮都快炸開了。
他這次顯然不是淺嘗即止,一開始描繪形時還很溫,舌尖一下一下地輕掃、舐,讓腦袋都跟著有些昏昏沉沉的。
可他撬開齒關時,吻就慢慢變了味道,兇狠又蠻橫,仿佛之前的溫只是為了騙放下戒心,為他自己贏來這一場饕餮盛宴。
秦箏不住想躲,可他扣在后頸的大掌按得的,力道本不容掙。
住下顎的手松開,橫去腰間一提,被帶著面對面坐到了他上,脊背抵著后的方桌,后面直接被他按在方桌上親了個夠本。
結束的時候,秦箏氣都不勻,襟被扯得松散,也腫得不像樣。
楚承稷領口也被抓得沒好到哪里去。
兩個人都愣住了。
院門輕響,估著是盧嬸子下地回來了,秦箏幾乎是跳起來跑去關門,又手忙腳地整理自己的裳。
明明是正經夫妻,但愣是像似的。
可能是那個吻有些過火了,這一晚兩人都有些不自在。
秦箏以前看小說電視以為親著親著就滾一起只是戲劇效果,可這會兒自己親經歷了,事后回憶的時候,還是有點懵。
只是一個吻而已,怎麼后來就演變那樣了呢?
睡覺的時候看了一眼依然側睡個床邊朝外躺著的楚承稷,默默拉過被子也朝里睡了。
至于半夜楚承稷出去吹了好幾次冷風,秦箏是不得而知了。
*
第二日秦箏就去后山實地考察地形,楚承稷要練組建起來的新兵,便點了幾個寨子里功夫不錯的同去。
林堯聽說了,讓馮老鬼也跟過去打下手,畢竟馮老鬼在寨子里算是對建筑工程懂得比較多的,對山寨里的地勢也悉,總能幫到秦箏。
林昭自是帶著喜鵲一道去幫忙,主要也是心,想知道如何才能在幾十丈寬的山崖之間建起索橋。
秦箏是第一次去后山,一路上林昭給介紹了不寨子里的防工事,說是上次水匪從后山突襲上來后,林堯就命人強化了這邊的機關陷阱。
秦箏蹙眉問:“后山山崖上的橫木還沒燒掉?”
林昭擺擺手:“早燒了,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寨子里多設置些機關陷阱,總歸是有備無患。”
這點秦箏倒是贊同,等后山的索道建好,祁云寨就又多了一條與外界聯通的道路,將來若是索道失守,后山的機關還能為祁云寨的第二道防線。
到了后山的山崖邊上,秦箏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片被燒毀的竹矛墻的殘骸,以及稀零長著的幾株矮灌木。
崖邊上覆蓋著的的土壤極薄,秦箏用子刨開表層的土壤,沒刨幾下就出底下的巖層。
林昭好奇問:“阿箏姐姐,你刨土做什麼?”
馮老鬼在涼抱著個酒葫蘆喝酒,聞言起耷拉著的眼皮看了秦箏一眼:“這山崖上風吹雨淋的,泥早就被沖走了,底下全是巖層。想在這里打樁子,可得費些功夫。”
馮老鬼干了二十多年修橋建路的活計,一眼就看出秦箏在那個位置刨土是想看底下的土壤覆蓋度有多深,方便挖基槽固定樁子。
他暗自搖了搖頭,鑿開巖石層打樁都不是難事,難的是如何憑空在幾十丈寬的山崖上憑空架起索橋。
雖然知道秦箏是軍師夫人,也曾救過寨子里的人,但在自己的老本行上,秦箏此舉在馮老鬼看來無非是個半吊子。
他在山寨里不知多年了,寨子里但凡要修個什麼建筑工事,第一時間都是找他。
這過元江拉索橋,他先前就已經當著林堯和山寨眾人的面說過了不可能,現在一個小娃跳出來說能修,林堯還讓他跟過來打下手,馮老鬼面子上多多還是有點掛不住。
眼下見秦箏似乎本沒弄懂修這條道的難點在哪里,馮老鬼只覺年輕娃子不知天高地厚,心底也稍稍松了一口氣。
活到他這把歲數,若是被一個年輕娃把索道修出來了,他這張老臉可就丟盡了。
秦箏似乎半點沒聽出他方才那話里的輕視和賣弄,道:“馮師傅知道如何在巖層上挖?甚好,等我測出這山崖之間的寬度后,還得勞煩馮師傅帶人在這里挖個打樁的坑槽。”
知道山崖的寬度和鐵索要承的的重力,才能更準地計算出樁子要打進底下的巖層的深度。
在巖層上鑿本來就不是易事,鑿深了無疑是浪費人力力,更浪費時間。可若鑿淺了,承不住索道來回運輸重的拉力,一切就前功盡棄。
如果索道上渡的是人,從這麼高的山崖掉下去,還得出人命
馮老鬼都快被秦箏口出狂言給逗笑了,蓋上酒壺,道:“軍師夫人口氣未免大了些,這山崖底下便是滾滾元江,如何度量?還能長了翅膀飛過去不?”
秦箏道:“我自有我的法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023 章

超甜鰥夫有三娃
【種田+馬甲+打臉+甜寵】重生后,唐九穿成了沒爹沒娘的小可憐,房屋土地都被大伯霸佔,自個兒還被磋磨成了古代版的灰姑娘。甚至差點被嫁給命硬克妻、還帶著兩個拖油瓶的男人。嘖!看她手撕渣親戚,腳踩地痞惡棍,順便撩個哪哪都順眼的農家漢子。啥?漢子就是差點成了她未婚夫的人?不!她拒絕當后媽!可是,漢子死纏爛打,軟磨硬泡,馬甲剝了一件又一件。最後,唐久久看著面前一身鎧甲頂天立地的男人,唐九覺得……后媽什麼的,都是浮雲!
108.6萬字8 38398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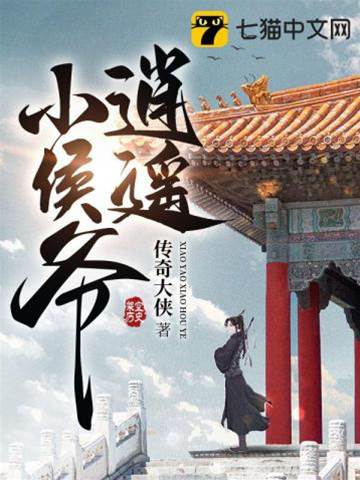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01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