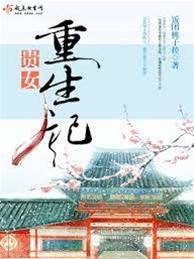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逐鸞》 第112章 第112章
十二月底, 大捷的燕軍浩浩開進京都。
柳絮楊花一般的雪花紛紛揚揚飄灑在廣闊的天空中,穿烏黑鎧甲的軍士如暗河奔涌在寬闊的京都主道上。
京都這一日萬人空巷。
不論是布百姓還是錦貴族,都自發地匯聚到了主道兩邊,歡迎這支匯聚了游牧民族和燕人的軍隊。
謝蘭胥一騎當先, 旁邊是頭戴帷帽的荔知, 再之后是此戰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荔慈恩兩兄妹,以及以阿奢奇為代表的草原十三部。
瑯琊郡王自不必說, 芝蘭玉樹, 宛若其父。準王妃巾幗不讓須眉, 自鳴月塔之戰后,又聯手瑯琊郡王再次大勝, 即便頭戴帷帽,也能過搖曳的薄紗一窺其清麗姿容。
街邊百姓被其肅殺的氛圍所染, 一臉崇敬地注目觀看, 不敢有毫喧嘩。
到了皇城腳下, 大軍停留在皇城外等候封賞,按道理, 皇帝應該接見此戰的主要人員,聽取他們陳述戰爭的發展,以及最后的得失結果。然而謝蘭胥他們等了許久,等來的卻是一道論功行賞的圣旨。
雖然白沙一役平定了草原十四部, 將燕國的國威傳揚至關外草原之上, 但圣旨上的獎賞,卻乏善可陳。得到爵加封的也不過是歸降的十三部首領, 以及和談有功的荔慈恩一人, 作為主將的謝蘭胥, 只獲得了一些金銀賞賜。
皇帝針對的冷淡, 明眼人一目了然。
宣旨的小太監讀完圣旨,對荔慈恩說:“你就是主持和談的荔慈恩”
“正是民。”
小太監看了一眼,涼涼道:“皇上要宴請十三部落的首領,屆時還要你居中翻譯。勞駕你跟首領們說上一聲,跟咱家走吧。”
Advertisement
荔慈恩愣住,下意識看向荔知。
荔知點了點頭。
心里門兒清,皇帝這是有意分化他們。那位九五之尊,已經覺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脅。
“……民接旨。”荔慈恩放下心來。
荔慈恩和草原十三部的首領進宮赴宴去了,其他人則打道回府。
沒有慶功宴,沒有歡迎儀式,甚至連皇帝的面都沒見上一面。謝蘭胥這支得勝之師,境忽然尷尬了起來。
但謝蘭胥不委屈,因為他知道,京都里有的是人替他委屈。
幾日后,京都中已經因此流言霏霏。
皇帝此舉,雖是為了晾一晾謝蘭胥,卻也同時涼了許多有心為大燕建功立業的武將之心。就連百姓之中,也對此頗有微詞。
謝慎從已經了陣腳,只要錯了一步,離步步錯也就不遠了。
……
數日后,紫微宮中。
皇帝在早朝上發了一大通火后,急召王宮。
謝慎從在書房里等了許久,王才拖拖拉拉地進了宮,等到見了滿酒氣,冠不整的王,謝慎從心里著的火蹭一下就冒了起來。
“你看看你現在什麼樣子!”
謝慎從隨手抓起案上一本奏折向他用力擲去。
謝韶呆呆地站在原地,任由堅的奏折砸在上。
“為了一個人,你就連太子之位都不想要了嗎!”謝慎從怒聲道。
高善袖手站在一旁,眼觀鼻鼻觀心,宛如一沒有生命的雕塑。
即便是提到太子之位,謝韶依然一臉消沉和麻木。從踏紫微宮起,他就沒有抬眼看過座上的謝慎從一眼。
“兒,你聽聽京中的風言風語,他們眼中可還有你這個王的影子”謝慎從痛心疾首道,“你如此作踐自己,你母妃見了,該有多心痛”
Advertisement
聽到母妃二字,謝韶的眼神了。
“……有父皇陪著,便不會心痛。”謝韶說。
“你是唯一的孩子,也是朕最看重的兒子,朕知道,此前一段時間,對你過于嚴苛了。但那也是因為朕盼你長大心切,你的那些兄弟們,沒有一個好相與的啊!父皇在時,還能護你一二,若父皇走了,你又該如何自”
“……”
謝韶又開始神游天外。
謝慎從看得心頭火起,但不得不抑怒火,他的那些個兒子,能與謝蘭胥抗衡的已經只此一個。
“朕知道你的心結在什麼地方,自從朕發布了那道賜婚旨意,你便悶悶不樂。”謝慎從說,“朕現在才看清瑯琊郡王心所圖甚大,不堪信賴。荔知是個好姑娘,指給瑯琊郡王的確倉促了。只不過瑯琊郡王如今勢大,朕即便是想收回命,時機也不甚……”
謝慎從說得晦,意思卻很明顯。
荔知在他眼中并非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可以轉贈的寶,誰讓他高興了,他就能把這寶贈與誰。
謝韶聽懂了他的言下之意,冰封的苦痛與憤怒一時高漲,袖中的雙手漸漸攥了。面上也顯出了痛苦之。
謝慎從還誤以為是自己的激勵起了作用,讓王重新升出斗意。
“瑯琊郡王現今不過是尚書左仆,從今日起,朕便封你為尚書右仆,你又是親王之,比瑯琊郡王高出一頭不止。能不能如意,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謝慎從擺了擺手,說,“回去拾掇拾掇自己,明日上朝時別人看輕。”
謝韶沉默不言地離開紫微宮后,謝慎從覺心里落下了一塊大石頭。
他自認有識人之,謝韶從小便被他重點培養,心才智都有,端看他能做到哪一步。
如果荔知能激起他的斗意,那便給他做個侍妾也無妨。
反正一開始的賜婚,也只是想著用一個出有污點的子牽制謝蘭胥。
只要謝韶能夠如他所愿,和謝蘭胥斗起來,他便又能高枕無憂十幾年。
如此,一個罪臣之又算得了什麼。
他正為自己的聰明才智得意,忽然猝不及防打了個噴嚏。
有了今年夏日的前車之鑒,他特意讓宮人在紫微宮各燒足了碳,讓各室暖如初夏,即便外出,也是裹著厚厚的皮草,懷里揣著手爐。
如何能著涼
他略有狐疑,但并未放在心上。
然而——
三日后,謝慎從便一病不起了。
本以為只是一個小風寒,卻不想發展到纏綿病榻的程度。
怡貴妃為了爭寵,走了侍疾的鹿窈,偏要守在龍床邊近伺候。但怡貴妃養尊優的人,哪里會照顧人旁的倒還好,能學的學,能忍得忍,怡貴妃是真的一顆心掛在皇帝上,所以一開始,倒是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直到皇帝某日一咳,一口濃痰飛到了怡貴妃的上。
謝慎從之前沒覺得咳出痰有什麼——誰不吐痰他當地的時候,一日要吐十幾口痰,那鹿昭儀,侍疾的時候總是用手來承接他的口痰,還有那些宮人,也從未因此皺過眉頭。
邊沒人敢表現出惡心,謝慎從也就忘記了此舉的惡心。
他是九五之尊,一國皇帝,別說口痰了,便是大小急,那都是龍尿龍藥。
然而,當那口痰飛到怡貴妃的子上時,怡貴妃嫌惡至極的尖劃了破紫微宮的平靜。
隨之而來的,便是從皇帝破碎的自尊心上升起的然大怒。
虛偽——
惡毒——
薄——
故作姿態——
謝慎從所能想到的符合怡貴妃此舉的惡言惡語,都毫不吝嗇地扔給了這個陪伴他多年的人。
當慘白著臉的怡貴妃——不能再怡貴妃了,當剝奪了封號,降為修儀的蘇嫦曦被拉出紫微宮時,謝慎從連一個多余的眼神都沒有給投去。
在他看來,是自己多年的寵喂了狗。
在他看來,他不可能對不起別人,只有別人對不起他的份。
他用力地咳了咳,嚨里總像堵著什麼東西,但偶爾能咳出痰,偶爾又不能。
“太醫院養的是一群飯桶嗎!說是風寒,怎麼這麼久了還沒有一點好轉!”
謝慎從不適,心也不好,他一暴怒,殿便呼啦啦跪滿一群宮人。
“皇上,可要太醫院院使來看看”高善躬問道。
謝慎從一邊咳,一邊點頭示意。
“還有……鹿昭儀來。”他說,“患難才可見人心啊……”
高善不置一語,低頭退下了。
殿,又響起了痛苦的咳嗽聲。
不一會,鹿窈便來了。
聘聘婷婷地坐在龍床邊,對面蒼白,衫不整的他沒有毫輕視,即便他沖著的手心吐出濃痰,的眼中也只有心疼。
“娘娘——”
高善遞來剛煎好的湯藥。
濃烈的中藥草苦味飄在空氣中,里里外外放置的炭盆散發著熱氣,蒸騰著空氣中的苦。
鹿窈接過高善遞來的藥碗,用湯匙輕輕攪拌著烏黑的藥,緩緩吹著。
翹著小指,指甲上涂著鮮紅的丹蔻,如本人一般鮮。
謝慎從不看出了神。
等到藥的溫度差不多涼了,鹿窈用湯匙喝上一口,確認溫度怡人,才耐心地服侍他喝下。
比起蘇嫦曦那個涼薄虛偽的人來說,不知好了多倍。
“窈兒啊……”
謝慎從握住的手,深道:
“這兩次生病,你待朕都全心全意,朕一直看在眼里。如此品行,區區昭儀之位怎可配你今日起,朕封你為德妃,嘉獎你之德行。”
鹿窈又驚又喜,連忙要跪下行禮謝恩。
謝慎從將其攔在邊,繼續道:
“這里沒有旁人,你我無需多禮,如民間尋常夫妻即可。”
鹿窈一臉地偎依在謝慎從邊。
“待朕好了,還要與你再生個兒子。”謝慎從輕拍著鹿窈的肩膀,甜言語道,“到時,這偌大的家產,也要與他繼承。”
“那皇上可得快些好。”鹿窈抬起頭,仰著九五之尊,嗔道,“臣妾都快等不及了。”
謝慎從最吃這套,他哈哈大笑,十分快,尚覺自己年。
高善沉默不語,立于簾下。
闔宮宮人也都垂頭不語,敬畏沉默。
他沉醉于天下無敵的幻象之中,渾然不察,懷中之人眼底的冷漠。
皇城之外。
謝蘭胥坐在窗臺下,同一榻的荔知上披著謝蘭胥的大氅。
兩人都在賞雪。
窗外的雪,仿佛永遠不會停歇。
一片片,一顆顆,仿若春風中飛揚的小的公英。
漫天的新生命。
“一切就要結束了。”謝蘭胥若有所指。
荔知著那飛揚的碎末。
“……是啊。”
猜你喜歡
-
完結483 章

休了那個陳世美
大閨女,「娘,爹這樣的渣男,休了就是賺到了」 二閨女,「渣男賤女天生一對,娘成全他們,在一旁看戲,機智」 三閨女,「娘,天下英豪何其多,渣爹這顆歪脖子樹配不上你」 小兒子,「渣爹學誰不好,偏偏學陳世美殺妻拋子,史無前例的渣」 腰中別菜刀,心中有菜譜的柳茹月點點頭,「孩兒們說得對! 我們的目標是……」 齊,「休了那個陳世美」
89.7萬字8 17036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24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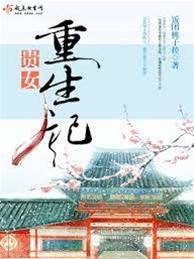
貴女重生記
大晉貴女剛重生就被人嫌棄,丟了親事,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將未婚夫賣了個好價錢!被穿越女害得活不過十八歲?你且看姐佛擋殺佛,鬼擋殺鬼,將這王朝翻個天!小王爺:小娘你適合我,我就喜歡你這種能殺敵,會早死的短命妻!
62.1萬字8 1704 -
連載773 章

洞房夜,給禁欲殘王治好隱疾后塌了床
穿成丑名在外的廢柴庶女,洞房夜差點被殘疾戰王大卸八塊,人人喊打! 蘇染汐冷笑!關門!扒下戰王褲子!一氣呵成! 蘇染汐:王爺,我治好你的不舉之癥,你許我一紙和離書! 世人欺她,親人辱她,朋友叛她,白蓮花害她……那又如何? 在醫她是起死回生的賽華佗,在朝她是舌戰群臣的女諸葛,在商她是八面玲瓏的女首富,在文她是下筆成章的絕代才女…… 她在哪兒,哪兒就是傳奇!名動天下之際,追求者如過江之卿。 戰王黑著臉將她抱回家,跪下求貼貼:“王妃,何時召本王侍寢?” ...
142.7萬字8.18 150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