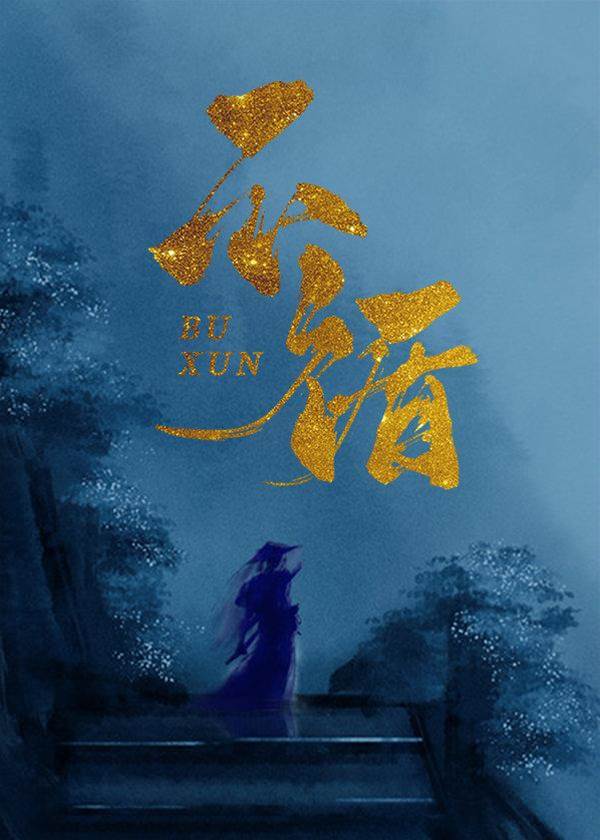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被庶妹替嫁后》 第41章 第四十一章
今日坐的這把凳子像是扎了釘, 挪前挪后都坐不安穩,頻頻用余去瞄韓祎那。
在看別人,別人自在看他。兩人的眼神撞在一, 前者鬼鬼祟祟,后者卻高深莫測。
韓祎眼皮子了, 郁桃眼瞧著他的作, 就指著這人能從眼神里瞧出點楚楚可憐, 然后大發慈悲將荷包還給。
終于,男人掀起眼睫, 沉默的看向。
郁桃低下頭用手抹了把應當掛著荷包的位置,然后又抬起頭可憐兮兮的眨了下眼睛。
韓祎安靜的坐著, 看了眼的手, 落在那雙有些發紅的眼睛上, 眉漸漸蹙起。
“眼睛疼?”
眨眼睛的作一瞬定住, 又慢慢瞪大,帶著點不可思議。
但從韓祎靜默的神來看, 顯然他這句話并非玩笑,甚至帶著點難得的關切。
啥?眼睛疼?
我這麼明顯的暗示您讀不懂。
卻來關心我的眼睛疼不疼?
提起勉強笑了下, “是呢,風迷了眼睛。”
得了答案, 韓祎便收回了落在上的目, 自去瞧遠的風景。
在他面前, 矯慣了,眼睛眨吧幾下,帶著些姑娘家慣有的小心思, 但不說, 他也只能猜到微末。
“唉......”一口氣送出氣, 心底那點希冀徹底沒了,索往椅背上一靠,垂頭喪氣的捉來案幾上的茶杯,抿了一小口。
這一聲嘆息極長,韓祎手去去瓷壺的手頓了下,側頭去看。還從未見過這麼喪的樣子,像棵被霜雪乍住的白菜似的,瞧著玲瓏剔,實際上早就被打的蔫兒了。
郁桃干了這杯茶,在木把手上蔫了一小會兒,腦子里面像是有一千個小人在打架,發被抓撓,一面是‘要不算了,不一定韓祎就認識那是韓偉。’另一面瑟瑟發抖‘說不定他已經看了那幅畫,若是稍一查探,事不久敗了?’
Advertisement
安逸的是畔的人,苦的卻是。郁桃‘唰’站起,因為作稍有些魯,實木椅子在船板上出糙響。
兩人皆是抬頭。
韓二公子面帶疑:“郁姑娘,怎麼了?”
郁桃環顧四周,小郡主與蘇柯遷一圈人著實離的有些遠,不然有他們在旁邊稍微顯得熱鬧些,也不至于境地如此尷尬。
這天下韓姓不,平城韓家是韓,京城韓尚書是韓,閆韓侯府牽頭帶著‘閆韓’卻偏偏也姓韓。
心口打著鼓,連腳下都站不住。
郁桃手搭在翹楚腕間,往前挪了兩步,停下來。
天尚不算晚,但端午要的彩頭已經看完了。
“翹楚。”朝翹楚了眼睛,“祖母是不是囑咐了,龍舟賽完早些回去?”
“啊?”翹楚會意,迅速道:“啊,正是呢,老夫人說謝過郡主恩典,讓您早些回去呢。”
“那這樣......”郁桃帶著幾分惋惜的神轉過頭,“多謝世子今日的款待,阿桃恐怕要先走了。”
韓祎目掃過去,瞧半響,垂首喝茶之際,淡淡應了。
但要的還是那只香囊罷。
離開不過是為討要荷包的借口,若說在沖向世子夫人這條披荊斬棘的路上,郁桃時時刻刻都在后悔,但都比不過此刻。
“我記著還有......”
郁桃里打著磕絆,瞧著男人平靜的臉,一字一字小心翼翼的往外撂:“早上世子從我這兒拿了只荷包,只是,旁的荷包送給世子便罷,只是嗯、那只是我母親在今年生辰親手做給我的......”
韓祎手中茶碗的碗蓋一落,發出脆響。
他一手松松兜著茶碗,眼著郁桃,“就這麼只荷包,用的著你在這想這麼久?”
Advertisement
郁桃訕訕笑到,強著心口忐忑不安的蹦跶,“哪里的話,畢竟是世子看上的荷包,也不敢輕易討回來。”
看了眼在一旁表快要維持不住的韓二,手在掌心掐了下,出點笑,“只是想著,世子什麼樣的荷包沒見過,若是我要回來,世子大人大量,肯定人意。”
韓祎嗤笑了聲,顛了顛手中的釉青枝白瓷杯,不知道在和什麼較氣。
“七宿,將荷包取出來。”
直到順順利利將荷包拿在手里,郁桃都有種做夢的覺。狐疑的抬起頭,著那只實實在在的荷包,覺得今日的狗男人過分的好說話。
總有些不太對勁。
荷包瞧這還是原先那只荷包,外頭的花紋式樣都未曾變過,連香味也是,只是......
下意識了,終于覺到不對勁在何。
因為荷包扁了,也輕了。
若是仔細瞧那絡子,口子上明顯比先前松伐。
這是有人打開過。
一聲悶鼓‘咚咚咚’敲在腦袋里,郁桃扯開繩,如果這個口子夠大,一副恨不得將頭塞進去用眼睛挨個兒查探的架勢。
翻來覆去三四回,里面除了香料外,還是香料。
姻緣符不在,平安福不在。
頂頂要的那張畫了人像的紙片同樣不在。
香囊上致的繡圖被拽鄒的一團,郁桃的臉白了兩分,抬起頭,有些干的開口,“我里面的東西呢?”
韓祎指尖懸著杯蓋,看一眼陡然變化的臉,繼而目收回,用碗蓋濾著茶水往瓷杯斟茶:“什麼東西?”
郁桃頓了下,隨著韓祎合蓋斟茶那般慢條斯理的作,話到邊卻生生停下。
瓷杯斟滿,茶碗放下,端起白瓷盞,白霧從他臉上彌彌升起。
隔著白霧,他定定瞧著失語的模樣:“連里面放了什麼都忘了?”
郁桃心里打著鑼鼓,是有些出殯意味的哀樂,幾乎是破釜沉舟的語氣,“兩、兩張符,還有......一張、一張小紙片兒...撕下來......”
手上比劃著,出口的字句若是放在紙上,字和字中間的長度約莫好幾寸,像是出口極其艱難一般。
“兩張符......”
韓祎笑了下,“確實有。”
郁桃咽了下口水,目希冀,試探:“那另外一樣呢......”
韓祎的眸中流過一剎的,他瞧著,邊那抹笑漸冷,也似有似無,“哪一樣?”
郁桃眼神微微閃躲,再一次張的咽下口水,小心開口:“就是一張疊一團,上頭畫了個人,旁邊寫了幾個字兒......”
說完,韓祎卻并不出聲,只沉默著直直的定在上,而目中的審視漸漸浮于表面。
“......就是兩個字,我也記不清楚......”
郁桃聲音越來越小,嚨發,“若是沒記錯,應當是‘韓’什麼......”
邊的笑終于收斂,男人眸沉沉,似能將云層中的太一并遮蔽,天更暗。
“你藏著這畫做什麼?”
幾分興師問罪的口氣讓郁桃愣了下,但很快的心口因瞬間意識到眼前的人必然是瞧見了那幅畫而慌張跳。
睫了下,眼睛掃了掃四周,忙中找到一個不章理的借口:“可能是誤會,那幅畫其實......”
韓祎一聲嗤笑打斷,眸子睥過去,“郁姑娘可別說,那畫上的人是我。”
“怎麼可能呢!”
話頭被截住,一滴汗水從浸后背衫,郁桃眨了下眼睛,任胡謅:“那畫上的人韓偉,與世子的名諱雖然差之毫厘,實則謬以千里,豈是畫上的人能相較的?”
“哦?”韓祎目邊掛著笑,語氣淡淡,“我的真名不是韓偉嗎?”
懸在頭頂的劍徑直朝郁桃砍來,但是還想垂死掙扎。
韓二公子再怎麼好奇的心中抓,從韓祎表的微末,也察覺到事態的不一般,從‘那幅畫’開始便將椅子后推,避禍保命。
郁桃往前兩步,迎上韓祎的視線,牙齒了下,勉力出誠摯的神。
“世子有所不知,我打小學問不大好,認字兒認半邊兒,從前是我眼拙,將名字認錯了。只是這畫確實并非出自我手,我和庶妹的事,世子在平城應當聽說過,那日我從手上翻到這幅畫,想著有朝一日當著眾人的面兒,狠狠辱一番......”
“只是......”眼神飄忽著,“只是那畫確實不堪目,拿出手怕是眾人也不相信是出自郁苒之手,所以才作罷......”
韓祎卻不應,輕描淡寫的瞧著江面,手指在瓷杯上一下一下的輕叩著。
郁桃心中沉沉的嘆出一口氣,最終出四指,用差點連都要相信的口氣沉重道:“世子不信,那我便起誓,若有半句虛言,必定天打.......”
不待‘雷劈’二字落下,晴天里一道霍閃落下,如一把利斧,將沉的天穹劈開半面。
郁桃張著,眼瞧著天,呆住了。
“天打什麼?”韓祎臉朝著江面,分明角勾起,神卻諱莫至深。
郁桃了下頭,里無聲的吐出剩下兩個字。
然而,未等最后一個字說完,天上一道悶雷平地炸響,震得河堤柳樹枝條四,沛河波紋四起。
郁桃一臉驚恐的抱住翹楚的手臂。
這下,徹底噤了聲兒。
片刻沉默后,眾人因這突如其來的天雷而紛紛議論起來,四周人聲鼎沸。
而落在郁桃耳中的卻只有,瓷杯與桌面相合的聲音,以及眼中瞧著,茶水在杯中輕晃,漾落在案幾上,在壑里浸潤深的痕。
一片袍角從面前過,極淡漠的聲音拂耳。
“七宿,將東西給。”
作者有話說:
講個故事,海綿寶寶和派大星會在一起一輩子,他們變了彼此的朋友。
猜你喜歡
-
完結195 章

半城風月
她來自鐘山之巔,披霜帶雪,清豔無雙,於"情"之一事,偏又沒什麼天賦,生平最喜不過清茶一杯,看看熱鬧. 都說她年少多舛,性格古怪,其實她也可以乖巧柔順,笑靨如花. 都說她毒舌刻薄,傲慢無禮,其實她也可以巧笑倩兮,溫柔可親. 不過—— 她·就·是·不·樂·意! 直到那天,她遇見了一個少年. 半城風月半城雪,她一生中的所有風景,都因他而輝煌了起來. …
42.6萬字8 4584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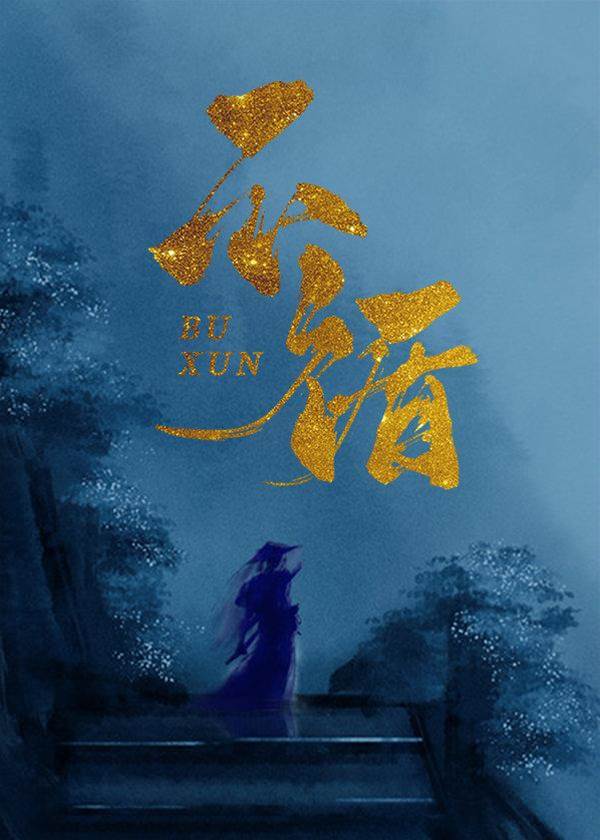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45 -
完結727 章

繡南枝
前世遭渣男陷害,她被活活燒死,兄父剖肚點燈,她恨。再睜眼,重回家族危亡之際。她染血踏荊棘,走上權謀路,誓要將仇敵碾碎成沫。素手執棋,今生不悔。看蘇家南枝,如何織錦繡,繡江山……
123.6萬字8 237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