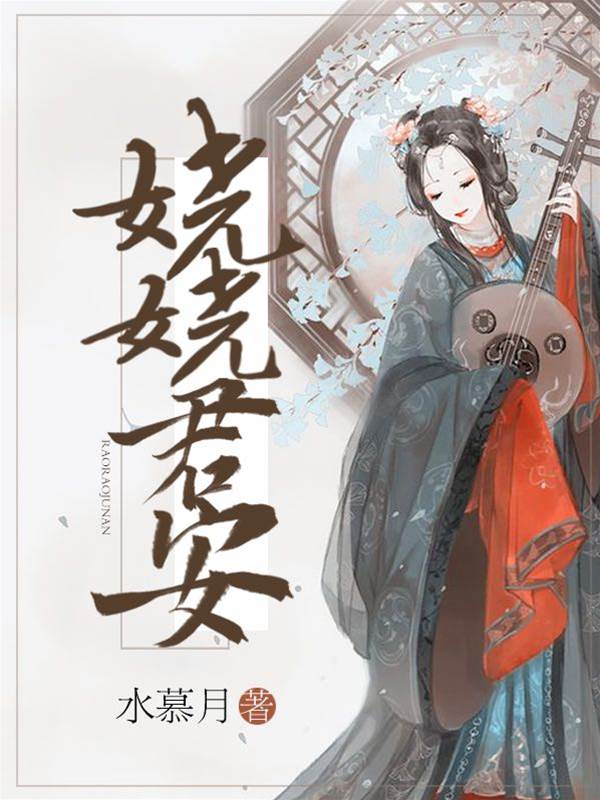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東宮美人》 第136章 壓歲錢
“嬪,嬪妾……”南殊搖頭:“嬪妾不能說。”
輕輕的打了個酒嗝,說完之后將頭埋在他的懷里。
太子殿下的手已經順著領口進去了,再這樣下去一準要出事。
長靴底下,南殊的腳趾蜷在一起。心口跳的越發厲害,咬著才忍住嚨里的聲音。
“孤給你太醫。”太子殿下把玩了一會兒,見到底是放開了。
瑩瑩燈火之下,像只鴕鳥一樣躲在他懷中。
雪白的頸脖像是窗外的雪,白的謊言。唯獨那一雙耳尖通紅的,勾人心魄。
太子殿下指尖勾弄著的耳垂:“心口疼可是大病,孤可瞧不好。”
南殊本就是半醉醉,心口疼也是扯謊,哪里能太醫?
佯裝迷迷茫茫的睜開眼睛,卻是看見太子殿下那帶著笑意的目。
他彎下頭,指尖落在的耳垂上,輕輕的撥弄著像是在哄:
“告訴孤,哪里難?為何難?”他以為懷中的人徹底醉了。
Advertisement
想盡法子來哄說真話。
可不,酒后出真言。
甜言語聽多了也沒那麼珍貴了,但是真心話往往都是最難的。
南殊知道殿下想聽什麼,也知道說什麼對自己最有利。
殿下既然給了機會,自然是要好好演下去。
“嬪妾不,不要……”揪住殿下的袍哀求他:“殿下不要太醫。”
“你說。”他難得的好脾氣,“你回答問題,孤就不。”
他手將輕輕的擁懷中,兩人的極近,連著呼吸都纏繞在一起。
南殊紅著臉,乖巧的坐在他懷里,一雙含著水霧的雙眼癡癡的看著他。
“嬪妾是,是見不到殿下才難的。”不敢看他,眼睫抖著,語氣也顯得溫和了下來。
像是刺猬出了肚子,坐在懷中滿臉忐忑,但還是小心翼翼的吐出了心神:
“今,今日除夕,要跟家人在一起守歲,來年才能順遂如意的。”說到這里,忽然委屈了起來:
Advertisement
“南殊沒有家人,每年這個時候都是一個人。可是今年不同啊,今年有了殿下……”
“我以為………以為能跟殿下一起過的。”
一臉醉氣熏天的樣子,委屈的聲音都帶著哭腔。
可心中卻依舊是不可置信,大年三十的殿下真的來了?
除夕守歲,整個后宮殿下都沒去,而是在這兒。
窗外的雪落聲靜悄悄的,南殊心口跳的啪啪作響,抱著殿下的手也放了下來,幾乎算是絕開口:“可是,殿下去,去陪旁人去了。”
“孤沒有陪別人!”
屋寂靜,顯得他這話有些急促。
酒席一過,太子妃醉臥不醒。
他下意識的便過來了。
九云臺中宴席沒結束,他寧愿在這等著,也沒想過去旁人那兒。
太子殿下眉心皺著,他并非不知道對他而言這是危險的。
如劉進忠所言,他不該。
能偏寵不能獨寵,能寵卻不能。
他雖不承他對了心,但若還是要選,他今日還是會來。
“孤沒有陪別人。”他著眉心強調了一句。
“那……”南殊不傻,連忙追問:“那……那殿下是特意來陪嬪妾的嗎?”
復雜的目落在臉上,太子殿下深深的嘆了口氣,反駁道:“不是。”
南殊不信,還要問。
太子殿下像是妥協,又像是隨意的從袖中掏出只香囊給。
“這是什麼?”香囊下墜這個玉玦,南殊想要仔細看,太子殿下手接過。
他低下頭,指腹落在腰間,將香囊寄在上。
語氣淡淡的,不知喜怒。
“歲錢。”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143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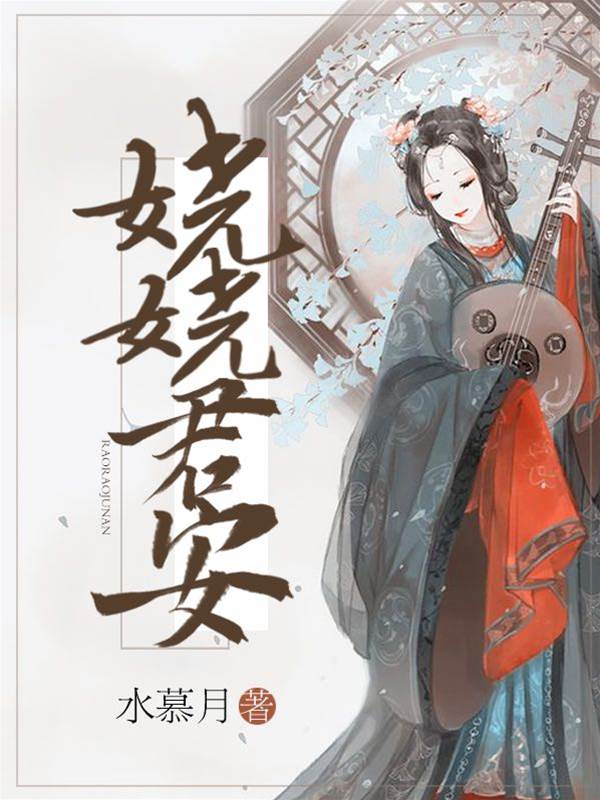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1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4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