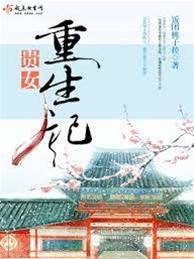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晚庭春》 第 38 章 第 38 章
梁霄怔住,他呆呆著明箏,見因著惱怒而俏麗微紅,整個人倒多了幾分生氣。眼中毫不掩飾的鄙夷令他有一瞬心虛。
轉念,他驟然惱恨起來。
他這樣低聲下氣求了,他把自己為男人的尊嚴的都舍出去了,他都已經委屈了安如雪,把暫時送到莊子上去了,到底還有什麼不滿意?到底在生什麼氣?不就是在下人面前丟了點臉嗎?夫為妻綱,他怎麼就不能發作了?
此刻滿屋子的人目齊刷刷盯在他上,他當眾跪求,給足臉面,損失掉的面早就找補回來了,竟還說什麼,和離?放妻?
梁老太太見兒子被打得怔住,早就心疼得不得了,揮開閔氏的攙扶幾步踏上前來,“明箏,你這是干什麼?他好生生的哄你勸你,你這樣做,可就是有些不識好歹了!”
那嬸娘附和道:“不錯,明箏,長輩們疼你,霄哥兒敬重你,由得你發泄心里頭的怨氣,可你不能沒規矩失了統,霄哥兒再怎麼和,他也是你男人,是你的天,要罰他罵他,自有我們這些長輩在呢,哪里就到你手往他臉上招呼?”
閔氏不敢吭聲,只是暗中扯了扯嬸娘的袖子,勸別再刺激明箏。
梁霄被母親攙扶起來,語調悲切地道:“阿箏,你就那麼瞧不上我嗎?婚八年,便是我近來犯了糊涂,細數從前的日子,我也不曾虧待過你吧?”
明箏淺笑,“二爺說笑了,您豈會犯糊涂?是明箏無福消您的好,各有立場,話不投機,二爺不若高抬貴手,放過明箏,也放過您自個兒吧。”
回朝明太太行了一禮,“娘,兒的心意已經盡述,再無旁的可說。”
Advertisement
明太太下復雜的心緒,點了點頭,“這里有我,你去吧。”
明箏側從梁霄母子畔走過。
他試圖拉住,被在氣頭上的梁老太太按住。側而過的一瞬,往事諸般洶涌,那些恩愉悅的日子,如黃沙在曠野吹過,出手去捕捉,掀開手掌,卻是空無一。
八年夫妻,在心里難道就半點不值得留麼?
明箏沒有回頭,簾子卷起又落下,緩步朝自己住的院落走去。
天已然黑沉下來,燈火幢幢,照壁上落下花樹的影子。風吹來的一瞬,明箏彎起角,笑了出來。
從未有過的輕松、愉悅,盈了滿懷。
說出來這個決定,仿佛整個人生都變得更明朗了。
不是為了嫁人活著。
婚姻,是為了讓人更幸福的活下去。如若不能,那就不必擁有。
后跟著的瑗華瑗姿擔憂地著自家主子。當世沒有幾個子,會向夫家主提出放妻,明箏走出這一步,完全將過往端莊賢惠的風范顛覆。
麗景軒中,眾人在勸明太太,“孩子一時意氣,說出來的氣話怎能當真?梁家放妻事小,明箏清名蒙污事大。說出這等有違法度綱常的氣話,給人聽了去,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就不怕被扣上不安于室的罵名?明太太也勿要太縱著了,由著子胡來,這像是個出嫁多年的夫人該做的事嗎?”
梁霄立在廳心,臉上火辣辣的疼痛逐漸消減,連適才心底的惱恨也一并在消退。他要找到明箏,去問一聲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折騰,好好地日子不過,非要鬧出這些是非給人瞧了笑話。到底為什麼不滿意他不滿意梁家,這麼多年,他哪有虧待過?
Advertisement
他轉就朝外走,梁家他來得雖不多,也是門路,徑自闖出院落,就朝花園更深扎。
遠遠一聲悠揚的琴聲,劃破靜夜在花香馥郁的空氣中漫開。
跟著千軍萬馬一般的節奏,仿佛征途中的將士踏著湊的鼓點而來。
明箏原彈了一手好琵琶的。
婚前某次見面,隔窗聽奏一曲桃夭。輕快利落充滿愉悅的節奏令他心跟著明快不已。
婚后再也沒有彈過琴,琵琶月琴都被堆到閣中去,在塵封的一角沉默地祭奠著那些快樂的時。
面前就是小院輕掩的門扉,就在其間,梁霄出手——下一瞬有人扣住他的手臂,將他死死拖開。
太湖石堆的假山前,梁霄下上挨了一拳。
他轉過頭,抹掉角的跡,眉眼狠戾地問:“你干什麼,明軫?你們不要欺人太甚!”
明軫揪住他前襟,冷聲道:“到底是我們欺人太甚,還是你欺人太甚?我姐姐是什麼子,是什麼人?你得如此,寧可拼卻名聲不要,也要與你分開,你不自省自己的錯,竟還好意思說什麼‘不嫌棄’?到你嫌棄我姐姐麼?當年你腆著臉來求娶,我就瞧出你不是什麼好東西,可給我瞧中了吧?”
梁霄本就一肚子氣,想找明箏理論未,倒被個比自己還小兩三歲的舅子給打了一頓,他氣呼呼地推搡對方,大聲斥道:“我不好?我再不好,也是你姐夫!是你爹娘點頭首肯,收了我們家聘金,奉上四十多抬嫁妝,把閨陪送進門!我再不好,也是朝廷四品衛指揮僉事,是勛貴之后,承爵的嗣子!倒是你,你算個什麼東西,憑你也配來跟我說話?”
一聲悶響過后,梁霄右臉跟著挨了一拳,他吐出口中的水,靠在那假山石上,裂開笑了,“怎麼?惱怒?你瞧不上我,你姐姐可瞧的上呢,別看鬧脾氣跟我提什麼和離,轉回頭,不定怎麼后悔痛哭反轉過來求我呢。過往這麼多年,把我伺候得服服帖帖,你當是什麼天香國貞潔烈呢,在床上還不是被我……”
“梁霄,你不是人!”明軫揪住他襟,將他整個人提得離地半尺,“我殺了你,我殺了你!”
“住手。”
遠遠一聲呵斥,兀自笑著的梁霄變了臉。
甬道另一頭,承寧伯梁輕和明思源并肩立在那,已不知來了多久。
梁霄心里一驚,自己適才說那些氣話惡話,豈非都給岳父聽了去?
梁輕快步走過來,低聲斥道:“霄兒,胡說什麼?還不給你岳父大人致歉?”
明軫松開了梁霄,垂頭喪氣立在原地,知道父親定會教訓,他也破罐子破摔,決心認罰。
明思海卻久久未曾說話。
梁輕心中忐忑,含笑道:“思海兄勿怪,年輕人話趕話爭執起來,失了分寸,他心里定不是這麼想的。梁霄,還不給你岳父賠罪?”
梁霄作勢要行禮,明思海擺了擺手,“罷了。”
梁輕見他不追究,長長舒了口氣,“還不謝你岳父海涵?”
“岳父,我……”
“梁世子,”明思海負著手,沉沉開口,“這些日子,暫先不必來了。”
梁輕笑容一頓,聽他緩慢說道:“你在軍營所犯之事,我會向吏部的人求證,若你有一字蒙騙,不盡不實,這件事,我都不會再管。”
說罷,朝梁輕點點頭,“伯爺恕罪,明某便不遠送了。”
梁輕滿心狐疑不定,聽他這意思,像是不打算為梁霄爭取了?
他老糊涂了不?小夫妻吵個,芝麻綠豆大小的事,至于把兩家幾十年分拋之不顧?姻親姻親,早是拴在一繩上的螞蚱,梁霄出了事,他明家能獨善其?
思慮間,明思海已經踱出步子走了開去。小廝含笑守在一邊兒,做了個“請”的姿勢,“梁伯爺,梁世子,這邊請……”
**
“天殺的不識好歹的東西!”馬車里,傳出陣陣斥罵,伴著噎噎的哭聲。
梁老太太手里著沾了藥的帕子,正為兒子小心拭著傷,“明軫這小王八蛋,敢下這麼樣的死手打我兒,回頭定要他明家上下好瞧!”
“行了!”已經哭罵了一路,梁輕早就聽煩了。
梁輕此時看見梁霄垂眉喪眼的模樣就氣不打一來,“在家里說好了,凡事大局為重,明箏在宮里跟各家院有關系,為你求求走走路子不好?明思海再不濟,也是吏部尚書簡詢的老師,他但凡愿意替你說句話,都比咱們無頭蒼蠅似的跑斷強,不爭氣的東西!”
梁老太太抹了把眼睛,惱道:“您是伯爺,往上數三輩,老祖宗是陪□□打天下的功臣,百年勛貴傳承至今,怎能滅自己威風漲他人氣焰?論關系人緣,您比他明思海短了什麼不?再不濟咱們家也是出過娘娘的人,皇陵里還躺著您親妹子呢,那可是皇上的枕邊人,您去求一求,難道比不得一個后宅婦人說得上話?我就偏不信,咱們家離不得明箏!”
“混賬!”梁輕咆哮道,“就是你這麼驕縱,袒護,才養出了這麼個逆子!你聽聽他適才說的都是什麼話,人在明家地頭上,把人往死里頭作踐,你當明思海沒脾氣?早年跟皇上斗氣,這廝稱病十二年不上朝,你瞧瞧皇上罷了他職銜沒有?說過他一句重話不曾?要不說你頭發長見識短,分不清輕重緩急,眼前都要火燒眉了,還在意那麼一星半點的臉面?我你跟著來,是你護著這廢的?你們娘兒們,哭一哭,勸一勸,好話多說說,至于是這個局面?”
他氣得腦袋疼,抬手捂住額頭,“等著吧,等吏部的結果出來了,丟削爵,屆時你們娘兒倆就快活了。”
“爹,真有這麼嚴重嗎?”梁霄到底還是在意自己的前途的,在這事上,他比老太太張。否則也不會愿意幾次三番地下跪去求明箏回心轉意,比起尊嚴,自是前程更要。
“廢!”梁輕想到他做的糊涂事就暴跳如雷,隨手抓了個墊朝他擲過去,“連個人都辦不下來,你算什麼男人?我問你,你打算怎麼置莊子上那賤貨?”
“我……如雪……”梁霄支支吾吾,送安如雪去莊子上暫住只是緩兵之計,原想等把明箏接了回來,再慢慢磨的子,等時機,再把安如雪接回,此時父親一問,他倒不敢說真話了。
“沒用的東西!一個西夷人手里頭搶的爛貨,也值得你寶貝這樣?簡直丟我承寧伯府的臉!”
梁老太太默了一會兒,聽到這里便坐不住了,“你還怪兒子?不是你打的好樣子,你兒子會跟著學?庶長子天天杵在眼皮子底下,我給人笑話了一輩子,你倒沒事人兒一般,繼續風流快活你的,難道你藏在家廟那個不是爛貨?上個月初五說是外頭喝酒,打量我不知?那賤人徐娘半老也沒歇了勾搭男人的心,你們干了什麼丑事,我都不稀罕說!”
幾句話堵得承寧伯滿臉通紅,私事被當著小輩面前撕開,里子面子全不好看,他怒喝道:“給我閉!我梁輕還沒死呢,得到婦人兌?”
一路爭吵不休,梁家的車漸漸駛遠。陸筠騎在馬上,回后那只頗有年代的匾額。
——“明府”。
郭遜笑道:“小兩口吵架,全家出來勸了,看來沒勸和,不歡而散,打量這梁夫人,是個頗有脾氣的人啊。”
當然不是。陸筠在心底默默反駁。
是再溫不過,再有涵養不過的人了。
能氣得如此,可見梁家錯頗多。
如今吏部搜羅的罪證也差不多了,明日前傳喚,多半圣上要找他問話。
他雖不是梁霄直屬上峰,對對方的一些事也是所耳聞的。
這回只怕對梁家是個不小的打擊。
會不會宮來,向太后替梁霄求呢?
——不管怎麼做,也不到他來關懷了。
“派個人跟著,蘇薩哈的行蹤未明之前,梁霄見過誰,去過哪,本侯都要知道。”
郭遜肅容應下,想到一事,問道:“那負責看守梁夫人的那些眼線?要不要撤換了,單跟著梁霄就夠了吧?宅婦人,難道會與朝廷欽犯有什麼往來不?”
陸筠沒說話,足尖輕夾馬腹,緩慢離開了明家府前大街。過了許久,郭遜聽他低聲吩咐,——
“不用,留人守著。”
郭遜點頭,“行,那這夫妻倆,都派人盯點兒,有什麼不妥,屬下會及時稟告。”
陸筠頷首,沒有再開口。
天氣越發悶熱。回到虢國公府,浸了冷水浴,出來瞧了會兒書,正要熄燈時候,見書下卷了半幅畫軸。信手掀開來看,陸筠眉頭蹙了蹙。
畫上是個,顧盼神飛,苗條貌。旁書一行小字,寫著姑娘生辰名諱。
是前幾日陸三夫人從江南寄過來的畫卷。畫上姑娘是當地有名的人兒,出族,父兄皆在地方任職,雖尊貴不及國公府,憑著姑娘出眾的才樣貌,倒也足以襯得他。
三夫人言之切切,他仔細思量。
其實他也曾想過,在眾多貴中擇個能合得來的,只要日子能湊合著過,能讓外祖母放心便是好的。
家里頭二嬸四嬸,族里頭那些長輩,無不在為他婚事心,沒人明白為何,人已經從西疆回來了,還不娶妻是想怎麼呢?
除卻外祖母,他對任何人都沒有言說過自己深藏的那份,由著流言滿城,猜測不斷,寧被誤會龍之輩,也不曾解釋過半句。
如今決心放下心里的人,大抵,一門婚事是最好的選擇。
一來不必再牽扯眾人力,要他們為自己苦心持。二來,也不再給自己后悔的機會,借此徹底斷了妄念。
陸筠著畫軸的手收,迫自己多瞧了一會兒畫上的人。
京中脈絡復雜,理不清的人關系,他喜靜不喜聒噪,也不愿在各家之間來回周旋,娶個遠道而來的姑娘,也正適合。
丟開畫卷,他吹滅燈,在黑暗中索至枕邊。
手一片針腳細的繡花,一朵一朵,他便是看不見,也能勾勒出整幅畫面。
的里,是質地輕的綢,穿著這雙鞋走著,腳步輕緩,一步一步踏在他心間。
陸筠繡鞋,蹙眉弓腰伏在床邊。
相思一旦開始,就再也不控制。
他肩膀輕,額頭青筋跳起,汗珠自發際滲出。
他是個男人,他阻止不了這種磨人的。
是他慕的人,一旦夜幕降臨,的影子就會縈繞在他周邊。
戒不掉這令人窒息的思念。
戒不掉這沉痛無的。
不敢又百般貪,他心掙扎揪扯,理智和相互較量,何敢令人知道自己這齷齪的一面。
那些好姑娘跟了他,不過白白蹉跎年華。他這輩子都沒辦法再上另一個。
**
麗景軒中,明氏一家人沉默地坐立在稍間。明箏被人請來,步屋中,平靜地跪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483 章

休了那個陳世美
大閨女,「娘,爹這樣的渣男,休了就是賺到了」 二閨女,「渣男賤女天生一對,娘成全他們,在一旁看戲,機智」 三閨女,「娘,天下英豪何其多,渣爹這顆歪脖子樹配不上你」 小兒子,「渣爹學誰不好,偏偏學陳世美殺妻拋子,史無前例的渣」 腰中別菜刀,心中有菜譜的柳茹月點點頭,「孩兒們說得對! 我們的目標是……」 齊,「休了那個陳世美」
89.7萬字8 16990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612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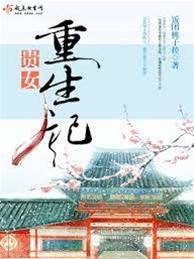
貴女重生記
大晉貴女剛重生就被人嫌棄,丟了親事,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將未婚夫賣了個好價錢!被穿越女害得活不過十八歲?你且看姐佛擋殺佛,鬼擋殺鬼,將這王朝翻個天!小王爺:小娘你適合我,我就喜歡你這種能殺敵,會早死的短命妻!
62.1萬字8 1245 -
連載773 章

洞房夜,給禁欲殘王治好隱疾后塌了床
穿成丑名在外的廢柴庶女,洞房夜差點被殘疾戰王大卸八塊,人人喊打! 蘇染汐冷笑!關門!扒下戰王褲子!一氣呵成! 蘇染汐:王爺,我治好你的不舉之癥,你許我一紙和離書! 世人欺她,親人辱她,朋友叛她,白蓮花害她……那又如何? 在醫她是起死回生的賽華佗,在朝她是舌戰群臣的女諸葛,在商她是八面玲瓏的女首富,在文她是下筆成章的絕代才女…… 她在哪兒,哪兒就是傳奇!名動天下之際,追求者如過江之卿。 戰王黑著臉將她抱回家,跪下求貼貼:“王妃,何時召本王侍寢?” ...
142.7萬字8.18 132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