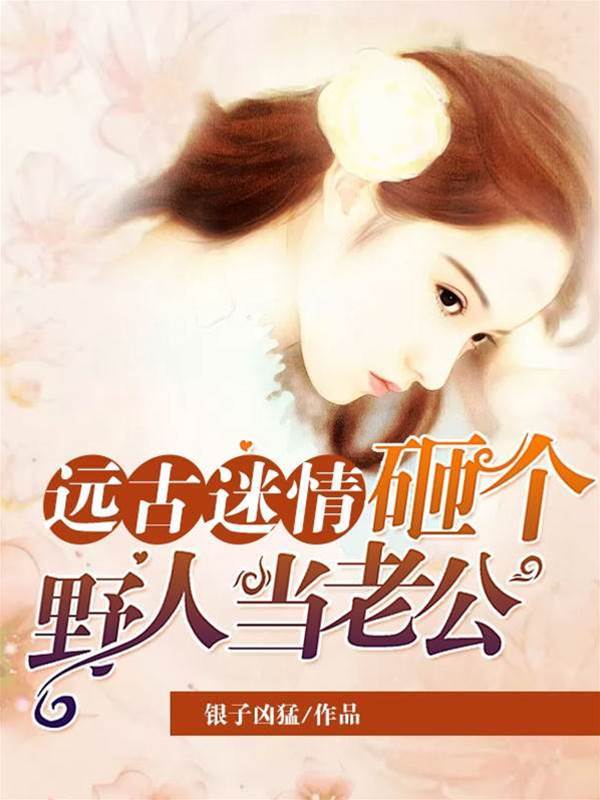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穿書後我成了反派的童養媳》 第一卷:童養媳養成記 第89章:甩鍋
什麼大事還要避開說?
舒雨微又打了個呵欠,心知晏謫江還將當細作看待,便也沒將此事放在心上。
吃吃睡睡兩三日,才重新打起神來,準備去弄清楚自己這些日子以來遇到的謎題。然而當日一下課,便又被晏謫江拉著出了府。
坐在馬車裏,舒雨微一面剝著從府裏帶出來的橘子,一面出聲問著邊的人:「小爺,你不會又要帶我出城吧?」
將剝好的一瓣兒遞到晏謫江面前,但那人卻沒有接過去,反而擺了擺手。只好撇撇,悻悻地拿了回來,又自己一口悶了進去。
「去刑部。」
晏謫江撂下這麼一句話,便閉上眼休息。舒雨微想多問幾個問題都沒有機會,只好從荷包里拉出臨走前塞進去的幾個橘子,默默坐在一旁橘子、吃橘子。
等到了地兒,舒雨微才知道晏謫江是帶來理方徽的事,原來當日回來后,他便讓若歆的小侄子帶著證據去報了,因為涉及地方員,府便將此事上報給了朝堂,只不過隻字未提晏謫江,至於方徽的死,男孩只說是個好心人救了他們兄妹二人,又帶著他們來到京城。
這件事引起不小的轟,皇帝一方面派大理寺調查男孩口中的神人,畢竟無論方徽是否有錯,隨意殺死地方員,都會引起百姓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他又命刑部著力審查方徽一事。
晏謫江扔給舒雨微一頂帷帽,出聲對道:「那孩子知道的事不多,你進去幫他講清楚,九翊會跟著你一同進去,不要暴份。」
舒雨微撇撇,就知道這人帶出來準沒好事。默默接過帷帽戴上,從位子上起,將將掀起車簾來,就聽到後的人忽然出聲:「我囑咐你的話,你都記清楚了?」
Advertisement
舒雨微咧一笑:「承蒙小爺信任,自然是記得清清楚楚啦。」
說完下了馬車,臉頓然一變。冷哼一聲,舒雨微將頭上帷帽紗放了下來,隨同一樣帶著帷帽的九翊,緩步朝前走去。
馬車停在偏僻,跟著九翊穿過好幾個小巷子,才終於來到刑部的大門前。
二人同看守的侍衛解釋了一番來意,待他們通報了掌管邊城刑名案件的員后,緩步了裏面。
男孩兒正跪在地上,訴說著自己與妹妹所到的不公,他特意沒有提及父親,想來應該是晏謫江特意囑咐過。
舒雨微提跪下,先聲說明了來意。
「見過大人。民願為這位小公子作證,當日方徽慘死,民恰好在場,大人若有什麼問題,民自當儘力解答。」
審案的員是個頭大耳、面相不善之人。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舒雨微,清了清嗓子,坐直了子問道:「你是何人?」
「民原是邊城人,因為家中過方徽迫害,所以特地來此,為他作證。」
那員又看了須臾,像是在思索著什麼,許久,才幽幽出聲:「這男孩說,當日是個神男子救了他妹妹,方府也是在那之後傳來了噩耗。本且問你,你可見過那神男子?」
「我當日確實見到一男子。方徽為財殺了我全家,事後又抓了我來想要滅口,好在出現一男子及時救下了我,這位公子口中的神男子,應該也是那人。」
員又問道:「那你可有見到他的模樣?」
舒雨微道:「那人……」
原打算說那人當日是矇著面的,但轉念又想起晏謫江那日從方府出來時,邊城眾多百姓都有圍觀,若說是蒙面,實在太容易被拆穿。
於是道:「那人形修長。我見到他時,他是破窗而,直直擋在我前的。他一劍便殺死了方徽,我當時太過驚恐,所以就昏了過去……我也,沒有看清他的臉。」
Advertisement
案臺後那人不由得皺起眉頭,他手了邊的鬍鬚,思忖須臾,又出聲問道:「那他上,可有什麼與眾不同的配飾?」
舒雨微一滯,佯裝思索,許久才遲疑著出聲:「……他的上似乎別著一支簫,是玉制的,看著極為貴重。」
三皇子常承瀟的上一直帶著一支簫,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恰逢前段時間常承瀟出京辦事,這事兒賴在他頭上自然是最好不過的。
當然,這些事自然是晏謫江告訴的,而這話,便也是晏謫江讓說的。
那人神驟變,詫異地扭過頭看向旁的人,眼神流須臾。他才垂著眼輕咳一聲,又問道:「你所言可當真?」
「民自然是不敢欺瞞大人,所言句句屬實。」
那人瞇了瞇眼,又道:「把你的帽紗掀起來。」
舒雨微沒有依著他的話照做,反而將頭埋得更低,「大人恕罪,民臉上生了膿瘡,實在無見人。」
「本讓你掀起來你就掀起來,哪兒那麼多廢話!」
他說著,便揮手示意側的侍衛過去,舒雨微聞聲抬頭,隔著面紗看去,只見那人離越來越近,心一橫,立刻在袖中索起來。
九翊忽然上前幾步,擋在了的面前,看那架勢像是要手。
雖然們二人都矇著面,便是起手來也不會牽扯到晏謫江,但多一事不如一事,萬一九翊寡不敵眾,那豈不是要出大事。
舒雨微閉著眼嘆息了一聲,將剛剛在袖中索到的噴霧取了出來,又在潛意識裏讓小悠調整了裏面的香型,隨即便不聲地朝自己臉上噴去。
「你想幹什麼?」
那員重重一拍案,指著九翊便道:「你們二人今日若是不以真面示人,我便以妨礙公事的罪名給你們論!」
舒雨微一把抓住九翊的角,帷帽隨著的腦袋左右晃了一下,道:「不要多事,我摘就好。」
說著,乾脆將頭上的帷帽取了下來。
眾人神各異,但大都逃不過一個驚嚇的神,上座那人也是一愣,連忙別過視線,揮手說道:「戴上去戴上去!」
九翊見此景,心中詫異,於是也轉過頭去看。然而一向自詡定力極好的他,此刻也像是到驚嚇般朝後挪了一步。
難怪敢摘掉帷帽,這幅樣子不要說能不能看得出是誰,就連是不是個人只怕都得再三思慮。
舒雨微沖他嘿嘿一笑,嚇得九翊又是一個激靈,連忙轉回頭去。
撇了撇,舒雨微拿起手上的帷帽,不等自己主套在頭上,離最近的一個侍衛便已經忍不住沖了過來,一把將帷帽按在了的頭上。
上座的員這才轉回頭來,扶額緩了好一會兒,才又沖九翊說道:「你也摘下來。」
舒雨微扯了扯九翊的角,想將噴霧遞給他。九翊似是猜到了,連頭也沒回一下,直接對上座那人說道:「我是陪同我家小姐出來的侍衛,當日之事我並不清楚。」
「那也得摘。」
上座那人直勾勾地看著他,神凝重。僵持了片刻,見九翊還是沒有摘下的打算,他於是再度揮手,示意侍衛過去親手摘下。
九翊兩三下便將那人撂倒,一腳還踩在他的上。員臉大變,慌忙從坐上站起,他一拍案臺,大喊道:「什麼笛子,什麼不知道,我看那神人就是你!來人!將他們二人速速拿下!」
九翊反應極快,他一把拽起地上的舒雨微,拉著便往外跑去。兩人好容易才從屋的侍衛手中逃出,院外的一眾侍衛卻頓時他犯了難。
舒雨微幻化出銀針,趁著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九翊上,隨即丟出銀針擊昏幾人,與九翊打起配合。
然而院兒的侍衛實在太多,他們實在難以抵擋,千鈞一髮之際。一群黑人忽然從府外竄,將院侍衛全然圍住,隨即展開攻擊。
面前一團混,舒雨微本想趁機拉著九翊逃走,自己的子忽然一輕,一個矇著臉的黑男子一把將抱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帶著逃出了這裏。
舒雨微隔著帷帽,抬頭看著面前蒙得嚴嚴實實的人,不假思索道:「小爺出門怎麼還多帶一套行頭?」
那人輕笑,「你如何猜出是我?」
「不是猜。我待在小爺邊這麼久,小爺上的氣味我還是悉的。」
晏謫江沒再說話,一直帶著回到馬車裏,才將面罩摘了下來。
他的頭髮雖然糟糟的,但卻是半點也妨礙不到他的值,那張臉是該多妖孽還是多妖孽。甚至這樣披散著頭髮,舒雨微倒覺得別有一番清冷的好看。
然而自己卻還帶著那頂帷帽,晏謫江想手給取下,卻被眼疾手快地給攔了下來,「別摘!……我,我覺得戴著好的,神的……」
晏謫江挑了挑眉,狹長的丹眼裏頭一次出好奇的意味,盯著面前「沒臉」的人看了半晌,他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抬手掀掉了頭上的帷帽。
「啊!!!」
舒雨微連忙捂住臉去,將頭低得死死的,生怕自己的臉出一丁點。
誰看都行,可就是不想讓晏謫江看見,雖然也不知道為什麼,可就是很抵,很抵很抵被晏謫江看到!
晏謫江一把扯下的手,用力將舒雨微拉到自己面前。看著這張慘不忍睹的臉,他並未出屋裏那群人一臉驚悚的樣子,只是疑著聲問:「你的臉怎麼了?」
「嗚嗚嗚。」
舒雨微假哭了幾聲,委委屈屈地把事的原委訴說了一遍。
晏謫江聽后,不嗤笑起來,舒雨微更為惱,立刻轉過頭蹲在角落裏,出聲吐槽道:「早知道九翊非要打這一架,我就……我就不把自己搞得這麼狼狽了!」
原以為晏謫江笑笑也就過去了,誰知他越笑越起勁,笑得整個子都抖了起來。
「啊啊啊!晏謫江!你不要再笑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8 章
歡天喜帝
泱泱亂世下,一場王與王之間的征戰與愛。他是東喜帝,她是西歡王。他叫她妖精,她稱他妖孽。他是她的眼中釘,她是他的肉中刺。他心狠手辣霸氣橫溢,她算無遺策豔光四射。相鬥十年,相見一面,相知一場,相愛一瞬。是他拱手山河博卿歡,還是她棄國舍地討君喜?世間本有情,但求歡來但尋喜。
43.2萬字8 8888 -
完結407 章

重生后成了皇帝的嬌軟白月光
(重生1V1)論如何從身份低微的丫鬟,獨得帝王寵愛,甚至於讓其解散後宮,成為東宮皇后,自此獨佔帝王幾十年,盛寵不衰。於瀾:“給陛下生個孩子就成,若是不行,那就在生一個。”反正她是已經躺贏了,長公主是她生的,太子是她生的,二皇子也是她生的,等以後兒子繼位她就是太后了。至於孩子爹。“對了,孩子爹呢?”慶淵帝:“……”這是才想起他。朕不要面子的嗎? ————於瀾身份低微,從沒有過攀龍附鳳的心,她的想法就是能吃飽穿暖,然後攢夠銀子贖身回家。可,她被人打死了,一屍兩命那種,雖然那個孩子父親是誰她也不知道。好在上天又給了她一次重來的機會。既然身份低微,就只能落得上輩子的下場,那她是否能換個活法。於瀾瞄上了帝都來的那位大人,矜貴俊美,就是冷冰冰的不愛說話。聽說他權利很大,於瀾想著跟了他也算是有了靠山。直到她終於坐在了那位大人腿上,被他圈在懷裡時。看著那跪了一地高呼萬歲的人,眼前一黑暈了。她只是想找個靠山而已,可也沒想著要去靠這天底下最硬的那座山……完結文《權臣大佬和我領了個證》《向隔壁許先生撒個嬌》
59.5萬字8 278267 -
完結1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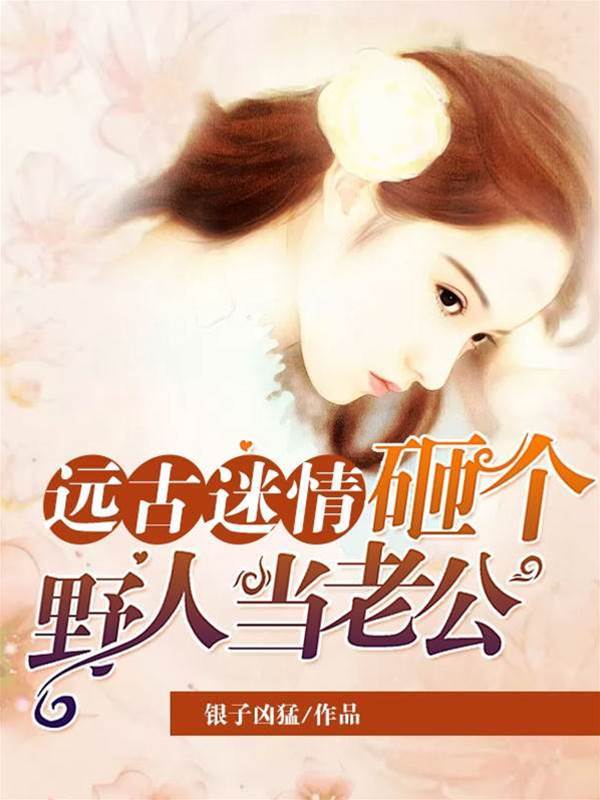
遠古迷情:砸個野人當老公
穿越到原始深林,被野人撿了 野人很好,包吃包喝包住,然而作為代價,她要陪吃陪喝陪睡! 于是見面的第一天,野人就毫不客氣的撕了她的衣服,分開她的雙腿 作為報復,她將野人收集的皮毛割成一塊塊,將他抓來的兔子地鼠放生,生火差點燒了整個山洞 然而野人只是摸摸她的小腦袋,眼神溫柔,似乎在說,寶貝,別鬧了!
41.9萬字8 13085 -
完結889 章
嫁給渣男死對頭
前世,沈鸞那寒門出身的渣男夫君給她喂過兩碗藥,一碗將她送上了權傾天下的當朝大都督秦戈的床,一碗在她有孕時親手灌下,將她送上了西天,一尸兩命。兩眼一睜,她竟回到了待字閨中的十五歲,祖母疼,兄長愛,還有個有錢任性的豪橫繼母拼命往她身上堆銀子。沈鸞表示歲月雖靜好,但前世仇怨她也是不敢忘的!她要折辱過她的那些人,血債血償!
167.1萬字8.18 78103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5 91345 -
連載573 章
侯府雙嫁
葉家心狠,為了朝政權謀,將家中兩位庶女,嫁與衰敗侯府劣跡斑斑的兩個兒子。葉秋漓與妹妹同日嫁入侯府。沉穩溫柔的她,被許給狠戾陰鷙高冷漠然的庶長子;嫵媚冷艷的妹妹,被許給體弱多病心思詭譎的嫡次子;肅昌侯府深宅大院,盤根錯節,利益糾葛,人心叵測,好在妹妹與她同心同德,比誰都明白身為庶女的不易,她們連枝同氣,花開并蒂,在舉步維艱勾心斗角的侯府,殺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最后,連帶著不待見她們二人的夫君,目光也變得黏膩炙熱。陸清旭“漓兒,今夜,我們努努力,再要個囡囡吧。”陸清衍“寒霜,晚上稍稍輕些,你夫君我總歸是羸弱之身。”
100萬字8 3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