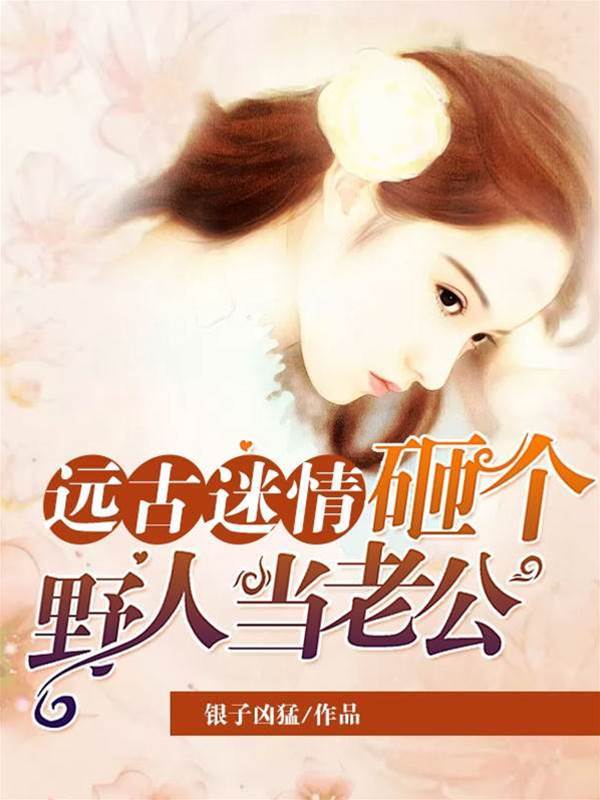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重生后成了太子朱砂痣》 第59章 續夢前世
孫霞薇額角一個窟窿,本就昏昏沉沉,此時突然被揪住頭發,頭皮扯得生疼,一陣暈眩。
孫常戎跪著地上哆哆嗦嗦,聽不來頭頂皇上的恩典,心尖打抖,余瞥見孫霞薇半響無靜。
孫常戎氣得肺都要炸了,都是這賤蹄子搞事,他垂著頭,抬手朝孫霞薇腰間狠狠擰了了一下,低著聲音齜牙咧:“快向皇上和太子請罪。”
孫霞薇猝不及防,腰間如同刀絞的疼痛,登時驚呼出聲。
孫常戎嚇得一個哆嗦,余看到了皇上面如沉水,神冷峻,他為這麼多年,最是會察言觀,登時嚇得掐死孫霞薇的心都有了。
他抬手一個掌扇得孫霞薇趔趄趴在地上,劈頭蓋臉罵到:“你什麼,圣上面前豈容你無禮!”
說罷,孫常戎又跪在地上低垂著腦袋,哐哐磕了幾個響頭,恭恭敬敬請罪:
“臣一時鬼迷心竅,妄想一步登天,污蔑太子,罪該萬死。臣平日忙于公務,對宅疏于管教,污了圣聽,請陛下恕罪。”
他這話是不管孫霞薇死活了,卻把自己摘了一干二凈。
孫霞薇捂著臉,額角帶,殷紅的跡覆蓋著一個深的口子,右側雪白的面頰上有一道曲曲折折的痕,左側面頰卻紅腫不堪,深深淺淺覆蓋著三層深重的掌印,鮮紅糙的五指在面上如綻開了一朵重瓣的小花。
眉目如畫,此時細白的臉蛋卻不堪目,雙目無神,怔怔看向孫常戎。
知道自己的父親不疼,平日里對苛責,今日也不過想博個好的前程,想回到前些日子父親拉著的手笑著喚“”的日子。
孫霞薇眨了眨眼睛,兀得角勾出一抹大大的弧度,低低輕笑一聲。
Advertisement
聲音從嚨深溢出,低低得如同魔怔,竟一時有些嚇人。
孫常戎心驚膽戰覷著圣,孫霞薇此時不在他跟前跪著,他想教育孫霞薇,可金鑾殿上又不敢太過放肆,只能以目為刀,狠狠瞪著孫霞薇。
孫霞薇老老實實跪好,孫常戎心里慢慢長舒一口氣,以頭搶地,正要再次求恩突然聽到旁的孫霞薇開口。
“皇上,臣孫霞薇舉報父親,前禮部侍郎,現禮部郎中,中飽私囊,貪污賄,請皇上徹查。”
話音一落,一時寂靜無聲。
孫常戎怔楞一瞬,臉陡然大變,面無,他立即爬起去打孫霞薇,眼睛瞪得赤紅,狠聲道:“你這個賤蹄子在胡說什麼。”
孫霞薇被他揪住頭發,臉上唰得又重重挨了一個掌,角都是鮮,臉偏向一側。
孫常戎著氣,目兇:“讓你胡說八道。”
“夠了!”
突然凜冽一聲。
孫常戎一個打,當即送了孫霞薇,伏爬在地上戰戰兢兢,哭訴:“皇上,臣為公兢兢業業,恪盡職守……”
孫常戎想說,余中卻瞥到皇上,一時嚇破了膽,嗓子張開,卻發不出聲音。
皇上如蕭鈞煜絕似的端眼幽深如潭,閃著凌冰,角一直掛著淺淺的弧度,悠悠道:
“孫大人真是讓朕和文武百看了一場好戲。”
孫常戎兩,咽了咽結,瓣哆哆嗦嗦,面如土:“皇,皇上……”
“拖下去。”皇上按了按額角,懶得聽他再辯解。
四個錦帶刀侍衛上殿,步履整齊劃一,面無表,周帶著凜凜殺氣,作迅速將孫霞薇和孫常戎拉了下去。
孫霞薇盯著蕭蘇軒舉的太子殿下,目懇求。
Advertisement
蕭鈞煜目云淡風輕,自始至終沒有對孫霞薇出一一毫的憐惜或者憐憫之。
杏黃的影越來越遠,蕭鈞煜如玉的側冷若冰霜,孫霞薇角的弧度大大,低低慘笑一聲,淚珠簌簌而落:
是鬼迷心竅,貪太子殿下的權勢,嫉妒當朝首富沈家嫡,可何嘗不是想過得好一點?
錦衛拖著孫霞薇越過高高的門檻,孫霞薇一個哆嗦,驟然驚醒,扯著嗓子大喊:“太子殿下,臣好歹救過你的命,為您理過傷口,不合眼守了您一夜,求嗚嗚唔。”
錦衛毫不憐惜捂著的。
金鑾殿上文武百低垂著腦袋,脊背直,不敢直視圣,半響聽到上座甩袖起的聲音,倏爾,大太監扯著嗓子喊:
“下朝。”
蕭鈞煜看著空空的龍椅,角抿直,黑漆漆的眸深邃。
他立在原地良久,方才抬步大步流星出了金鑾殿,突然,他腳步一頓,有人低低私語:
“你說這孫姑娘不是太子殿下的救命恩人,誰是太子殿下的救命恩人?”
“先不說這個,聽這意思,這救命的過程……嘖嘖,估計不是什麼端莊賢淑的大家閨秀。”有人挑了挑眉梢,低低笑了一聲,嗓音里帶著難以明喻又直白的某種意思。
他正要向對面的同僚再要細說,卻突然只覺周一冷,脊背生寒,他僵緩慢轉頭,看著太子殿下不怒而威的目,撲騰跪在地上,結結道:
“臣,臣……”
“管好你的。”蕭鈞煜淡淡道。
太子殿下的目如一把利刃,如帶著千萬鈞的力道,那大臣撐著一口氣勉強脊背直,垂著頭連勝應道:“是,是,臣知錯。”
等蕭鈞煜的腳步聲沒了,那大臣在同僚的扶拉下起,有些麻,一袍都浸了冷汗。
他了額角的汗,著太子殿下拔如松的背影,心有余悸低聲音道:
“剛金鑾殿上孫家污蔑太子殿下,我見太子殿下始終神淡淡,怎麼我剛說一句,就覺太子殿下恨不得將我砍了。”
太子殿下寵辱不驚,方才金鑾殿上一直神自若,流言蜚語對他應是無半點影響,這才是他們群臣口稱贊的當朝太子,未來的儲君。
他對面是一個老臣,五十多歲,滿面滄桑,此時轉了轉眸子,瞳孔驟然一,喟然嘆道:
“沒準,大盛朝當真要迎來太子妃了。”
……
蕭鈞煜出了金鑾殿,他沒有回東宮,乘了一輛低調的馬車去了東四大街。
蕭鈞煜執著椒圖敲了幾下門。
沈府漆黑的大門緩緩開了一道小小的口子,一個年長的老伯從里探出一個腦袋,看到蕭鈞煜,眸一閃忙躬道:“太子殿下。”
“孤想拜見沈姑娘,還老伯幫忙通稟。”
石伯子立得更正,頭垂得更深,語氣恭敬道:“太抱歉了,太子殿下,我家姑娘子不適,特意囑托了不見客。”
蕭鈞煜眉頭微蹙。
“煩勞老伯幫忙再通稟一聲。”
福明從側邊塞過來一個沉甸甸的荷包,石伯嚇得連連退后,惶恐道:“太子殿下折煞奴才,不是奴才不通稟,是姑娘當真子不適,特意代了誰也不見。”
蕭鈞煜垂了垂眼簾,從袖中拿出一封信:“勞煩老伯將此信箋給沈姑娘。”
石伯跪在了地上,連連磕頭:“求太子殿下不要為難奴才。”
蕭鈞煜薄繃直,垂著眼簾比今日殿上孫常戎還誠惶誠恐的石伯,握了握拳頭。
沈筠曦是當真不愿見他,也不愿收他的東西,門房見了他才會如此害怕。
蕭鈞煜無意為難一個無辜的下人,他轉。
“太子殿下,您的份,您何必對一個下人如此客氣。”福明跟在蕭鈞煜后,回頭看了一眼沈府閉的大門,有些不忿。
蕭鈞煜貴為當朝太子,一國儲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若當真想進門,那沈府的奴才哪里敢阻攔。
“不喜。”蕭鈞煜抬眸看了眼沈府西側的位置,淡聲道。
沈筠曦居住的玉蘭苑坐落在沈府的西側,此時四月天,玉蘭開得正盛,蕭鈞煜立在此,似乎嗅到了所有似無的玉蘭清香。
正此時,沈府的大門慢慢打開,從里面出來了一位著一件深王絨線三藍百花紋樣襦,外搭芥末黃鋪地錦外衫,子裊裊,一抬眸看著不遠的蕭鈞煜,忙垂下頭,耳尖發紅,半響,小碎步靦腆福禮:“太子殿下。”
“武姑娘。”蕭鈞煜輕輕頷首,抬眸又看了眼玉蘭苑的方向。
“武姑娘可是從玉蘭苑出來?”
“是。”武琇瑩小聲回稟,雙手擰在一起,不敢看蕭鈞煜。
蕭鈞煜從袖中拿出剛才的信箋:“勞武姑娘幫孤送封信。”
“臣領命。”武琇瑩立直子,登時爽聲應道,面鄭重,一時沒了平日的靦腆,反而帶了些將門之的爽朗。
武琇瑩看著手中雅致的信箋,筆鋒遒勁,嚴謹工整:“沈筠曦親啟”,瞄一眼蕭鈞煜,只見蕭鈞煜已經上了馬車。
“太子殿下,您不去看看沈姑娘嗎?沈姑娘今日似是子不適。”武琇瑩托口而出。
蕭鈞煜眸一暗,回眸看了眼沈府,他手拳拳握握,眸深邃而晦。
半響,他慢慢撂下車幔。
“不愿見孤。”
蕭鈞煜聲音有些低啞,聽得武琇瑩莫名惆悵,心揪在一起。
武琇瑩目送蕭鈞煜的馬車離去,看著手里的信箋,擰眉,咬了咬,小聲嘀咕:“兄長說想要追求到心之人就要厚臉皮,不能總是端著,太子殿下您這般子,沈姑娘不會喜歡的。”
武琇瑩與沈筠曦相不常,卻萬分喜歡沈筠曦的子:明而真摯,爽朗不拘小節,帶人赤誠而熱烈。
零星的話語傳馬車,車中端坐的蕭鈞煜登時渾一僵。
他眨眼,卻突然眼前閃過夢里的畫面,反反復復,幾個畫面錯。
沈筠曦纖纖素手在他結輕,倏爾,俯,櫻輕輕啄他的結,被他用手抓住,兀得低低輕笑一聲:
“太子殿下這般子,多虧是我心悅于您,否則您這般清冷矜貴,我才懶得搭理你。”
眼前一晃,又閃過沈筠曦轉嗔他一眼,輕哼一聲,飽滿的櫻微微嘟起曼聲道:“太子殿下這般清冷無趣,等我以后不喜歡你,你別想追求到我。”
眼前再一晃,沈筠曦淚眼婆娑,扭不愿看他,聲音嘶啞而悲傷:“太子殿下這般子,我真不該喜歡。”
蕭鈞煜面上安然自若,指尖卻了,他結緩而慢滾一下,復而,又滾一下。
鋪天蓋地的惶恐襲來,蕭鈞煜拳手低聲:“孤改。”
眸中明明滅滅,蕭鈞煜合上眼簾靠在車廂上。
車轆轆,蕭鈞煜靠在車廂壁,眼皮越來越沉,竟不知不覺陷沉睡,黑暗沉下,暖紅的夕在天邊灑滿余暉,瑰麗的晚霞得驚心魄。
蕭鈞煜環視一周,終于,他看到了自己心念念的夢中上巳節后第六十八日,沈筠曦被曝未婚先育后,約他相見。
……
玉蘭苑中,沈筠曦看著蕭鈞煜蕭蘇清舉、無于衷的樣子,忍了忍,依舊沒有忍住,紅著眼睛道:
“殿下,我一直在等你。”
這一句,藏在心口多個日夜,在齒流連無數次,一開口,心中積了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貪嗔癡怨便如水涌上。
沈筠曦委屈不能自已,圓潤如黃豆大小的淚珠,簌簌而落。
蕭鈞煜放在桌案上的手有一瞬的輕,卻垂了垂濃的眼簾,緘默不言。
他上巳節時心意已決,不想耽誤沈筠曦。
“昨日太子殿下來沈府,是想同我說什麼?”
蕭鈞煜抬眸,幽深如潭的眸目不轉睛凝視沈筠曦。
“怎麼懷孕了?”蕭鈞煜頭如卡著一魚骨,聲音有些喑啞。
沈筠曦纖細白如青蔥的指尖陡然抓住了膝頭的裳,靨飄起一層緋暈,垂首不敢直視蕭鈞煜,纖長卷翹濃如蝶翼的眉睫撲撲,聲音幾不可聞。
“就是那次意外。”
有些話,于開口。
蕭鈞煜看著沈筠曦撲閃的翹睫和傾城的側,手指握拳,心臟驟疼。
蕭鈞煜垂下眼簾。
長睫遮住了眼瞼,漆黑的眸暈著難以明喻的憾和哀傷。
是他說了,他與沈筠曦無緣,沈筠曦應另擇佳婿,六十多個日夜,他不愿見,自是可以尋個郎君,自是可以與他們親近。
蕭鈞煜知道,心臟卻莫名如被鈍刀子磨,一下,一下,細細的痛卷上心頭。
花廳一時落針可聞,只有氤氳的茶香裊裊騰空。
沈筠曦等了許久,久到面頰升起一陣紅熱,面紅耳赤,又熱氣一點一點消退,膝上的擺被手心攥得鄒鄒。
沈筠曦沉不住氣,側眸睇了一眼蕭鈞煜。
蕭鈞煜側清冷,眉頭鎖,角抿,一言不發。
沈筠曦騰得一下心頭火氣,整個人如炮竹樣被點燃,唰一下子站起來,杏瞳霧煞煞怒瞪蕭鈞煜,揚聲質問:
“蕭鈞煜,我都懷孕了!都未婚先育了,你還不娶我,你讓我以后怎麼嫁人!”
此時是一點禮儀尊卑都不講了,大聲喚著蕭鈞煜的名諱,心口劇烈起伏,貝齒咬著瓣。
蕭鈞煜應聲抬頭,眼睛有一瞬不可置信。
他自下而上凝視沈筠曦梨花帶雨的小臉,結不由得慢慢滾,菱微開,聲音有些艱喑啞:
“可,我不能給你……太子妃之位。”
他于隆福寺傷,被禮部侍郎之孫霞薇舍清白相救,孫霞薇因此懷孕,于于理,他當娶了孫霞薇。
蕭鈞煜沒有問沈筠曦孩子是誰的,為什麼不嫁與那人,因為若是兩廂愿締約,今早或是昨日便有人來沈府提親。
昨天,他聽到蕭和澤愿以二皇子正妃之位迎娶沈筠曦。
“不給就不給,我又不是看中了你的太子妃之位!”
這話把沈筠曦給氣著了!
慕蕭鈞煜,想嫁給蕭鈞煜,難道是貪圖蕭鈞煜的太子妃之位!
沈家盛朝首富,富敵數十個國庫,沈筠曦自錦玉食,千百寵,日子哪點也不比王公貴族差,還犯不著為了一個太子妃之位斷送了自己的婚姻。
沈筠曦氣得雙腮鼓起,圓潤的淚珠掛在潤潤的眉睫,如同一只炸的小貓,纖纖玉手氣得去蕭鈞煜心口,目水流盼,高聲質問:
“我不過一腔癡你,你不娶我,你讓我未婚先育,嫁給誰!”
盛朝民風開明,子二婚再婚皆有,婚姻相對自由,尤其沈筠曦仙姿佚貌,沈家又是當朝首富,就是沈筠曦不想嫁人,招婿也自有千上百芝蘭玉樹的好兒郎上門自薦。
不是嫁不出去,只是,嫁的那些人,終究不是你。
淚珠如同斷了線的珍珠,一顆接著一顆,順著沈筠曦凝脂雪腮滾落,匯聚在下尖,嗒滴落。
低低的啜泣聲,如千萬只螞蟻啃噬著蕭鈞煜的臟,他指尖反復捻,角抿一抹直線,盯著沈筠曦面頰的淚珠,向來端方自持清冷,今日卻有沖為沈筠曦去淚珠。
一個淚珠砸到蕭鈞煜手背時,蕭鈞煜不再克制,指腹輕輕上沈筠曦的眼尾。
馬車中,蕭鈞煜猝然睜開眼睛,他心口劇烈起伏,他長睫緩而慢閃了一下,雙目暈著深沉濃郁化不開的痛楚。
“沈筠曦,孤對不起你。”蕭鈞煜聲音又低又啞,讓人猝然落淚。
凄肝脾的痛,讓蕭鈞煜捂著左心臟自般按在傷口。
傷口再次裂開,創巨痛深,蕭鈞煜眨了眨眉睫,驀然震聲。
“福明,去沈府!”
已過宮門,福明才將對侍衛出示太子信手到腰間,剛見蕭鈞煜沉睡,思忖蕭鈞煜近日太累沒有休息好,福明沒喚醒蕭鈞煜,擅作主張駕車進了皇城。
福明聞聲勒住駿馬,猛得調頭。
“孤當真愚昧。”腔微震,蕭鈞煜似哭似笑道。
沈筠曦如此顯而易見的話,他前世竟然沒有察覺不對,蕭鈞煜已然確認那是前世。
前世,他雖多次遲疑孫霞薇子不像他的救命恩人,反而沈筠曦神態舉止在他瞇著眼朦朦朧朧端看時,像極了他的救命恩人,可囿于種種證據,或是他心底也不敢相信沈筠曦是的救命恩人,他還是將孫霞薇認作了救命恩人。
簡直愚笨至極。
他真正的救命恩人沈筠曦救了他的命,為他失了清白之,為他未婚先育,遭流言蜚語,他卻將無名無分安置在東宮,許諾娶了孫霞薇,他真混蛋!
蕭鈞煜心臟如被一張大手攥住,狠狠著他的心臟,要將他心臟破,痛得不過氣,痛得無法呼吸。
聽見侍衛行禮的聲音,蕭鈞煜陡然開車幔,翻躍上宮門停候的一匹烈馬。
他迫不及待想見到沈筠曦。
作者有話要說:明日要早起上班,這兩個月去醫院醫生都再三叮囑不能熬夜,可想今晚把這個節點寫到,碼完一看時間一點了,哎。
寶們,你們想看的翠兒會寫到,但允許翠兒按照自己心中的綱和鋪墊寫這個故事,我在努力加快進度。晚安!
猜你喜歡
-
完結158 章
歡天喜帝
泱泱亂世下,一場王與王之間的征戰與愛。他是東喜帝,她是西歡王。他叫她妖精,她稱他妖孽。他是她的眼中釘,她是他的肉中刺。他心狠手辣霸氣橫溢,她算無遺策豔光四射。相鬥十年,相見一面,相知一場,相愛一瞬。是他拱手山河博卿歡,還是她棄國舍地討君喜?世間本有情,但求歡來但尋喜。
43.2萬字8 8887 -
完結407 章

重生后成了皇帝的嬌軟白月光
(重生1V1)論如何從身份低微的丫鬟,獨得帝王寵愛,甚至於讓其解散後宮,成為東宮皇后,自此獨佔帝王幾十年,盛寵不衰。於瀾:“給陛下生個孩子就成,若是不行,那就在生一個。”反正她是已經躺贏了,長公主是她生的,太子是她生的,二皇子也是她生的,等以後兒子繼位她就是太后了。至於孩子爹。“對了,孩子爹呢?”慶淵帝:“……”這是才想起他。朕不要面子的嗎? ————於瀾身份低微,從沒有過攀龍附鳳的心,她的想法就是能吃飽穿暖,然後攢夠銀子贖身回家。可,她被人打死了,一屍兩命那種,雖然那個孩子父親是誰她也不知道。好在上天又給了她一次重來的機會。既然身份低微,就只能落得上輩子的下場,那她是否能換個活法。於瀾瞄上了帝都來的那位大人,矜貴俊美,就是冷冰冰的不愛說話。聽說他權利很大,於瀾想著跟了他也算是有了靠山。直到她終於坐在了那位大人腿上,被他圈在懷裡時。看著那跪了一地高呼萬歲的人,眼前一黑暈了。她只是想找個靠山而已,可也沒想著要去靠這天底下最硬的那座山……完結文《權臣大佬和我領了個證》《向隔壁許先生撒個嬌》
59.5萬字8 278249 -
完結1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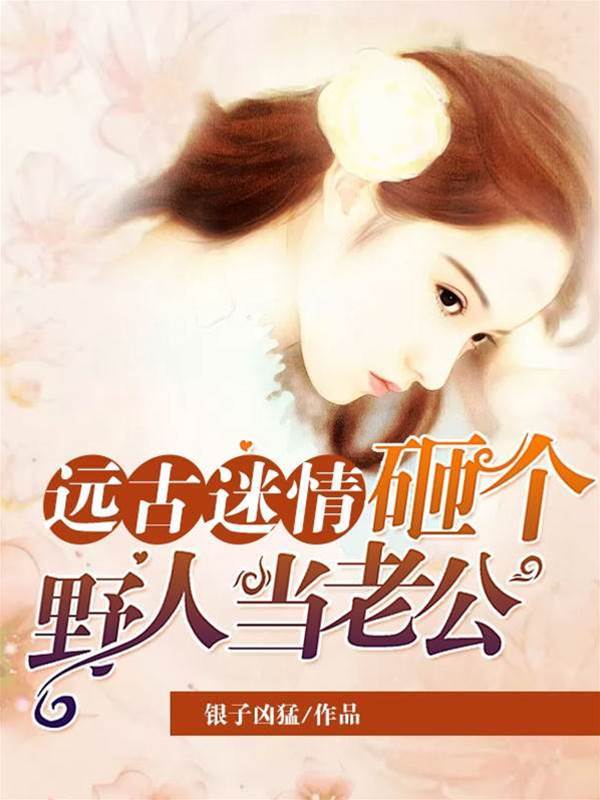
遠古迷情:砸個野人當老公
穿越到原始深林,被野人撿了 野人很好,包吃包喝包住,然而作為代價,她要陪吃陪喝陪睡! 于是見面的第一天,野人就毫不客氣的撕了她的衣服,分開她的雙腿 作為報復,她將野人收集的皮毛割成一塊塊,將他抓來的兔子地鼠放生,生火差點燒了整個山洞 然而野人只是摸摸她的小腦袋,眼神溫柔,似乎在說,寶貝,別鬧了!
41.9萬字8 13084 -
完結889 章
嫁給渣男死對頭
前世,沈鸞那寒門出身的渣男夫君給她喂過兩碗藥,一碗將她送上了權傾天下的當朝大都督秦戈的床,一碗在她有孕時親手灌下,將她送上了西天,一尸兩命。兩眼一睜,她竟回到了待字閨中的十五歲,祖母疼,兄長愛,還有個有錢任性的豪橫繼母拼命往她身上堆銀子。沈鸞表示歲月雖靜好,但前世仇怨她也是不敢忘的!她要折辱過她的那些人,血債血償!
167.1萬字8.18 78020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495 -
連載573 章
侯府雙嫁
葉家心狠,為了朝政權謀,將家中兩位庶女,嫁與衰敗侯府劣跡斑斑的兩個兒子。葉秋漓與妹妹同日嫁入侯府。沉穩溫柔的她,被許給狠戾陰鷙高冷漠然的庶長子;嫵媚冷艷的妹妹,被許給體弱多病心思詭譎的嫡次子;肅昌侯府深宅大院,盤根錯節,利益糾葛,人心叵測,好在妹妹與她同心同德,比誰都明白身為庶女的不易,她們連枝同氣,花開并蒂,在舉步維艱勾心斗角的侯府,殺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最后,連帶著不待見她們二人的夫君,目光也變得黏膩炙熱。陸清旭“漓兒,今夜,我們努努力,再要個囡囡吧。”陸清衍“寒霜,晚上稍稍輕些,你夫君我總歸是羸弱之身。”
100萬字8 31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