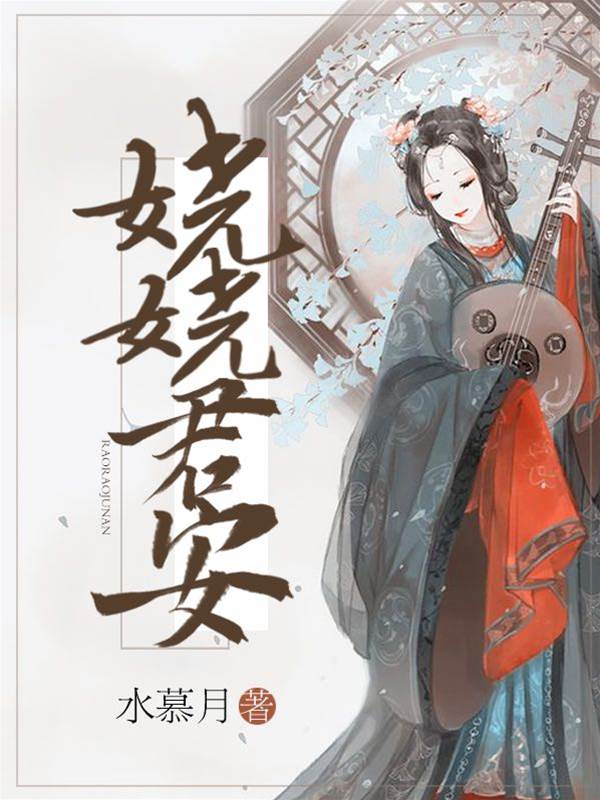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病嬌太子的外室美人》 第55章 解(三合一) “你自己來看,我心里究……
江音晚卻未醒,而是恍惚又置另一境,香燭氣味更濃,木魚聲聲,清脆不紊,梵音深滿空明。
聽到略有幾分悉的嗓音,細思片刻,似是無塵,印象里閑逸的高僧,此刻端肅沉穆。
與他談的是一把極黯啞的男聲,仿佛開口說話便異常艱難,染滿了死寂,幾乎不似生人,竟是裴策的聲音。
江音晚聽清他們說了什麼,一切人聲此時卻都隔了一層堅質隔般,朦朧不明。直到最后,四合極靜,木魚停歇,梵音遠去,終于聽清裴策話語,吐字平澹,如敘尋常。
只一個字:“可。”
心下迷惘焦切,一時急,竟從夢中掙出。額角已布滿冷汗,呼吸虛促,有幾息的恍惚,漸漸看清了自己躺著的梨木月門架子床。
意識回籠的一霎,江音晚心口,呢喃了一句“裴策”,倏然翻坐起,掀開被衾就要下床。
起的作急切,面一白,眼前驟然晃過一陣黑。手了額,撐著床柱勉強站起,未等眼前暗影散去,又要邁步往外走。
裴策恰好進來,見狀疾走幾步到床畔,見臉慘白若紙,扶住道:“晚晚慢些。是不是頭暈?還有哪里不舒服?”
氣不足,晨起若是太急,總會有頭暈的癥狀。
江音晚攥住了他的袖擺,穿過眼前虛晃的黑,那樣用力地凝睇他的面容。一分一分,越過茫茫生死,白骨黃泉,鐫到的心頭。
裴策凝眉,又喚了一聲:“晚晚,你怎麼樣?”
江音晚綿弱無力地說了句“我沒事”,卻仍怔怔著他。稍緩過這一陣后,眼前晃繚的暗散去,視線卻更模糊,淚霧溢滿,滾落。
裴策握著的肩,扶到床畔坐下,為拭去淚痕。他只當江音晚是為江寄舟擔憂,盈滿心疼的眼不著痕跡過一寂寥波瀾,如投石潭,水花微濺后,石子一路沒無蹤。
Advertisement
他低緩道:“江寄舟昨夜退了燒,太醫說他已命無虞。只是毒雖已解,上傷勢過重,還需一段時日才能醒來。”
江音晚依然是恍惚模樣,回了兩分神,問:“當真麼?”
裴策輕輕笑了笑,沒太多緒:“自然是真的。”
他想再勸兩句,讓無需為江寄舟傷懷,卻有一只荑,輕輕上他的面龐。
裴策一夜未眠,玉容神俊依舊,下頜卻有青的胡茬,著清倦。江音晚的指腹順著他下頜廓,遍遍挲輕。
裴策微微蹙眉,結滾了一下,攏住了的荑,嗓音低低沉沉:“做什麼?”
江音晚凝睇著他深濃的眸,輕聲喚:“殿下。”
裴策“嗯”了一聲,等著的下文,卻只是這樣喚了一聲,便不再說話。
裴策著的蔥指,慢慢挪到眼前,將纖手翻過來,漫然看了一眼,確認指腹有沒有胡茬被磨出紅痕。
江音晚面漸漸緩和過來,眸中淚霧盈滿,似滿天星漢爍,櫻翕合幾次,最終只是道:“殿下,多謝你。”
指兄長之事。
未說出口的一句,是前世已不可追,幸而我們還有今生。
仍有一點沉重,在腔。覺得夢中未聽清的、裴策同無塵高僧的談話極為關鍵,有心尋找合適時機問一問裴策,抑或去拜會無塵方丈一面。
然而只一瞬功夫,腦海中他二人的依稀談竟已淡去,心頭迷惘,卻只是茫然,無從問起。仿因天機不可窺探。
裴策深深看一眼,再確認一遍的面,才取過掛在架子上的。是昨夜派人臨時去苑坊取來,玉白上襖,配一襲茜云錦百迭,幫換上,又為穿好鞋,扶去看江寄舟。
Advertisement
江寄舟果然已好轉了許多。面雖蒼白虛弱,卻不似昨日那般泛著將死之人般的青黃。
江音晚總算安心,懇切謝過各位太醫和大夫。眾人忙稱“不敢”,躬拱手道:“請姑娘放心,這位公子已離了險境,過段時日便能醒來。”
裴策帶啟程回到苑坊的私宅。
江音晚本就風寒未愈,這一番勞頓后,午間便又發起了熱。此后斷斷續續地病了好幾日。
床柱上那條金鏈已不見,不過裴策吩咐了秋嬤嬤,盯著臥床靜養。他雖忙碌,每日都會過來,喂用膳、喝藥。
直到將近正月底,江音晚才算徹底痊愈。這日午后,倚在梨木嵌螺鈿花鳥紋人榻上,正懶懶翻著一本游記,忽然聽到庭院中的傳來靜。
憑窗過去,看到李穆正指揮著幾名小廝,將幾個箱子搬到西側廂房。
李穆亦遙遙見了江音晚,趕忙近前,隔窗向躬一禮道:“奴才等驚擾了姑娘,還姑娘恕罪。”
江音晚聲道:“無妨,不知公公搬來了什麼?”
李穆恭敬答:“是姑娘從前在定北侯府的舊。”
江音晚一怔。又聽李穆接著道:“定北侯府所有資產被罰沒,近日一應件清點國庫,殿下亦不能做得太惹眼,只能暗中扣下了姑娘閨閣中的舊,命奴才送來。”
李穆心里明白,江公子雖已險,卻至今未能醒來,殿下知道江姑娘記掛江公子,只能用旁的法子來緩解眷家人之。
“殿下的意思是,若姑娘想家了,隨時可以翻出來看看,若是怕景傷,便妥善封存在廂房。”
江音晚眸底漣漪淺淺,怔然許久,才笑了一笑:“公公代我謝過殿下。”
李穆躬應喏,心里想的卻是,殿下可不愿意聽江姑娘的“謝”字。
江音晚起走到廂房,命人打開了箱子,大略掃了一眼,并未仔細清點,只先找出了母親留下的幾樣。
母親留給的東西并不多,有一塊純白無瑕的羊脂玉,一串小葉紫檀的佛珠,并一些釵環首飾,而最意義可貴的,是母親早年同父親往來的書信。
江音晚一一妥帖收匣子,讓丹若收于寢屋床頭的金楠木柜中。
又將一些過于久遠的件,譬如兒時的布偶之類所在的箱子鎖起。
看著剩下的箱子,有書本紙硯,有釵環,亦有一些畫卷。稍稍出了會兒神,待李穆小心問“姑娘,是否有何不妥?”才恍然回神,淺笑道:“無事。”
命黛縈將尚可用的脂首飾和收拾出來,便回了寢屋。
裴策為探查定北侯府冤案,以及柳昭容柳簪月前世所為,這段時日愈發忙碌。然而矯詔和王益珉之事一時未能理出頭緒,只能先順著柳昭容的線查下去。
柳簪月宮以來,同江淑妃關系淡淡,并無過節,甚至曾在江淑妃積郁疾時說過一番助想開的話。而同江音晚、同裴策都無甚集。
且膝下無子,算來與裴策沒有利益沖突,實在難以堪破其機。
裴策一路查到柳簪月宮之前,派人去了的故里,江南東道吳郡。終于找到了一點可循之跡。
三年前,皇帝遣花鳥使,采擇天下姝好,之后宮(2)。柳簪月正當適齡,又素有名,被花鳥使一眼選中。
閨中的兩名婢已隨宮。往日照料頗多的一名仆婦在宮后不久,便被打發到了莊子里。
探知柳簪月的過往,自是要尋這名仆婦,然而此人卻似人間蒸發了一般,杳無蹤跡。
裴策派去的人覺出了可疑,在柳家其他仆人口中旁敲側擊,又在附近一帶打聽。三年前的事,并不久遠,即使非柳簪月邊之人,不知詳,也難以抹去所有痕跡。
果然查到一點信息。柳簪月在宮前不久,曾同一名長安來的貴人有過往來。甚至據柳家一名下人說,“甚是親”。
這其中不知是否有添油加醋的分。而問及這名貴人份,眾人并不詳知,只記得其人相貌俊雅風流,依稀聽邊的人喚過他一聲“殿下”。
能稱殿下者,滿朝不過寥寥,并不難查。消息飛鴿傳回長安,裴策核查三年前曾至江南東道的皇子、諸王,唯有一人相符。
淮平王裴昶。
此時已是二月初,白玉直頸瓶里著最后的紅梅,一枝品種喚“骨紅照水”,又一枝喚“千臺朱砂”,開得濃紅醉,灼艷不妖。
裴策坐在人榻畔,將探知的消息一一告知江音晚。
“殿下的意思是,柳昭容是淮平王安宮的人?”江音晚斜憑人榻上,面向裴策安安靜靜聽完,輕聲問。
“僅是推測,尚無證據,還需找到那名失蹤的仆婦才能有定論。”不過裴策心中已有七八的把握。
且唯有如此,方能解釋得通。前世,淮平王趁皇帝病重,發起宮變,被裴策斬于劍下。若柳昭容是淮平王的人,便有了挑撥裴策與江音晚關系的機。
然而這一脈雖能捋清,線索到此便斷了,王益珉之事和那封矯詔仍然無從解釋。
淮平王同安西節度使合謀起兵,王益珉獻策,尚有可能是淮平王看到局勢不利,背棄盟友、斷尾求生之舉。
然而那封矯詔,斷不可能是淮平王偽造。他有何理由在盟友出頹勢之前,便江景元出兵剿滅,且使自己與之勾結的證落于江家父子手中?
裴策慢慢手,到江音晚擱在圓枕邊的手,仔細確認一眼,并無抵之意,才將那只荑慢慢收攏在掌中,一字一字沉緩道:“晚晚信孤,孤定會一一查明。”
江音晚淺淺點一點頭,因側躺著,鬢邊點翠穿珠流蘇垂下來,輕晃著過青。
又聽裴策接著說下去,他濃睫垂下,遮住眸底深涌似海的緒,嗓音低沉至暗啞:
“這一世,我們好好重新開始。不論你心里有沒有孤,心里那人是誰,孤都可以不計較,只希你放下前世的錯恨,給孤一個機會。”
江音晚杏眸頓然睜圓了。翻坐起來,深吸了一口氣,連名帶姓喚了一聲:“裴策。”
這一世還從未這樣喚過他。裴策微愕抬睫,注視著,對這個稱呼沒有不高興,反而有等待宣判般的張。
下一瞬,裴策掌心一空。
因他不曾用力,江音晚微掙一下,便出了手。他的腔也似被空了一塊,二月料峭的風灌進去。他未敢再手去握住。
他眸底翻涌著千仞墨浪,表面卻是澹澹寂寒的靜潭,安安靜靜等著江音晚的決。
江音晚抿了抿,忽而起下榻,往屋外走。
裴策默默跟著,看走進了右側的廂房,在幾個未鎖的箱子里翻找。
“晚晚在找什麼?”他聲音很輕,似這時節江上最后的浮冰。
江音晚沒有理他,兀自翻找著。他便不再問,只靜靜站在一邊,玉容寥落寂和,向江音晚的眸底卻抑著瀕臨崩潰的瘋狂。
靜潭慢慢顯出幽險莫測,若拒絕他,裴策不能保證自己不會做出什麼。
半晌,江音晚抱出一堆畫卷,新舊不一,尺幅各異。
“裴策,你自己來看,我心里究竟是誰。”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0795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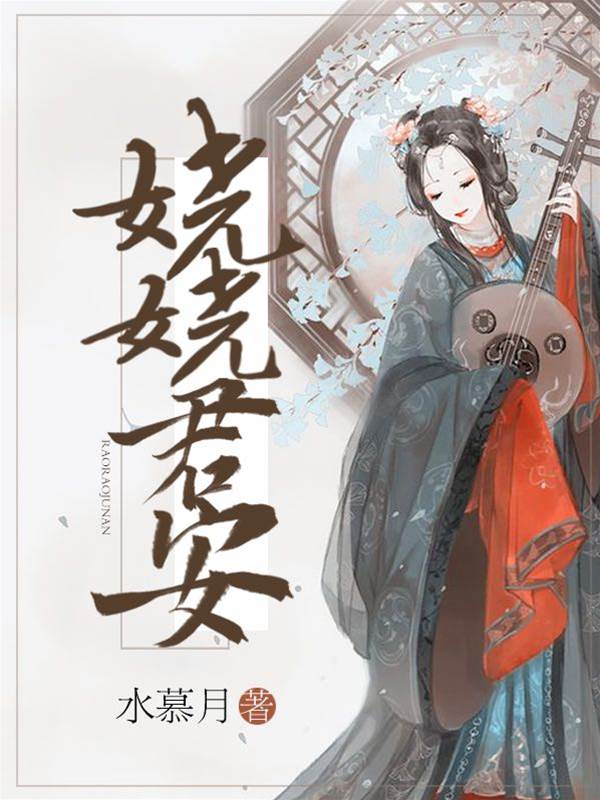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3911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