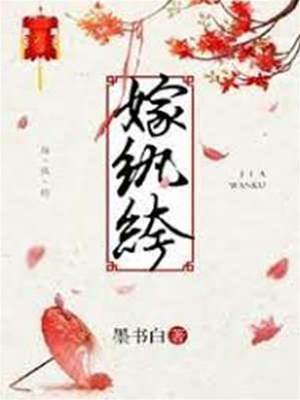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侯夫人與殺豬刀》 第85章 第 85 章
公孫鄞此番負責在中路大軍陣,打到一半,忽見一隊騎兵殺了進來,沖散崇州的步兵陣,助他完了后方的絞殺。
兩軍匯師,公孫鄞見到一布從容稱撐傘立于大雨的老者,訝然與驚喜齊齊浮現在臉上,忙上前拱手道:“侯爺先前就同在下說,山下援軍里有高人坐鎮,未料竟是太傅在此!”
親衛隨其后,為他掌傘,雨線從傘骨飛瀉而下,冷風卷起他袍的一角,頗有幾分吳帶當風的飄逸之。
陶太傅道:“云游此地,順道過來看看。”
他打量著眼前的年輕人,面贊賞之意:“早聞河間公孫氏出了一賢,能說你來他麾下,也是那小子的本事。”
公孫鄞頷首道:“侯爺心懷天下,恤萬民,公孫敬佩其氣節,甘為其所驅使。”
言罷,又引著陶太傅往馬車去:“石越麾下有一名力大無窮的猛將,撕開前鋒軍,助石越逃了出去,侯爺追敵去了,想來已在回來的路上,太傅先隨我上山,喝杯姜茶祛祛寒。”
已是晚間,這場大戰后,將士們也需要修整,眼下山上有現的營地和筑起的防墻,先留守于山上才是上策。
陶太傅道了聲“有勞”后,同公孫鄞一道上了馬車,雨珠子拍在車篷上撒豆子似的噼啪作響,馬車搖搖晃晃沿著山道前行,陶太傅的嗓音在雨聲里也慢悠悠的:“還勞煩公孫小友替老夫尋一個人。”
公孫鄞正在給陶太傅斟茶,聞言和煦一笑:“太傅且說便是。”
陶太傅道:“半月前護送糧草上山的那批薊州軍里,有個娃娃,算是我半個弟子,那日貿然上了山,這些日子想來吃了不苦頭。”
公孫鄞斟茶的手一頓,心道上次運送軍糧上山來的那批援軍里,也只有樊長玉是子了,難不陶太傅說的是樊長玉?還是說現在山上還有個扮男裝的?
Advertisement
他把一盞茶推向陶太傅,問:“不知太傅徒什麼?”
陶太傅道:“姓樊,喚長玉,是個敦厚的孩子。”
公孫鄞只覺自己剛喝進的一口茶,霎時變了百年老陳醋,酸得他都差點沒能張開,好半晌才道:“聽說您收徒對資質要求頗高?”
陶太傅何許人也,一聽公孫鄞這話,便覺他應當是接過樊長玉的,沒好意思說是自己主提出收徒,還被樊長玉拒絕了,輕咳一聲著山羊須道:“那丫頭骨好,在武學上是個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就是慧穎上差了幾分,老夫才說只算半個弟子。”
公孫鄞得了這話,頓時也不酸了,笑道:“您那弟子,晚輩見過。”
-
樊長玉一回了軍營,就去找長寧,沒見著長寧,一番打聽,才知長寧被謝七帶走了。
當即尋了過去,進帳卻見長寧在謝七軍床上睡著了,床邊放著一個不知什麼用途的竹簍子,里邊裝了些干草,海東青正蹲里邊打盹,一聽到腳步聲,立馬睜開了一雙溜圓的豆豆眼。
樊長玉看到海東青愣了一下,一時間也分不清這大隼究竟是被謝征馴好的,還是一開始就是他的。
謝七也不知自家侯爺的份有沒有暴,見了樊長玉,試探地喚了一聲:“樊姑娘。”
樊長玉看了他一眼,一言不發抱起長寧往回走。
他這里會有那只大隼,說明他也是知曉謝征份的,自己這些天一直都被他們騙得團團轉。
謝七一見樊長玉這副神,便知應當是知曉一切了,心中半是心虛半是愧疚,見要走,也不敢攔著。
長寧覺自己被搬,迷迷糊糊睜開眼,看到了樊長玉,了聲“阿姐”,又趴在肩頭睡過去了。
Advertisement
樊長玉單手抱著長寧,還能騰出一只手來撐傘,謝七見狀,忙上前道:“樊姑娘,我來幫您撐傘。”
樊長玉盯著眼前這個僵笑著討好的青年看了一會兒,終究是沒再為難他,他上邊有謝征著,一起騙自己也不是他本意。
雨水打在傘面發出“噗噗”的細微輕響,雖是天公不作,打了一場勝戰的軍營里,每一頂軍帳卻都是亮著的,將士們不便天慶功,便在帳好酒好地吃一頓。
隔著一層雨幕,那些聲音遙遠又清晰。
謝七素來機靈,斟酌道:“樊姑娘,我知道您大概惱侯爺一直對您瞞份,但侯爺這也是無奈之舉,侯爺邊一直群狼環伺,長寧姑娘之前就被反賊劫了去,侯爺怕您也有什麼閃失,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樊長玉腳步微頓,問:“長寧之前被劫走,也跟他有關?”
謝七一時遲疑,不知該如何接這話,樊長玉卻已從他這片刻的沉默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一時間心底愈發紛。
前方就是和長寧住的軍帳了,樊長玉在門口轉過頭道:“勞小七兄弟送我這一程了,里邊沒收拾,就不請小七兄弟進去坐坐了。”
謝七忙道:“樊姑娘言重了,此乃謝七分之事。”
樊長玉沒再多說什麼,進帳后,燈都沒點,黑把長寧放到床上,給搭上被子,自己則有些茫然地抱膝坐到了一旁,著黑漆漆的夜發呆。
整個西北只有一個侯爺,所以言正就是那個令北厥人聞風喪膽的武安侯?
從前覺得言正是鮮活真實的,他脾氣壞,不饒人,還挑食,但是又很善良,嫌不聰明卻總幫著,承諾的事幾乎不會食言。
他還讀過很多書,明白很多道理,是見過的最聰明的人。
可能遇到言正的那段時日,是爹娘去世后,過得最苦的一段日子,以至于在他離開后,常常想起他。
有時候是鹵了腸,想著他若是還在,大抵會皺著眉頭下筷,心中便有些好笑。有時候是翻著他做了注解的書冊,一彎腰塌背想起他曾經說的讀圣賢書都沒個坐像,立馬就坐直了看書。有時候是去糖果鋪子里給長寧買松子糖,鋪子掌柜的問怎麼不買陳皮糖了,家里明明已經沒有吃陳皮糖的人了,但還是下意識再買一點回去……
遇到難的時候,也會想,要是言正還在就好了,他那麼聰明,肯定能幫想到辦法的。
跋山涉水來找,不懼生死上戰場想護的,是那樣的一個人啊,可那個人本就是不存在的。
沒法把武安侯繼續當言正。
那個稱謂背后是赫赫戰功,是萬民景仰,也是于而言的遙不可及。
被雨淋的頭發還沒絞干,水珠從發梢墜下,將剛換下的干爽濡了一小塊,的布料在上,有些冷,卻也讓樊長玉愈發清醒。
-
謝征冒著大雨一回營,便有親衛上前為其牽馬,“侯爺,公孫先生方才命人前來傳話,讓您歸營了過去一趟,說是有貴客來訪。”
的披風掛在上很不舒服,謝征解下來丟給親衛,道:“本侯先換干爽。”
大步走進中軍帳,親兵早已備好了沐浴的熱水和。
謝征簡單洗一番后,用干帕子胡揩了揩上的水珠,撿起床邊的一套箭袖長袍便往上套,問:“回來后如何了?”
在屋伺候的是謝七,他斟酌道:“夫人瞧著還是有些生氣,屬下勸了幾句,但夫人幾乎沒說話。”
謝征微微皺眉,系好腰帶后道:“我過去看看。”
-
樊長玉還坐在帳發呆,外邊突然傳來踏著雨水走近的腳步聲,聽著似乎不止一人。
須臾,那腳步聲在帳門口站定,是謝七的聲音:“樊姑娘,火頭營煮了姜湯,我給您送一碗過來。”
樊長玉現在心里糟糟的,只說:“我底子好,用不著,你拿給其他將士吧。”
帳外的人卻并未離去,反而直接掀開帳簾抬腳走了進來。
樊長玉一抬眼,便撞謝征那雙漂亮又乖戾的眸子里。
他端著姜湯進屋,后的謝七用一只手小心護著前的燭臺,見了樊長玉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把燭臺放到桌上后便退了出去。
滿室的冷似乎都被那一盞暖融融的燭驅走了一般。
長寧一向睡得沉,被猩紅的披風裹得只剩一張圓嘟嘟的小臉在外邊,知到源,翻了個背對燭臺后,砸吧砸吧,呼吸聲又綿長了。
樊長玉看著謝征,他從前穿一布都好看,此刻著一繡著致花紋的錦袍,通的貴氣更是掩不住,只不過眼角那團淤青扎眼了些。
這會兒已經完全冷靜下來了,也想清楚了利弊,知道他好歹是個侯爺,自己當時又氣又委屈打的那一拳,終究是不妥,便抿了抿道:“抱歉,把你打了這樣。”
謝征頗有些意外地抬了抬眉梢,道:“比起上一次打的,這次應該算輕的。”
樊長玉當然知道他說的上一次是他征兵被抓走那次,又說一次:“抱歉。”
謝征原本只是半開玩笑同說這話,聽了的回答,眉頭皺起,說:“一直同我道歉做什麼?那次的確是我混蛋。”
他黑漆漆的眸子鎖著,散漫的神下像是一條收起了尖齒的惡犬:“我讀過不圣賢書,也懂禮義廉恥,但是對你,有時候總控制不住想干些混蛋事。”
他這句話甚至說得有幾分自厭。
樊長玉下意識狠瞪了他一眼,沉默兩息后,又緩和了語氣:“言……侯爺,我們談談吧。”
謝征聽到對自己稱呼的轉變,眼皮起,眸轉深,說:“好啊,先把姜湯喝了。”
他把姜湯碗遞過去。
樊長玉端著一口悶了,一碗姜湯喝下去,確實整個胃里都暖了起來。
謝征這才開口:“當初騙你,非我本意,我被人追殺流落至清平縣,巧被你救了回去,如實告知你份,只怕會招徠禍端,這才一直瞞。”
樊長玉說:“我沒怪侯爺當初的瞞。”
突然擺出一副極好講道理的樣子,卻讓謝征心底莫名升起一不安。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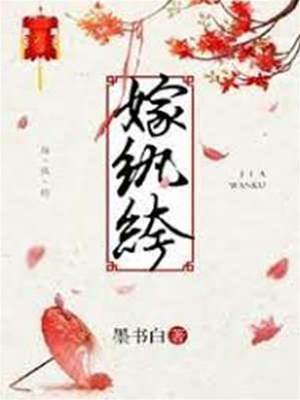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287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381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78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