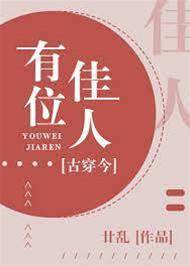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名醫貴女》 092,分娩(早更,求票)
嶽縣,李府別院,前廳。
當蘇漣漪將那麻藥喝下時,纔想起,還在前廳。
腦子一團,心中暗暗責怪自己,平日裡看似辦事穩妥,今日怎麼就做出這麼糙之事?想來,是太急躁了吧。人在急躁之時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者考慮不周全。
若是平日,會告誡自己冷靜。但面臨著即將臨盆的初螢,本冷靜不下來也不想冷靜,自己在這異世唯一的摯友即將面臨生死大劫,說冷靜,那是自欺欺人!
無論結果怎樣,麻藥已經喝下。
漣漪很仔細地觀察自己的反應,包括麻醉程度、範圍、有無影響呼吸及其他。
李玉堂在一旁站著,就這麼直愣愣地看著,猶如今日才第一次見到一般,目瞪口呆、呆若木……一切驚訝的詞彙都可用上。
漣漪不懂中醫,也不懂中藥,更是不解爲何子沒了知覺,但意識卻是清醒的,呼吸順暢,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不用呼吸機?奇妙的藥卻可以得到局麻的效果,實在神奇。
但接下來問題就出現了,蘇漣漪喝麻藥前本沒考慮到癱在邦邦的椅子上會有什麼後果,而如今才知,後果是——子一歪,即將親吻地磚。
一旁的玉堂一驚,趕忙手去接,“得罪了。”一邊接,還不忘補了句。
漣漪好笑這李玉堂也實在太“君子”了,明明是他幫忙,還有什麼愧疚?做了個鬼臉,“不是你得罪了,是我要麻煩你了。”
李玉堂渾繃,一隻手攬著蘇漣漪虛的腰肢,另一隻手則是扶著的肩,不知應要怎麼辦。是直接放在地上?還是再扶椅中?
的與男人完全不同,李玉堂只覺得呼吸困難,一雙眼不知應放在何。
Advertisement
乾咳了兩下,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儘量去想一些其他事。“蘇小姐,若是你不介意,我將你送到房間可好?”他是一片好意,但這話說出口,就有種變味的覺,將子送房間,還是……他的房間。
想到這,又趕忙解釋,“蘇小姐你放心,我李玉堂不會趁機怎樣,只是這廳堂簡陋,若是直接將你放地上又實在不妥。”
漣漪尷尬,今天算是丟人丟大發了,考慮不周。“今日是我考慮的不夠周全,與李公子無關,我也知今日之事定然讓李公子難辦,但事發急,我朋友的預產期臨近,若是在那之前我沒做好完全的準備,將面臨生命危險,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失去!”蘇漣漪越說越激,只要想起這那麼純真可的初螢消失在這世上消失,就無法冷靜下來。
李玉堂一愣,在他印象裡,蘇漣漪是鮮這麼激慌張,從來都是有條不紊,包括那一日中了春藥,也沒見的狼狽。但今日卻因爲一名子如此……
世人都說君子重義,但他們卻未見到蘇漣漪,原來子只見的友也是深如海、堅如石!
李玉堂大爲,面容也嚴肅了下來,“蘇小姐切勿著急,既然你信得過在下,我定然會全力幫你。”一手,將攔腰抱起,出了前廳,在衆目睽睽之下著頭皮向自己房間走。
“謝謝你了。”漣漪聞到了他上的一乾淨的清香,有種儒雅之。
玉堂搖了搖頭,“應該說謝謝的是我纔對,蘇小姐,自從認識了你,我學到了很多。”他由衷得說。
李家別院很小,無客房,本就是李玉堂建的一個私人空間,沒想招待過客人,連下人都很,加上管事也就不到十人,這與李府相比,已經小了又小。
Advertisement
當初修蓋之時雖設計了客房,但因從不招待客人,便荒置,若是想啓用,也得打掃個把時辰。所以,在這別院之中,除了下人們住的房間,便只有李玉堂的房間了。
玉堂十分在意私人空間,除了起居不用下人伺候外,其房間也不是人隨便進的,每一次打掃之前,都要請示墨濃。
房間整潔,單調,桌椅雕花牀,都是深紅,其餘則滿是白。雪白的牆面,不掛一幅字畫,雖單調,卻別樣乾淨。
李玉堂將蘇漣漪平放在自己的牀上,怦然心跳,一種異樣之。
上沒有尋常子那般香氣,很淡、淡的不能再淡的一種馨香,好似落花拂過襟留下的點點,若有若無,讓他留不已。
“蘇小姐,你真對在下這麼放心?就不怕在下對你不軌?”他忍不住問了句。
“放心,若是你對我心存不軌,想一日我中春藥時便不軌了,哪等到今日?”漣漪道,看人也算是準,絕不會看錯的,“李公子,這幾日你對我蘇漣漪做的幫助,我都記在心裡,有一日定會報答。”
李玉堂忍不住微微笑了,“蘇小姐言重了,應該怎麼辦,您說吧。”
漣漪也不多說那些沒用的謝之詞了,大恩不言謝,專心考慮如何實驗。因頭無法,只能用眼看。
桌上是剛剛一同帶來的銀針和匕首,“李公子,您先用那最長、最細的針,在我胳膊上扎一下。”
李玉堂心中吃驚,卻沒表現出來,修長素手執起銀針,“扎再何?”看著那隻垂下的雪白荑,指形優,有些下不去手。
漣漪想了下,“將我袖子挽起來,扎我手臂吧。”不能扎手上,若是被飛峋發現,可就不好了。
李玉堂聞言,子僵了一下,子的手臂算是蔽之,若是大家閨秀,這一生都不會將手臂給陌生男子,他這樣看了蘇漣漪的手臂,會不會唐突?
漣漪心中也猜測到了李玉堂的顧忌,從初螢得知,古代子的子都只能給夫君看的,手臂、、足,心中好笑,在現代,姑娘們穿著半袖熱不是很正常?
“讓李公子爲難了,深表歉意,但如今況急,你就照我說的去做吧。”漣漪雙眼堅定,又帶了淡淡哀求。
李玉堂輕嘆了口氣,點了點頭,將袖子拉開,雪白的手臂盡現。他忍住心中那異樣之,手起針落,爲了儘量減的痛苦,那針,迅速紮上。
“怎樣?”玉堂問,小心翼翼,略微張地看著蘇漣漪。
漣漪沒去看他,盯著頭頂的牀帳,細細會疼痛,竟毫覺不到,心中驚喜,“李公子,這一別拔出,換一,稍一些的。”
李玉堂心知應是麻藥起了作用,點了點頭,將一些的針如法炮製,扎蘇漣漪的胳膊上。
“再來。”
“下一。”
“繼續。”
就這樣,不到一刻鐘,那滿滿的一包銀針,就都紮在了蘇漣漪雪白的手臂上,好好的一條手臂,如今如同刺蝟一般。
李玉堂是有分寸的,因和李府周大夫學了醫理、背了藥方,自然也多涉獵了經脈之圖,他刻意避開蘇漣漪手臂上的幾大位,生怕傷害。
蘇漣漪鬆半口氣,爲何是半口?因爲提著的心並未落下,這最得銀針直徑才兩毫米,與手刀本無法相提並論。“將這些針都拔下去吧。”
李玉堂也暗暗鬆了口氣,終於可以結束了。
不料,他剛把所有針拔出,蘇漣漪的話卻讓他也忍不住大驚失。“李公子,麻煩你,用匕首在我胳膊上割一下。”
李玉堂終於忍不住了,衝到牀前,兩隻手撐在牀沿,雙眼直視的雙眼,“蘇漣漪,你瘋了?如今用銀針都用了,爲何你非要在上平添傷口?”
漣漪能覺到李玉堂的急切的關心,心中大爲,微微一笑,“因爲我即將做的不是扎針,而是割開的皮及臟,那種疼痛是銀針之痛本無法比擬,李公子,好人做到底,聽我的吧。”
李玉堂猶豫掙扎了下。
漣漪嘆氣,“若是你不做,一會我也會找人做的,你太善良,也許太爲難你了。”
玉堂失笑,善良?竟有人說他善良!?
李玉堂也不多言,轉到一旁的櫃子中,取出一隻木箱,從中拿出一隻陶瓷小瓶和乾淨棉布繃帶。“我這就準備做,蘇小姐還有什麼要叮囑的嗎?”
漣漪想了一想,“在小手臂面上割,不要割肘彎等部位,那裡經脈多,若是不小心割到靜脈,儘量止,若是止不住,我也不怪你。”
好在,李玉堂不懂什麼是脈、靜脈,也不懂不慎傷了靜脈、脈會有什麼後果,否則,他怎麼也是不肯下手的。
玉堂先是找了塊巾子墊在蘇漣漪手臂下面,而後拿起匕首,用藥水了幾下,在蘇漣漪胳膊上小心刺下,頓時,鮮流出,在雪白的手臂上,那紅豔的,更爲刺目。
李玉堂的眉猛然一皺,眼中是不捨,恨不得此時傷的是自己。
漣漪卻突然笑開了,“太棒了,竟不疼!這麻藥,實在太神奇了!”爲什麼口服麻藥可以做到局部麻醉的效果?在現代,這是要有專門的麻醉師,據病人質狀況制定麻醉方案。
但,這麻藥竟可以做到局麻!
與蘇漣漪的興高采烈不同,李玉堂則不知暗暗嘆了幾次氣,爲其上藥,止,而後包紮。他的手是技巧的,包紮得很完。
蘇漣漪還沉浸再歡樂中,不僅使因初螢的手有了曙,更是因發現了現代所沒有的奇藥。
的,不小心沾染到了李玉堂雪白的襟上,他有潔癖,若是放在往日,早就大發雷霆,立刻沐浴換,這件污了的,直接燒掉。
但如今,他卻愣愣地看著自己上的一抹,嚴重滿是驚訝和疼惜。驚訝是,原來這人世間竟有如此真摯的友,他雖與瀟小耽從小玩到大,但爲了瀟小耽,他是不肯傷害自己的。
蘇漣漪,真是個奇子,讓他一再,此時更是開始搖過去十幾二十年的信念,甚至對自己的人格也有了質疑。
雖然這麻藥有效,但蘇漣漪卻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每個人的制都是不同,甚至有些人天生便有一些抗藥。不知初螢從前的生活如何,但就現在的瞭解,死去的夫家應該家中不錢財。
若是如此,初螢定然也喝了不補藥或珍貴湯藥,而自己本尊這一窮二白的子,自然無法與之相比。
若是初螢對麻藥無效怎麼辦?
即便是麻藥有效,但效果不如這般明顯怎麼辦?
若是手一般,麻藥失效,怎麼辦?
這些問題,必須考慮。
“李公子,這麻藥大概能作用多久?”漣漪問。
李玉堂回想了下剛剛蘇漣漪向茶碗中倒的劑量,“按照你剛剛飲下的麻藥,最還能作用兩個時辰,這麻藥與迷藥、春藥不同,作用時間有效。”
果然!
“那如果再次飲用麻藥,可以嗎?”漣漪忙問。
李玉堂微微搖頭,“再一次補飲麻藥,其效果也不會太好,可以說,這麻藥,五天只能使用一次,用第二次效果就不如第一次。”
抗藥!?
蘇漣漪心中後怕、冷汗!好在想到了這一點。雖然在這簡陋的環境,手的時間越短、病人的危險就越,怎麼也不會做兩個時辰的手,四個小時,在沒有輸的況下,多止鉗都是不夠的,但還是要作完全的準備。
李玉堂見面微變,有些擔心,“蘇小姐,是哪裡不舒服嗎?”
漣漪道,“不是,我……還有個不之請可以嗎?”已經麻煩了李玉堂太多事,實在不好意思再開口,但事已至此,又必須要麻煩他到底。
“蘇小姐儘管說。”玉堂道。
“一個時辰之後,麻藥逐漸解開,你能不能……餵我服用迷藥?”漣漪說著,自己想咬自己舌頭,今天真是厚臉皮,求人沒個完,李公子若是不耐煩,也是應該的。
李玉堂又是吃驚,不知第幾次吃驚,“蘇漣漪,你又想幹什麼?”也不管什麼禮節,指名道姓地說。
漣漪苦笑,“因爲我怕在手過程中麻藥失效,就如你剛剛所說,第二次補上麻藥,效果也不會太好,所以,第二次補的是迷藥,破釜沉舟。”
李玉堂長長嘆了口氣,臉上滿是無可奈何,用十分無奈的眼神看著蘇漣漪,“蘇小姐,你這是何苦?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或生或死都是的命數。”
漣漪失笑,“作爲商賈的李公子怎麼也相信這命數說?這些,都是統治者用來麻醉百姓們的工,你能不知?若真是生死由命,那爲何還要尋醫用藥?若真是富貴在天,那爲何還要科舉買賣?,是我在這世上唯一的朋友、最好的朋友,面臨生死,我若不盡到自己全力,又如何能對得起這朋友二字?若是真的沒了,我會一生愧疚。”
蘇漣漪的話又對李玉堂有了很大,他從來不知,對一個人可以這樣,即便是對父母,他也從來沒考慮到這一層。
難怪……難怪瀟小耽曾說過,他是自私的。
他的心中,唯有自己,自己建立了壁壘自己居住,最後的結果卻也是越來越孤單。
他時常覺得孤單、空虛和煩躁,難道其原因,便是如此?
漣漪笑著看他,“你有朋友嗎?”
李玉堂本想說,他有個發小,名爲瀟小耽,但話到邊,卻不知是否該說,他本以爲自己對瀟小耽盡到朋友之義,但如今想來,本沒有。
他每一次,都是有事之時纔將那瀟小耽找出來,發泄喝喝悶酒。
漣漪不解地看了看李玉堂,沒再說話,只是閉上了眼。
不得不說,李玉堂的牀還真是舒服,很,下的單子想來定時價值連城,沾在上舒適無比,與自己家中的普通牀單真是天然之別,果然,有錢人的生活就是好,想來,也賺了一些銀兩,是不是也得添置些好東西,犒勞下自己?
李玉堂想了很多、想了很久,在他想繼續詢問蘇漣漪“朋友”的覺時,卻發現,蘇漣漪已睡了去。
李玉堂站在牀沿,低頭看著包紮過的手臂,突然想起一句話——爲朋友,兩肋刀。這形容君子的話,如今卻被蘇漣漪這個小子做了去,實在讓七尺男兒汗。
玉堂怕醒來,便不敢離開。
好在,房間也有桌案,今日墨濃外出不在,他便只能喚來其他下人搬來卷宗賬冊,想繼續工作,但卻怎麼也是無法集中力。一雙眼,忍不住看向牀上的蘇漣漪,腦子裡卻將的話重複了一遍又一遍。
猜你喜歡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58011 -
完結1853 章

蝕骨溺寵,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一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一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襠部支起,她笑瞇瞇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一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慍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襠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換個法子解,本王給你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麼落在她肚子裡了。
346.3萬字8.18 5891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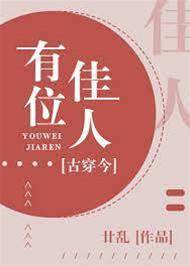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94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21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