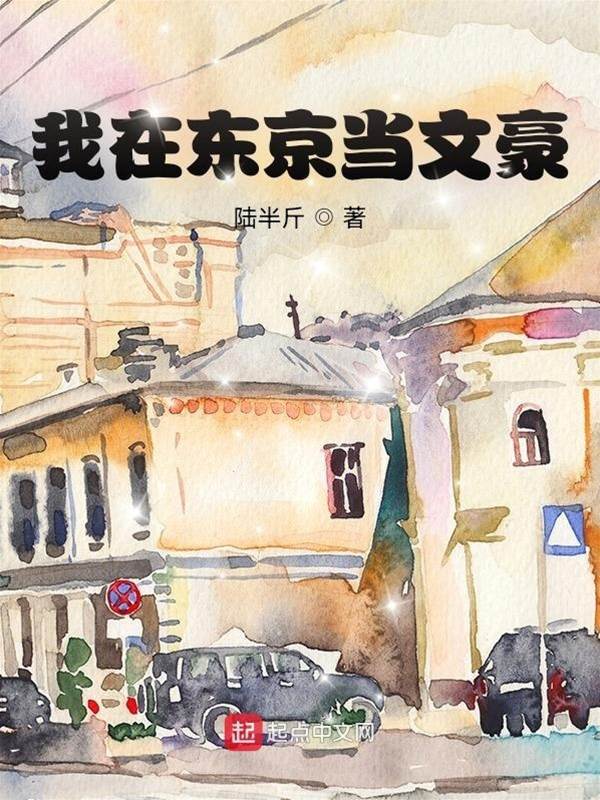《名醫貴女》 260,誤會
一素的玉容,靜立在門口,左手提著一隻食盒,右手則是向前方、蘇漣漪的方向,那修長的手指就如同鎖魂符一般。
“你到底畫了什麼,給我。”又說了一遍,本清澈如年的嗓音,因低,增了危險許多。玉容清楚的看見,畫了個人,卻因帳昏暗,未曾看清。
事發突然,又被人抓了包,蘇漣漪只覺得被乾,渾冷汗,就連吸的空氣都冷得冰肺。
玉容看著面蒼白的蘇漣漪,更覺得其中有鬼。他一直在努力信任小漣,但卻在每一次即將信任時,定要發生些什麼,撼他的信任。
蘇漣漪真的慌了,即便是巧舌如簧,也因事發太過突然,大腦一片空白,沒了主意。
“用我自己手去取?”玉容加重了聲音。
wWW●тt kan●C ○
蘇漣漪一不做二不休,將手上的紙張得稀碎。大不了撕破了臉、魚死網破,反正也未將希放在玉容上。只要這畫撕了,便沒了證據,沒有證據便不能說是潛奉一教的細作。
畫剛撕破,漣漪只覺得忽的一聲,眼前一黑,那碩大的食盒已砸上了。
食盒蓋子大開,飯菜撒了一,但最糟的是,那碗滾燙的湯直接潑向了的臉。
漣漪爲躲這湯,腳一,生生摔在地上。還好,那湯潑了一,卻沒燙傷的臉。
一雪白的玉容帶著冷笑,慢慢向前,腳踩著剛剛潑出的飯菜,好像那食盒不是他扔出的一般。彎腰,手撿起桌下的一張紙。
蘇漣漪猛然想起,玉容進時,那畫已是畫的第二張。本打算畫出四張給飛峋,畢竟鸞國畫師的作品無法做到素描這般寫實。
Advertisement
而玉容拿到的是,便是早已畫完的第一張。
完了……
蘇漣漪角帶著一種絕的笑,慢慢閉上眼睛。
從前所做的一切都化爲泡影,百必有一疏!懊惱自己缺乏警惕,惋惜之前的努力,將奉一教營地攪合得天翻地覆,暗中挑撥安蓮與邊人的關係,還得李嬤嬤和孫嬤嬤兩人捱打,費盡心思給安蓮催眠,以取得信息。
不擔心自己能否,因爲相信飛峋的實力。若出事,飛峋定會第一時間來救!影魂衛潛伏左右,傳說可以一敵百,帶離危險不是難事。
只是可惜……可惜了底奉一教的大好實際。
室很靜,悠長的靜,好像死刑犯被判刑前那煎熬的寧靜。
此時的蘇漣漪已逐漸冷靜了下來,閉著雙眼,慢慢恢復力。從進奉一教開始,便未曾睡過一天好覺,即便是偶爾休息,也是日夜顛倒,對損害甚大。而來時的路途艱難,沒有橡膠胎的木質車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駛,即便車廂墊再厚,也難以休息。
昨夜畫了圖紙,將計劃反覆思量,今日白天又爲病人看了一天病,神高度集中,所以現在遇到突發況,疲於應對,若不是天生意志力驚人,剛剛那一瞬間,怕是已暈倒過去。
玉容一時間不知如何說,不知說什麼。他愣愣地站在原地,手上拿著畫——那張惟妙惟肖的肖像畫。
畫中之人長髮,用白玉發冠束髮,瓜子臉,細眉淡淡,雙眼狹長微微上挑,鼻樑窄細,薄脣抿著,似笑非笑。畫中之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玉容。
“你……咳咳……”玉容想問什麼,話到邊卻不肯出來,最後化了乾咳。
Advertisement
蘇漣漪想到之前的努力化爲泡影,角的笑容滿是無奈,嘆了口氣。
兩人又僵持了許久。
玉容將畫輕輕放在桌上,而後輕輕蹲了下來,掏出隨攜帶的雪白帕子,輕輕去漣漪肩上的菜葉。
漣漪愣了下,有些不解,此時玉容不是應質問嗎?爲何……
以不變應萬變,蘇漣漪垂著眼,未表態,便任由玉容輕地將肩頭的飯菜去。
因爲蘇漣漪躲得即時,菜葉湯水並未潑到臉上,主要集中在上上。
玉容手僵了下,而後將那帕子遞了過去,“你自己吧。”
漣漪低頭一看,自己前的服上也滿是菜葉。
未接玉容的帕子,漣漪後退了一些,還是垂著頭,靜等玉容的反應。
玉容有些慌,從來慢條斯理略帶涼薄的臉上染了無措,“我不應該……扔食盒,但……你突然出現在奉一教營地,短短幾日營地便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讓人不得不懷疑。”
漣漪本閉著的眼,微微張開,長長睫掩住眼中的詫異。難道玉容不想質問什麼?不想問問,爲何在趁無人之時畫他的畫像?
“你……”玉容言又止,那話語中的尷尬,帶了一些。
蘇漣漪一頭霧水,玉容爲何會這種態度?玉容到底在想什麼?
漣漪腦子一時間雖未轉過彎來,但直覺告訴,玉容絕對是誤會了什麼,而誤會的容是所不知的,但玉容到底誤會了什麼?也許,可以將此事的推給這個誤會!
山窮水盡已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漣漪已沒了之前的慌張,心中異常冷靜,整顆大腦、蓄勢待發,無論對方說出什麼奇怪的言論,都會第一時間按將其圓滿。
“我……有未婚妻。”雖然男子三妻四妾是自然,但玉容還是想將此事早早挑明,即便那未婚妻,他只見過一面,甚至連話都未曾說過一句。即便那個婚姻只是家族利益的安排,他也會同意,因爲本不在乎。
劉海下,漣漪的眉頭皺了皺,未婚妻?他提未婚妻做什麼?難道玉容是因未婚妻才被迫效忠奉一教的?難道玉容加奉一教另有?
此時蘇漣漪的腦子已完全進了死衚衕,無論考慮何事,都不自地向奉一教靠攏。
等了一會,玉容得不到蘇漣漪的迴應,低頭看見那子,本修長玲瓏的子,此時蜷在牆角,那整潔得的上滿是油質污垢,既狼狽,又……引人疼惜。
玉容長長嘆了口氣,“你的心意……我瞭解了。”
心意!?蘇漣漪頭上的霧水越來越多,若說玉容知道潛奉一教的目的,也不能用“心意”二字來描述。混沌的思維中有一個答案,那答案呼之出,卻怎麼也不肯真正浮現。
“小漣,我對你也有……好。”玉容說得結結,天知道,這時他生平第一次對一名子說這些話。
“……!”蘇漣漪終於知道了玉容誤解什麼,也知道了整個屋的曖昧氣氛從何而出。這真是天大的誤會啊!敢對天發誓,對玉容絕對沒有毫遐想!……冤枉!
“對……對不起,小漣份卑微,不……不應該如此……”平日裡那自信悅耳的聲,此時帶著抖的哽咽,“玉護衛能……原諒我一次嗎?以後小漣再也不敢……這樣了……”
玉容家族富可敵國,在北秦國基甚深,北秦民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即便北秦改朝換代,慕容世家也絕不會被撼半分。從小到大,想勾引他的子甚多,甚至包括一國公主,但卻沒一名子這般……牽他心。
“這張,能送給我嗎?”玉容道。
漣漪點頭,“好。”心中竊喜,看來危急過去,但另一個危急卻也襲來。若沒記錯,剛剛玉容說他對也有好?這可萬萬不可啊!但如今,只能佯裝慕玉容,私自畫其畫像,隨後再找機會表現出對玉容死心了便好。
就在蘇漣漪心中默默篡改劇本時,那隻修長白淨的手卻進的視線,那手上拿著一枚玉佩。
雪白的冰玉玉佩。
從前無論經商還是爲,蘇漣漪都見過不奇珍異寶,自然也是識貨。冰玉,顧名思義,明的玉石,而玉石又如何能明?傳說數千石的玉石中,有可能出現一隻指甲蓋大小的冰玉,是以冰玉珍稀而昂貴。
傳聞鸞國太后有一雙耳墜便是冰玉製,價值連城。
而面前這玉佩,竟是如此大的冰玉雕琢而,蘇漣漪見到也是驚訝地瞳孔放大數倍。
“這個送你。”玉容道。
漣漪下意識覺得這玉佩絕不是那麼簡單,他收了的畫,又送了他玉佩,這不是換定信又是什麼?
驚慌擡頭,“抱歉,玉護衛,這麼貴重的東西,我……我不能收?”
玉容卻勾起薄脣,“你能看出此的價值?”
蘇漣漪後背又一層冷汗,面前這個男人真是個難對付的角,每一次都好像已信任了,但每一次卻又持了許多懷疑。
“我……畢竟從前伺候元帥的寵妾徐姨娘,姨娘喜玉石,蒐集了許多玉石,但姨娘一直憾自己未擁有冰玉,經常給我描述冰玉的麗與價值,所以……”漣漪又將一切推給了徐姨娘。
玉容牽起了漣漪的手,將冰玉輕輕放在了的掌心,“從今往後,這塊玉,便是你的了。”
“這麼貴重的玉佩,我……”漣漪正想拒絕,卻又被打斷。
“這也證明,你是我的人了。”玉容慢慢道。
“……”蘇漣漪更覺得這玉燙手得很,暗暗祈禱此話千萬別被雲飛峋聽到,否則真不知就雲飛峋現在這般暴躁脾氣,會不會不顧左右直接要了玉容的命。“玉護衛,既然您對我有好,那便是尊重我,是嗎?”
玉容一愣,不解其爲何這般說,“自然。”
漣漪擡起頭,一雙無辜的眼盯著玉容,“我承認,我對玉護衛很崇拜,但……那種崇拜還未到的程度,所以,這玉佩我不能接。”
玉容瞇著眼,卻笑了,“崇拜我?那小漣你來說說,你崇拜我什麼?”
蘇漣漪尷尬了下,“玉護衛醫高明,送了我醫學珍本,還幫了我不忙。”
“論醫,你比我更高明不是?就連這無人能醫的天疫,也是你找到的方法。說起珍本,你給我講解的西醫比珍本更有價值,而說起幫忙,應是你效忠奉一教,對我的幫忙更多一些罷?”玉容道,“小漣,你是不是還有什麼瞞著我?”
蘇漣漪無奈,將冰玉又塞回玉容手中,著頭皮道,“玉護衛,請您不要我,我承認之前真的慕你,我畫你的畫像,但那也僅僅是慕。我知道,收了這昂貴的冰玉便意味著什麼,所以我不能收。”
玉容突然發現慌的小漣甚是可,見其堅持,便將冰玉收了回。那玉,是慕容家的傳家寶,送給歷代備選主母。既然小漣已知冰玉的昂貴,如今見到冰玉便能猜到他的家世,卻未因此喜出外,更是堅持自我。單憑這一點,他對小漣的好又深了一層。
“我在門外等你,你換件服吧。”玉容將冰玉揣回懷中,溫和道。
“啊?”漣漪懵了。
玉容很想手輕漣漪的臉蛋,卻又覺得這行爲太過輕浮,終收回了手。“你的晚膳被我打翻了,我陪你去廚房,你想吃什麼,讓廚子立刻做給你。”
“不……不用了,”漣漪趕忙道,“玉護衛,老實和您說了吧,今日我確實不太舒服,也沒胃口用晚餐,我只想……早點休息。”
玉容頓了下,而後長嘆口氣,“今日是我不好,你驚了。”
“沒有。”漣漪低頭道。
“罷了,你早些休息,一會我讓李嬤嬤送一些點心過來,不要拒絕。”玉容深深地看了蘇漣漪一眼,心中疚。
“好,謝謝玉護衛了。”漣漪低頭,本不敢擡頭,也不知道如何面對玉容。
過了片刻,聽聲音,玉容已走了,漣漪這纔敢擡頭去。果然,室出了外,已無第二個人影。
蘇漣漪長長舒了口氣,癱坐在椅子上,手不停拍自己口,爲自己驚。
悲喜加!喜的是,玉容不再懷疑畫其畫像的機,危急解除;悲的是,這誤會越來越大,這可如何是好?
換了服,蘇漣漪將打翻的菜飯整理收拾乾淨,沒多一會,李嬤嬤真的來了,又提了食盒,食盒打開,飯香四溢,見那菜便知,這些菜餚皆是心準備。
“李嬤嬤,你有傷在,還讓你爲我送飯,我真的過意不去。”蘇漣漪扶著李嬤嬤,讓其坐在自己的牀上。
李嬤嬤笑道,“小漣姑娘別這麼說,老婆子這條命都是您的,送個飯又能怎麼的?”
“李嬤嬤以後不許這麼說了,”漣漪話鋒一轉,“這幾日太忙,都沒去伺候聖大人,聖會不會生氣?”
李嬤嬤嗤笑了下,“怎麼可能?現在聖大人一顆心都在蘇侍衛上,即便你去了,也沒心思見你。”
蘇漣漪的假笑卡在了臉上,僵住,“是嗎,呵呵,蘇侍衛有什麼好的?”一邊說,一邊手了自己面頰,有些扭曲。
李嬤嬤好像找到了八卦的話題,拉著漣漪便聊了起來,“要我說啊,這一次聖的眼算是有了長進,這回看上的人比之前那些回都好,蘇護衛雖容貌看起來醜了些,但給人的覺卻踏實,這樣的人過起日子來舒心。”
漣漪在心裡點著頭,是啊是啊,飛峋便是這種踏實的好人,上卻說這,“是嗎?原來這樣。那蘇侍衛喜歡聖大人嗎?”
李嬤嬤聽到這個話題,冷哼了下,“蘇侍衛可不是輕浮的男子,自然看不上那勾三搭四的聖。小漣你是沒見到,蘇侍衛對聖有多無禮,平日裡搭不理,若聖想手腳,蘇侍衛也本不憐香惜玉,每一次都將聖甩得老遠。”
“哦,這樣,”這樣我就放心了。後半句,蘇漣漪沒說出來,想到飛峋只對一人溫,心中滋滋的。
“倒是你這丫頭有桃花運了。”李嬤嬤話鋒一轉,曖昧地笑道。
“……”漣漪自然知道想說什麼,無奈,如今誤會已釀,難以解釋也沒時間浪費在解釋上。
隨便搪塞了李嬤嬤幾句,終於將李嬤嬤送出了帳子。
夜深了,越挫越勇的蘇漣漪重新拿起了畫筆,繼續畫玉容的畫像,無論發生什麼,這畫像必須準時畫出,好按時到飛峋手上,讓其著手調查玉容的份。
------題外話------
今天家裡來了客人,陪了一天,到晚上客人才離開,我才筆寫,時間倉促,了些,明天早晨應該再補上一些,算是贈送。
不早了,早些休息,晚安。
猜你喜歡
-
完結384 章

曹操之女
穿越長到三歲之前,盼盼一直以為自己是沒爹的孩子。 當有一天,一個自稱她爹的男人出現,盼盼下巴都要掉了,鼎鼎大名的奸雄曹操是她爹?!!! 她娘是下堂妻!!!她,她是婚生子呢?還是婚外子?
142.9萬字7.67 25081 -
完結556 章

全家去逃荒,她從懷裏掏出一口泉
特種兵兵王孟青羅解救人質時被壞人一枚炸彈給炸飛上了天。 一睜眼發現自己穿在古代農女孟青蘿身上,還是拖家帶口的逃荒路上。 天道巴巴是想坑死她嗎? 不慌,不慌,空間在身,銀針在手。 養兩個包子,還在話下? 傳說中“短命鬼”燕王世子快馬加鞭追出京城,攔在孟青羅馬車麵前耍賴:阿蘿,要走也要帶上我。 滾! 我會給阿蘿端茶捏背洗腳暖床…… 馬車廂內齊刷刷的伸出兩個小腦袋:幼稚! 以為耍賴他們
102.1萬字8.18 107784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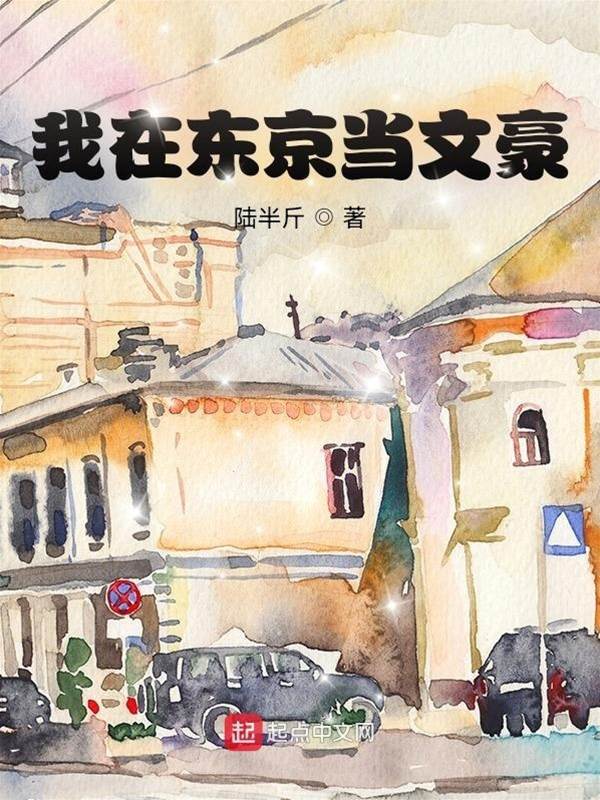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