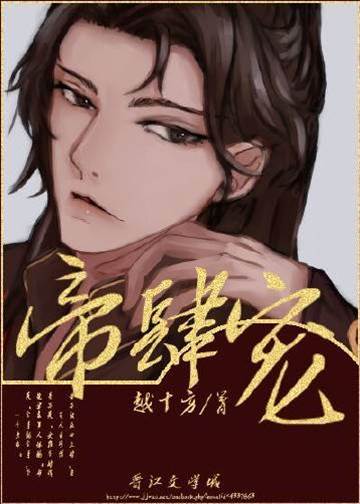《繼室難為》 第69章 第 69 章
趙義克制住想要朝那混不吝的玩意兒踹過去的腳,側與看了一場戲的貴公子對上視線,「祝大人一道吧,用過飯還有的忙。」
祝煊微微頷首,「那就叨擾了。」
三人行至廳堂,孩嬉鬧的聲音打破雨霧,稚又清脆,祝煊忽的想起了家裡瘦下來的兒子,好似從未聽他這般笑過,總歸是有虧欠的。
「阿爹!」
「阿爹!」
聽見腳步聲,兩道小影一前一後的張著手臂飛撲過來,各分了趙義一條抱著,歡喜得咯咯咯的笑。
趙義彎腰,一邊一個的抱起,故作嚴肅的問:「怎麼這麼能鬧?」只那為父者的慈卻是從眼睛里跑了出來。
兩個孩子也毫不怕他這模樣,趴在他肩膀上好奇的瞧那新面孔。
趙義掂了掂兩個糰子后又放下,語氣不覺和,「這位是祝阿叔,喊人。」
剛兩歲的小孩兒,小手握著,像模像樣的與祝煊行禮,聲氣道:「祝阿叔好!」
祝煊瞧著那倆雕玉琢的小人兒,難得生了幾分窘迫,與之解釋道:「今日來得倉促,忘了備禮,改日阿叔定給你們補上。」
肖萍聞言忍不住笑,「祝大人果真出世家,哪裡有那些個講究?」
他們這兒,也就辦宴席或是過年時會送禮,平日里你來我往的哪裡會講究那些?整日都想著如何填飽肚子,才沒工夫想這些人往來呢。
說話間,一道聘聘裊裊的影從屏風後走出,子弱柳扶風,臉上的笑也。
「這是我娘子」,趙義與之介紹,「這位是京城來的祝大人,新任按察使。」
「趙夫人。」
「祝大人。」
兩廂問候,趙義問:「寒哥兒呢?方才不就回來了?」
「後面換裳呢,都了」,楚月說著,一雙細眉蹙起,「也不怕孩子著涼了,你的裳也拿來了,去換吧。」
Advertisement
趙義也不與爭論,只指了指人大的兩個小孩兒道:「別抱他倆,又重了些,仔細腰疼。」
說罷,大步了屏風后。
楚月應了一聲,招呼祝煊與肖萍道:「先坐吧,他們換了裳就來,下人稟報的倉促,未來得及準備什麼,都是家常小菜,還二位莫要嫌棄。」
「嫂嫂客氣了,我這人像是我家婆娘說的,野豬吃不了細糠,有口吃的就行,不挑!」肖萍樂呵呵道。
他說完轉頭看向祝煊,頓時樂了。
梳著羊角辮的小姑娘著人家大,仰著腦袋瞧那張俊臉,乎乎的小兒流出了一串清亮的哈喇子。
小孩兒太了,祝煊渾僵,垂眸與那雙亮葡萄大眼瞪小眼。
「誒呦,曦姐兒,你都把口水流到祝大人上了,快收收。」肖萍說著,哭笑不得的躬把那小孩兒抱起來。
楚月聞聲回頭,一張臉險些燒起來,連忙讓人去拿一套乾淨的衫來。
祝煊剛要開口,那小婢已然疊步出去了,索作罷,了對方不安的歉意。
「阿叔……好俊!」趙曦被放在椅子上,晃著兩條小胖,喜滋滋的看著對面的男人。
楚月尷尬的厲害,所幸趙義與長子換了裳出來。
趙寒上前,先是與肖萍見了一禮,「見過肖阿叔。」
說罷,又微微側,再次拱手躬道:「晚輩趙寒,見過祝阿叔。」
年郎量比澄哥兒高了一截,也結實許多,臉上的稚已然褪去,逐漸分明的稜角顯現出了銳氣。
「三日後是犬子的冠禮,祝大人若是得閑,可帶夫人與令郎一同來觀。」趙義邀請道,又補了一句,「不必帶什麼禮,人來便好。
」
對後面那句,祝煊不置可否,只是疑,「寒哥兒年幾何?」
Advertisement
「束髮之年,只是蜀地不比京城,這裡各族多是束髮時便行冠禮,孩子苦呀,可肆意胡鬧的也就那幾年景。」肖萍與他解,「寒哥兒與趙義學武,也要軍營了。」
祝煊略一挑眉,隨即頷首。
用過早飯,祝煊換掉了那沾了口水的衫,隨著肖萍東奔西跑,時常立於眾人後,靜得仿若不在,瞧著他大事小事都親力親為,也算是知曉了為何這一日日的總不見他人影。
兩人一道回府,祝煊徑直往後院兒去,桌上飯菜已然擺好,只等他了。
「父親總算回來了。」祝允澄似是抱怨一般小聲嘟囔道。
沈蘭溪懶懶的掀起眼皮瞧來,上下掃一眼,頓時炸了。
「狗東西!」
祝煊眼皮一跳,還未開口,前的裳已經被一把扯住,那炮仗連推帶搡的趕他,「出去!別髒了我的地兒!」
祝允澄瞪圓了眼睛,一時反應不及,只瞧見自己父親被推出了門外,還頗為狼狽的絆了一下,險些摔倒。
祝煊腦子嗡嗡的,趕忙抓住的手,「怎麼了這是?」
這人臉上的怒氣不是假的,恨不得燃一團火把他燒個乾淨才好。
「我先前便與你說過,出去尋花問柳,就別再進我的門兒!看來那日你沒聽進去,那我今日也換一句,往前種種都作罷,明日你我就去府拿和離文契,往後——」
話且沒說完,沈蘭溪就被拽進了一個懷抱,箍在腰間的手臂似鐵一般,得都有些疼,憋紅了一雙眼。
「尋花問柳?我尋哪家的花了?問哪家的柳了?」祝煊摟著那發抖的子,腮幫子繃,頗有些咬牙切齒,「不信我?那解了裳來檢查,聞聞上面是不是你的味兒!」
男人氣極,胡言語著糙話,又恨恨的在上拍了下,一字一句的與算賬,「往前種種要作罷?去府拿和離文契?知道的不,還想作甚?」
沈蘭溪被他拍了兩下,不止紅了眼,更是紅了臉,氣急敗壞的嚷:「祝煊!你家暴我!」
祝煊被這聲兒喊得只覺腦袋要炸了,口起伏幾下,掐著那細腰避開被風吹得飄廊下的雨。
「你休想蒙我!你這上穿著誰的裳能說得清?」沈蘭溪被他在窗前,氣勢毫不減,「我不止知道和離文契,我還知道分家產!你如今的錢財都在我手裡,我——」
祝煊被左一句和離右一句和離,刺激得額角的青筋直跳,也變得口不擇言,「你怎的不說分產呢!」
沈蘭溪張了張,卻是沒出聲,整個人似是被雷劈了似的愣住,下一瞬,眼淚啪嗒啪嗒的滾落,了滿臉。
話出口,祝煊也覺得不妥,卻是被的反應嚇得晃了神,抬手抹去那滾燙的淚,不覺結:「哭,哭什麼?」
沈蘭溪委屈的哭出了聲,一把推開他,蹲下抱住了自己。
沒救了!
嗚嗚嗚嗚——
這個混蛋都出軌了,還是不希他死!
風聲雨聲和著委屈嗚咽聲,祝煊心疼得紅了眼眶,蹲下子拍了拍肩背,理智回籠,細細與解釋,「沒有你說的尋花問柳,今日我隨肖大人出去了,是以早上才沒與你一同用早飯,今兒一整日都與他在一,帶著從趙將軍借來的人去通了河道,又跑了兩個村寨……晌午飯是在街上吃的,肖大人請我吃的拌面,不怎麼好吃……」
他細細碎碎的說著,全然沒了邏輯,只落在背上的手一下下的幫順氣,安似的哄。
哭聲變了噎聲,一雙兔子眼睛慢吞吞的從手臂間冒出來,嗓音細帶著哭腔,「那你還吃……
我晌午還等你吃飯,都沒等到……你回來還換了一旁人的裳,上面還香香的……混蛋……」
祝煊眼皮一跳,瞬間領會了的意思,無語了一瞬,又忍不住輕笑,「這裳是趙將軍的,早上去他府上,他家孩子的口水沾到了我衫上,趙夫人過意不去,便讓人拿了一套乾淨的來給我換,後日他家長子行冠禮,你我一同去,屆時你一問便可知。至於晌午,對不住,阿年今兒駕車,也沒工夫回來說一聲,讓你平白等了,了嗎,進屋吃飯?」
沈蘭溪收回視線,抱著膝蓋一副可憐模樣,不時地噎一下,不想吭聲。
倒不是不信祝煊這話,而是覺得有些丟人,更是害怕。
今日這事雖是一場鬧劇,但的反應卻不如先前設想的那般灑,會難過,會控制不住的哭。
如果不快樂了,該怎麼辦?
「啊!」沈蘭溪驚呼一聲,兩隻手臂自發的纏上了男人的脖頸。
祝煊抱稚一般,托著的將人抱起,讓坐在他的手臂上,仰著那雙哭紅的眼,認真道:「別胡思想,不會有那些糟心事,你要知道,你我相比,你才是那個最讓人喜歡的。」
一旦辜負,此生都不會再有。
他的眉眼太過認真,沈蘭溪心跳搶了拍,瞬間了,晃了神,了腰,細兒晃了晃,哼道:「你放我下來。」
吵鬧過後,飯桌上甚是寂靜。
祝允澄悄沒聲兒的看看這個瞧瞧那個,惆悵的。
忽的,他碗里多了一塊臘,眼睛瞬間亮了起來。
「好好吃飯,別心。」沈蘭溪嗓音還帶著些沙啞。
祝允澄『哦』了聲,心下安心了不,禮尚往來似的給舀了碗湯喝。
翌日,用過早飯,祝允澄便背著書袋像往常一般出了門,往後瞧瞧,空無一人,腳步一轉,拐進了隔壁院子。
猜你喜歡
-
完結471 章

王妃日日想和離
前世葉非晚被封卿打入冷院鬱鬱而終,哪想一朝重生,竟重生在賜婚後。 葉非晚再不動情,作天作地、“勾三搭四”、為封卿納妾填房、敬而遠之,隻求一封和離書。 未曾想,那封卿終於被惹惱應下和離,卻在第二日詭異的反悔了,開始漫漫追妻路。 她跑他堵,她退他進,她撚酸他便砸了醋罈子,她要紅杏出牆…… 某王爺:乖,前世今生,冇人比本王更眼瞎。 葉非晚:…… 後來。 “娘子想要睥睨天下還是遍覽江湖?” “有何區彆?” “你若要天下,便是弒神弒佛,本王也給你奪了來。” “那江湖?” “舍王位,棄功名,此生白首不離!”
85.4萬字8.86 593972 -
完結43 章

君既無情我便休
“相爺,求您快回去看看夫人,夫人真的快不行了,她就想見您最后一面。”“你回去告訴她,她若不是真死,那麼……本相便送她一程!”——在南宮辰的心里,蕭傾泠一直都是一個謊話連篇的蛇蝎女子,直到她死的那一刻,他都不曾相信她……在蕭傾泠的心里,南宮辰…
4.5萬字8 25930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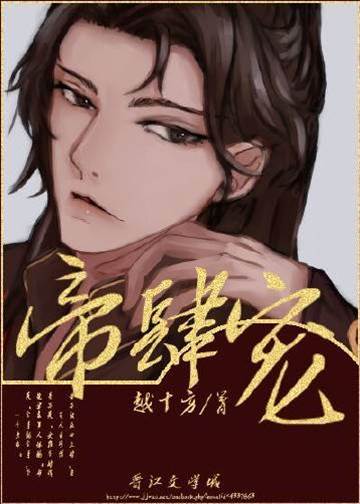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90 -
完結836 章
神偷世子妃
一朝穿越神偷變嫡女,可憐爹不疼繼母不愛,還喂她吃泔水! 為一雪前恥,她廣撒家中不義之財,誰知這劫富濟貧之事竟然會上頭……山賊窩,貪官污吏,吃人皇宮,甚至皇帝寶座……嗯,都能不放過……不巧倒霉偷走他的心,從此「惡魔」 纏身。 「娘子,說好要七天的」 「滾」 「哎,說話要算話……」 「滾」 這哪家王府的世子啊,拎回去挨打好嗎!
153.1萬字8 19827 -
完結337 章

重生后王妃嬌軟不可欺
京城人人傳說,杏云伯府被抱錯的五小姐就算回來也是廢了。還未出嫁就被歹人糟蹋,還鬧得滿城皆知,這樣一個殘花敗柳誰要?可一不留神的功夫,皇子、玩世不恭的世子、冷若冰霜的公子,全都爭搶著要給她下聘。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麼多好姻緣這位五小姐竟然一個都不嫁!她是不是瘋了?冠絕京華,億萬少女的夢,燕王陸云缺去下聘“那些人沒一個能打的,昭昭是在等本王!”宋昭挑眉,“你個克妻的老男人確定?”陸云缺擺出各種妖嬈姿勢,“娘子你記不記得,那晚的人就是本王?”宋昭瞪眼原來是這個孫子,坑她一輩子的仇人終于找到了。這輩子,她得連本帶利討回來了。
61.7萬字8.18 19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