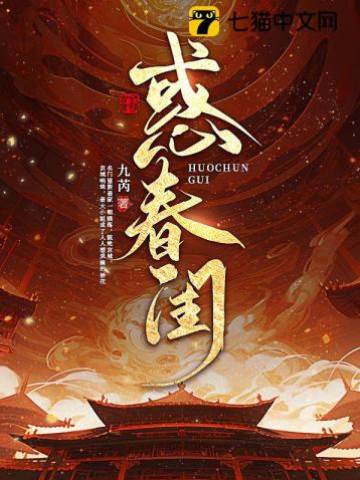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明月藏鷺》 第74章 第 74 章
傅懷硯的手扣著明楹的手腕, 上他襟的扣袢。
玉質的扣袢手的有點兒涼。
這種被他掌控緒的境況實在說不上是好,明楹在此時突然抬起眼睫,然后踮起腳吻了他一下。
素來都很生疏, 縱然之前與他接吻的次數并不算是, 但此時相的時候, 還是帶著一些顯而易見的不練。
傅懷硯襟散開,理分明, 冷白的猶如玉石。
明楹手指沒有落點, 只能被迫撐在他的肩側, 能覺到他稍微僵了片刻。
他聲音得有點兒低,垂著眼瞼看明楹:“……嗯?”
好像有點兒沒明白此時突然的行徑。
明楹指尖著他的,細細地從指尖傳遞到的思緒之中, 想了想,反問他道:“不可以嗎?”
傅懷硯只笑了聲,不置可否, 低眼看,目很深。
他的瞳仁很黑,緒也顯得淡漠,此時沉沉落在上。
明楹了一下手指, 有點兒不知道傅懷硯此時到底是怎麼想的。
每一瞬都似銀線, 似有若無地拖長在耳際。
他好像是在思忖, 又很像是在探究。
片刻之后,傅懷硯突然俯,打橫將抱起, 放到了床榻之上。
倏然騰空讓明楹下意識地勾住他的脖頸, 甚至覺到下都傳來了一點涼意, 他的步伐分明不急不緩, 卻很快就覺到背脊已經上了被褥。
擺上移,出腳踝上細細的銀鈴。
金鱗衛做事一向都很穩妥,此的布設都是新置辦的,就連被褥都是新曬的,帶著夏日午后的氣息。
明楹一只手從他的脖頸下順著拉住了他的襟,剛準備開口喚他的時候,傅懷硯突然了下來。
Advertisement
他此時襟散,明楹又是穿襦,是以廝磨之際,相,能覺到他的溫度比常人稍微冷一些,猶如冷玉,實而理分明。
明楹被傅懷硯的手帶著往他腰腹之上了,然后聽著他此時帶著笑地問道:“皇妹現在知曉是怎麼‘珠玉在前’了嗎?”
他的手腕其實并沒有扣得很,明楹的指腹能覺到他此時線條分明的腰腹,他素日看著高挑而清瘦,但是此時衫半褪,卻毫都不會顯得孱弱。
傅懷硯只帶著的手堪堪停在白玉鞶帶的上方,沒有再往下。
明楹的指尖停在這里。
其實于傅懷硯來說,實在是有點兒折磨。
他松開著明楹的手腕,然后突然聽到明楹輕聲道:“皇兄。”
手指了,“我從前對一事一向都知之甚,在我幾近乏善可陳的宮闈生活里,至多也只是聽旁人講過婚的事,誰與誰心悅,又或者是什麼難兩全的勞燕飛分。在那些旁人描摹里的言論里,又或者是書本上講述的種種糾纏里,我其實很會想到我日后會與一個人相對一生,但是這是旁人都要走的路,為了離開宮闈,我也覺得并無什麼不妥。”
“因為母親被先帝強娶宮闈,所以其實我對于這些事一直都看得很淡,又或者覺得思及這些或許一點意義都沒有,畢竟相對之人你并不想與他相守,實在是出宮闈之中再常見不過的事,而我那時見到霍離征,只覺得他合適,但也僅此而已。”
傅懷硯手指撐在肩側,低著眼聽開口。
明楹眼睛很亮,即便是此時屋中并沒有點燈,傅懷硯也能看到此時眼睛被月照亮,帶著浮的暈。
Advertisement
勾著他的頸后,在他的上又親了一下。
“但是傅懷硯,在垣陵你坐在蒸騰起來的熱氣中的時候,從前遙不可及的人步人間煙火。我那個時候就在想,我大概也懂了所謂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些人,你并不想和別人分分毫,而聽到旁人說及他過去的狼狽,你的第一反應,是會心疼的。”
的眼神不曾膽怯分毫,“所以皇兄,我已經想好了。”
傅懷硯的手指撐在的旁邊,他眼瞼垂著,緩聲問道:“想好什麼?”
他總是喜歡尋問底,明楹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別過臉去,隨后又覺得自己這樣好像是有些不妥當,又轉過來,輕聲回道:“皇兄上次說……或許太快了,言及我就算是心也只是一點,讓我可以想的再明白一點。”
“而我現在,已經想明白了。”
傅懷硯半晌都沒應聲,他的眼皮很薄,瞳仁又生得很黑,所以不笑的時候,時常帶著清冷的意味。
明楹一只手攀著他的頸后,此時后知后覺,卻實在有些看不準他現在到底是什麼緒。
晦暗的景之中,蜷了一下手指,剛準備輕聲喚他的名字的時候,話還沒有出聲,就盡數咽了回去。
他倏然低吻。
因為傅懷硯此時襟散開,所以明楹能覺到他上的,手背上的脈絡浮現,一一不在彰顯著他此時的忍。
明楹手指著他的頸后,很生疏地開始回應他。
另外的一只手從他的腰腹往上,到了他鎖骨下的那顆很小的痣。
在上京城的傳說之中,這個位置生了痣的人,多半是有緣未了,今世或許是個多種。
那日驟然升騰在垣陵上空的焰火,照亮了江南遠大片的平蕪與荒山。
流溢彩落那位于江南邊隅的小城時,大概那個時候就想明白了。
原本并不是會孤注一擲的人,也不是熱衷于博弈的子,因為過往的經歷,原本只想穩妥順遂地如人一般,并無其他所求。
只唯獨這一次。
曖昧的涌流,傅懷硯的手扣住的腰,另外一只手順著脊背向上,所到之,明楹能覺到自己也隨之僵了片刻。
明楹幾近有點兒不上氣來。
思緒也全然是錯雜的,好像是春日街頭開得繁蕪的花枝,一樹一樹皆是簇擁在一起。
花香纏,已經全然分不清來源。
窗外景晦暗,在這個時候,門外卻突然有人來叩了叩門。
川柏平靜無波的聲音在門外傳來,“陛下。”
明楹突然回神,想到川柏就在不遠之外,實在是覺得有些恥,所以忍不住抬手推了推傅懷硯。
他卻毫不為所,只低眼吻了吻的下頷,“別管他。”
川柏對著屋道:“陛下離開千金臺的時候并未做遮掩,高的人已經快找到這里了,似乎是有備而來,陛下現在是想怎麼置?”
蕪州皆在高的掌控之下,千金臺的事,高知曉得這麼快也在他們的意料之中。
原定的計劃之中,就是今日就前去蕪州刺史府,拋出高沒有辦法拒絕的籌碼,借此讓葉氏的人前來蕪州,葉氏其他人或許都會思慮些,但是傅瑋,找到另外一產鹽地這樣的大事,他未必能耐得住子。
而現在,唯一的變數,是明楹。
傅懷硯從來都并非清心寡,只不過之前念在年紀小,他又不能全然能確定對自己的,所以才數次忍著而已。
怕嚇到。
只是他的自制力,也在這日復一日的之中被消耗,但卻從未逾矩,即便是再如何,也不過點到即止,是希可以想明白。
他可以等。
而此時意迷之際,偏偏還有個蕪州的事要理。
傅懷硯現在的份是謝氏的謝熔,為了博取高的信任,金鱗衛并不適宜出面。
畢竟之后,他們還有一場易要談。
之前不過只是玩弄葉氏與高于鼓掌之中的游戲,游刃有余地周旋其中,卻沒想到,偏偏是在這個時候。
傅懷硯間上下滾了一下。
算了,不必這樣大費周章,直接把傅瑋和高全都丟進慎司監之中好好問問。
有什麼是問不出來的。
區區一個蕪州刺史和上不得臺面的皇弟而已,他若是當真想對他們手,也不過是轉念之際而已。
傅懷硯聲音喑啞,只對川柏道:“攔著。”
川柏領命,似乎是聽出傅懷硯此時語氣之中帶著的一點兒不同以往的意味,他不敢多想,只匆匆應了一下聲就離開了。
明楹抬眼,看著傅懷硯問道:“……皇兄現在準備怎麼辦?”
“不過一個區區葉氏。”他聲音有點低,“不值得誤了正事。”
“那皇兄是準備將人送到慎司監里去嗎?”明楹頓了下,“但是皇兄,你為了這件事已經做了諸多準備,若是這個時候放棄就是前功盡棄。況且傅瑋畢竟是六皇子,若是沒有確鑿證據就將他送到慎司監之中,恐怕日后會落下一個戕害親族的聲名。”
“皇兄才不過剛剛登基,先是王氏又是葉氏——”
明楹越說聲音越小,“所以我想的是,皇兄要不要還是以正事為先,這次,就先欠著。”
傅懷硯聽這的話,好像是突然覺得有點兒好笑,他扣著明楹的手,拉著的手往下。
“皇妹說得輕松。”
明楹手指被他帶著,渾上下滾起了一層戰栗。
腦海之中幾近一片空白。
他溫素來比常人稍微冷一些,帶著冷清疏離的意味,但是此時——
明楹從耳后的熱意,一寸寸地蔓延到了其他的地方。
手指頓住,喚他:“……皇兄。”
不開口還好,一開口,甚至能覺到自己的手指也隨之輕微了一下。
傅懷硯接道:“但深其害的人,是孤。”
他之前隔開了一點距離,明楹也只是約約覺到有東西在硌著自己,卻沒有想到才不過剛剛吻了片刻,他就起了這麼大的反應。
明楹抬眼,看到他手臂上的脈絡都很清晰可見。
大概是當真忍得很難。
猶豫了一下,試探著問道:“那皇兄,要繼續嗎?”
這句話才不過剛剛說完,到手指下又是了一下。
明楹實在是有些不好意思,著手想要收回去,但手腕被傅懷硯扣得,本不讓退避分毫。
一下眼睫,實在是赧,指尖微,忍不住小聲問他道:“……傅懷硯,你就不能管管嗎?”
雖然屋中并不熱,但傅懷硯此時頸間都帶著一點兒薄汗,他聽到明楹的話,忍不住又俯吻了一下,挑眉:“這怎麼管?”
他面上似有忍之,很快又道:“這只有皇妹管得了。”
這話明楹當真是不知道怎麼回,手指下意識蜷起,就聽到傅懷硯嘶了一聲。
連忙收回去,又問他道:“要繼續嗎?”
他停頓了片刻,看著此時的明楹,倏然很輕地嘆了口氣,“算了。就先欠著。”
已經從方才的意迷之中離,紛擾在外,這樣的事,他并不希是將就。
明楹聽到他的應聲,說不上自己現在到底是什麼緒,剛剛想收回自己的手腕的時候,卻發現他的手還在扣著,一點兒都沒有松開的意思。
明楹不知道他現在是怎麼想的,有點兒不明所以地抬眼,卻恰好對上傅懷硯此時垂下來的視線。
傅懷硯抵著的手腕,意有所指地了的腕骨。
“但皇妹得,幫幫孤。”
蒸騰的夏日之中,分明屋中還放著冰鑒,但還是毫不能減明楹周攀附而上的熱意。
鞶帶被走放在一旁的小幾之上,被滲的月照著,散著淡淡的暈。
傅懷硯手腕之上的檀珠早就已經被取下,現在也被擱置在小幾之上。
因為才不過剛剛取下,所以穗子此時還在很細微地。
明楹實在說得上是毫無章法,即便方才被傅懷硯帶著稍微學了學,但是也實在生疏。
傅懷硯覺得,現在盡折磨的人,還是他自己。
手腕有點兒酸,小聲問傅懷硯道:“還……沒好嗎?”
怎麼需要這麼久。
傅懷硯低眼看,半晌了笑了下,“若是當時當真要繼續的話,只會要更久。”
明楹大概知曉了他現在的意思,估計是并不想前功盡棄,回想了一下從川柏來這里到現在的時間,小聲問道:“所以現在,還是可以用謝熔的份與蕪州刺史易?”
畢竟到現在,也才小半個時辰的時間。
只是一時半會,刺史府的人遇到阻礙也尋常,繼續用這個份,高也未必會起疑,而若是整晚都讓刺史府的人不得靠近分毫,就只能用金鱗衛了,這絕對不是一個私鹽販可以做到的。
即便是高再如何蠢笨,也多半會發現端倪,傅瑋也會察覺到不對勁,不可能輕易前往蕪州。
但是現在,蕪州刺史的人畢竟還沒有找到這里,況且川柏一向很聰慧,他應當知曉怎麼理,至會最大程度地拖延時間。
之前計劃的,未必會因此前功盡棄。
傅懷硯垂著眼瞼,聽到方才的話,大抵是沒想到這個時候還將心思放在什麼易上,緩聲提醒道:“杳杳,專心。”
明楹方才還在想著這件事,此時因為他的話,突然回神,手下意識地收,倏然就聽到傅懷硯悶哼一聲。
他的聲音一向都很好聽,猶如泠泠玉石相撞,又像是檐上滴水相。
現在染上一點兒念,恰如雪雨融,轉眼就不見曾經的毫冷清。
明楹沒有看他此時的反應,思緒發散之際,卻在這個時候突然想起來傅懷硯方才說的話。
有點兒不好意思,但是想了想現今的境況,倒也稍稍退了一點兒恥。
活了一下自己已經泛酸的手腕,抬眼問道:“這樣,與繼續,為什麼繼續會更久一些?”
是當真有點兒想不明白。
分明現在也很累。
都這麼久了。
傅懷硯斂眉看,稍稍俯,眼眉之間帶著一點笑,瞳仁卻又著晦暗的緒。
好像是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兒天真。
他的語氣輕描淡寫,手指在的腕上。
“若是方才繼續的話,皇妹。”
“以為孤一次就能放過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169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107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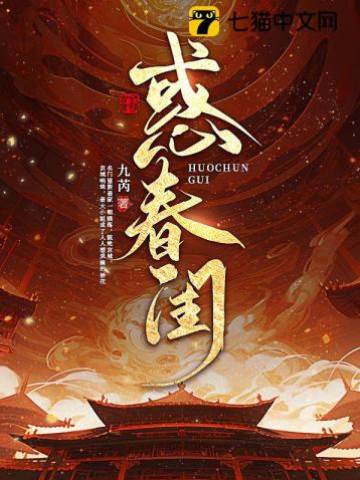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