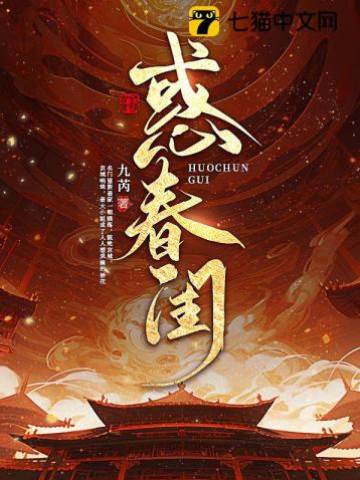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阿瑯》 141,
蕭珩眼底布了淡淡的一層紅,面帶倦,目落到不遠的門邊。
聽到甲一的話,他拂了拂手,示意甲一等會兒再說。
他略顯疲憊地朝門邊地阿瑯笑了笑,腳步頓住,凝視著。
阿瑯聽到腳步聲,將向遠天際的目拉了回來。
蕭珩穿著的還是昨日的那裳,雖看著整潔,他的鞋面上卻沾了些塵土。
看起來行了一些路。
這會上京的路面剛灑掃過,哪怕走過南街十三巷,也不會有這樣多塵土停在他的鞋面。
他昨日去了城外嗎?
“你來了?”問道。
阿瑯引著蕭珩進了書房。
看了眼甲一,讓他站在門外,然后把門扣上。
蕭珩沒有,只是站在那里看著,見神端凝,并不像是需要安的樣子。
阿瑯拉著他落座。
滿肚子的話真不知道挑哪句話說出來才最合適,最后索找了個不那麼敏的開場白,
“欽天監的婚期定好了嗎?若是我們大婚,你希我們婚后是什麼樣子?”
蕭珩雖然無比期盼著這一日,卻沒想到會在這個當口提及。
但他以為是特意尋找話題,至于原因,他還無從得知。
兩人面對面坐著,他微微傾,握住的手,盡量輕松地順著說下去,
“當然是希我們倆既能琴瑟和鳴,又能攜手走到我們相終那一日。”
“我會竭盡全力,讓你不后悔嫁與我,你呢?你有什麼想要我改的?”
這是蕭珩第二次說到這話。
阿瑯笑笑,“我希能和你一輩子平平安安到老,到我們滿頭銀發的時候,再樂樂呵呵地死去。”
蕭珩握著的手,將拉了過來,坐在自己這邊,
“你這話真是說到我心坎里去了。”
Advertisement
“你可知道,這一個晚上,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只要能跟你走完這輩子,我就是沒有下輩子也愿意!”
阿瑯頭如同鯁著刺,道,
“你又胡說,上次我被擄走回來后,你也是這麼說。”
“你沒有我,還有別的親人,陛下,娘娘,還有,你的父親。”
“那不一樣。”蕭珩著的發鬢,“不能這樣比,你給我的,沒有任何人能給我。”
阿瑯相信他說的。
沉了沉氣,“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蕭珩怔住,沒,過了會,“我也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阿瑯著他,說,“那我們就一個個的說。”
“你說你昨夜想我想了一夜,我同樣也是。”
“我甚至害怕,若是再來一次劫殺,會怎麼樣。”
“也許,不僅我沒命了,你也沒命了。”
這話讓蕭珩停了在背后輕的手,“胡說什麼。”
“我是認真的。”
“你還記得上次侯府上下一百來口都是怎樣的嗎?”
“那些人就是想來拿父親手中的一件東西,我們都以為是胡琴里掉落出來的那顆。”
“其實,不是。”
阿瑯靜默了一下,說道,“我昨日夜里整理父親的手稿,看了很多父親從前的手稿,讓我更加了解父親,母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蕭珩起初眼里還帶著些迷茫,隨著阿瑯越說越多,眼睛逐漸布滿震驚。
“父親當年出征前就發現了一樁,不是太確定,于是讓母親留在上京。”
“誰能想到……”
“當年父親之死的真相,我已經知道了,除此之外,我還知道了一樁。”
“?”蕭珩說了一句。
……
昨日,蕭珩送走了阿瑯,見了甲十三和同泰寺的那個短仆后,整個人僵坐在椅子里,在書房里呆了不知道多久,許久,許久,他才出了書房,讓人備馬,趁著宵前,趕著去了萬壽觀。
Advertisement
萬壽觀,同泰寺再過去一點,是老郡王清修之地。
從前,這里不過是個小道觀,因為老郡王在此清修,慢慢的擴建,如今的規模,是原來的兩倍不止。
他策馬狂奔,到了萬壽觀外,在岔路上分道前,不自地勒著韁繩,停下腳步。
甲十三的話,他是相信的,那個短仆,他見過之后,同樣相信他說的不是假話。
他覺得這個世界真好笑。
他的母親,為了自己逃命,丟下了他和兄長。
而他的父親,為了母親的命,丟下了他和兄長。
父不父,母不母。
老郡王妃時常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故而對更悉些。
至于那個給與他脈的男人,在他被老郡王妃帶到外祖家后,本就不曾真正地關心過他。
終于,他翻下馬,將韁繩丟給了跟過來的侍從,敲響那萬壽觀的大門,見到了他的父親。
蕭溢真在打坐,見到蕭珩很是詫異,問他為何而來?
蕭珩心思正恍惚,聞言坐下,拿出一副卷軸,緩緩打開,燈火照亮一細如雨的奇怪件,以及畫上一幅人像畫。
“父親,不知你見沒見過哪派異人用這種暗?”
蕭溢起先未答,端詳片刻方狐疑道,“未曾見過,此人是誰?”
蕭珩說道,“父親知道前些日子阿瑯失蹤了兩個月吧?侯府一門,上下一百來口仆人,全部不見。”
“當時就有這個人在場。”
蕭溢的目一寸寸在畫上一,最終緩緩點頭,
“見過類似的,在異地的軍中,但和琴弦差不多細,沒有如畫上的這般細。”
蕭珩有些失的樣子,“父親跟著陛下走南闖比,是見過世面的。如今,竟然連你也不懂。”
蕭溢打量了下兒子的神,“是不是畫錯了,也許世界上本就沒有。”
蕭珩面一如從前,面無表的,“不可能的,這是阿瑯見過的人,一一畫了出來。”
蕭溢有些驚訝,沒想到靖安侯之,竟然還會這些。
他見著蕭珩面誠懇,那深邃敏銳的目,仿佛能照見人心,凝視了兒子半晌。
點頭不再繼續追問下去,
“好,我派人帶著這幅畫爭取早日查到此人的底細。”
蕭珩點點頭,起,準備離開。
忽而就聽蕭溢到,
“你即將大婚,陛下了這麼多年的親王位置,這次終于可以給你賜了下來。”
蕭珩又轉過子,看著坐在團上的蕭溢。
“雷霆雨,皆是君恩,陛下賞賜,我自是歡喜,不賞,我做好自己的差事即可。”
蕭溢慢慢地站起來,撣了撣道袍,慢慢悠悠道,
“今上,這是什麼用意,你知道嗎?”
蕭珩反問,“那你說是什麼用意?”
“你且想想,滿朝大員都能想出來的,你能說你想不出來嗎?”
“我不知道滿朝大員會想些什麼,你若有事,不凡直說。”
蕭珩笑了笑,
“你要記得,今上他是天子,既然是天子,自己怎麼樣,并不重要。”
“對手怎麼樣,其實也不重要,他要計較的是這一殿朝臣究竟更愿意立誰為儲君。”
“帝王心,就是永遠都會算到別人的坎上。”
蕭珩聽完蕭溢的話,輕輕‘呵’了一聲,
“陛下的儲君,還需要搖擺不定?太子如今子大好,父親還擔心什麼呢?”
這下,到蕭溢輕輕‘呵’了一聲。
“陛下冊封你為親王,你以為是給你恩寵嗎?表面上是抬舉了你,可往后,你要走的路才更艱難。”
“最起碼,你如今手上的差事就要卸了,給你親王的份,是要以這個份來束縛住你啊。”
蕭珩離開的腳步微微凝滯,旋即快步邁出門檻,離開了萬壽觀。
天亮,他沒有回王府,而是直接到了靖安侯府。
此刻,和阿瑯面對面地坐著。
阿瑯起,把窗欞推開,芒一泄在上,將鍍金。
“父親本想借著那一次出征,拿到一些證據,等到陛下親征回朝,然后再稟報給陛下。”
“他發現和陛下一同打江山的重臣,有了異心。”
蕭珩著袖口上的那圈金,眉頭皺得死,沒有吭聲。
阿瑯靠在窗欞邊,眉眼里也浮出些許黯。
“我沒有依據,除去那兩封手書。”阿瑯幽幽地說道。
真正的危險,還藏在深似的。
蕭珩凝眉,“昨日你走后,我派出去的探子,回來告訴我,當日你被關押在同泰寺時,有一個人也在不遠。”
“昨天夜里,我也去了萬壽觀,最后從安的一個小道士口中得知,那兩個月,原本要閉關的人,并沒有閉關。
要閉關的人沒有閉關,那說得就是老清河郡王了。
阿瑯知道這種事沒辦法那麼快接,只沒想到,蕭珩說起來時,波瀾不驚。
和他的表是一樣的。
阿瑯口氣翻涌,強忍了忍,才又道,“你有證據嗎?”
蕭珩搖了搖頭。
“瑯瑯。”他了一聲阿瑯。
阿瑯抬眼看他,就見他面無表的,“瑯瑯,你信我嗎?”
不等答,他說,
“靖安侯府的一切仇恨,我都為你討回公道。”
“英烈為國捐軀,就應該讓后世銘記。”
他不是喜歡在暗中將一切握在手中翻來覆去的挑弄嗎?
好,那就看誰,更加會來的吧。
反正無惡不作的人,不是他。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175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496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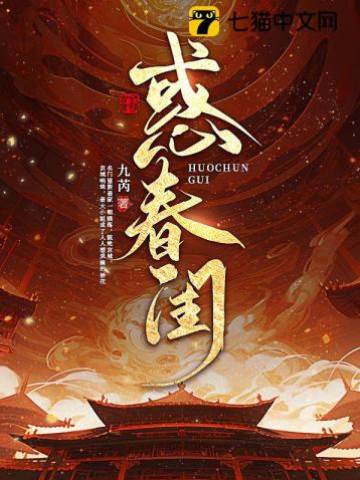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