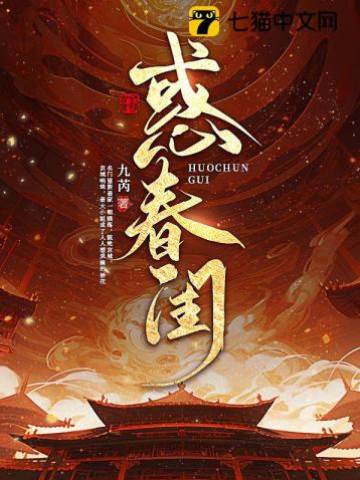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花嬌》 第28章 第 28 章
舒筠這一夜承了極大的力, 緒瀕臨崩潰,那口氣一直還懸在嗓眼,直到此刻見皇帝, 繃的力卸下,晶瑩的淚珠一顆顆出眼眶,泣著不知作何反應。
本就格外白, 哭過之后越發薄如蟬翼, 紅紅的一片跟胭脂般暈開, 裴鉞都舍不得,卻又不忍淚流不止,只抬起指背輕輕刮了刮鼻粱,
“不怕,你放心, 華老太醫隨時待命, 劉太醫和張太醫會流守在府上,直到你母親大安,華太醫的藥則不離,朕絕不準許你母親有事, 你信朕好嗎?”
得了他這話,舒筠紅彤彤的小一癟,方敢將哭聲放出來。
差點失去母親的害怕快要倒的神志,哭得撕心裂肺,子跪坐在裴鉞跟前輕,仿佛搖搖墜的柳枝無支撐。
裴鉞也沒阻止,任由發泄, 眼眶里布滿, 眼眸哭過越顯狹長, 像個懵懂的小狐貍,裴鉞明知現在該是最難最害怕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此刻的模樣極為可,也惹人憐。
這個姑娘無一不好,像個瑰寶讓人忍不住想珍藏。
裴鉞輕輕地將攏在懷里,也不敢用太親的姿勢,只讓靠在他膛,讓有個依靠。
舒筠著他結實又堅的膛哭過一會兒,心里好了,哭完后,方覺額頭磕得有點疼,
“陛下怎麼哪兒都這麼?”了額角,有口無心抱怨,慢慢直起腰,離開他懷里,
裴鉞險些沒維持住帝王的面,角微微繃,沒接的話。
舒筠也沒指他回答,緒發泄完便覺肚子,好在裴鉞有準備,給上了一盅燕窩粥,一碗人參湯。
Advertisement
舒筠也吃不下太多,喝碗粥裹腹,參湯吊著神氣,靈臺方恢復一清明。
抬袖拭去眼角的淚痕,催著皇帝回去,“夜深了,害您跑一趟,您明日還要上朝,快些回去歇著。”
裴鉞目卻落在了指甲,那指甲上殘留一些污,他捧了過來,“這是怎麼回事?”
指甲明顯有一條裂,延至□□里,該是很疼。
舒筠無暇注意這些小傷,被裴鉞提醒才想起是老太太與二夫人害了母親,眼底織著憤,兇地告狀,“我打人了,我撕了我二伯母的。”
裴鉞著實吃了一驚,舒筠在他印象里就是個糯可的小姑娘,了就吃,困了就睡,不高興就哭,竟然還會手,裴鉞用桌上的巾替清理傷口,問道,“何事?”
舒筠大抵將經過復述,也將陳文舟的事給坦白,皇帝今夜出了錦衛,意味著舒家的事瞞不了他,舒筠若再遮掩便是沒事找事。
裴鉞聽了陳文舟的事,臉上并無明顯變化,只是想起舒筠被氣得與人打架,他也跟著有些慪氣,能把他的小姑娘炸的小獅子,可見,“可惡至極。”
舒筠好歹將人打了一頓出了氣,裴鉞卻沒有,這點子慪氣一直延續至書房。
劉奎見他臉十分難看,只當人沒救回來,慌忙問,“陛下,舒夫人這是如何了?”
“舒夫人已轉危為安,”裴鉞吁了一口氣,皺著眉進去換裳,邊換邊氣道,
“朕的,那麼溫良善的姑娘,都給氣的用爪子抓人,你說那婦人多可惡。”
都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當朝皇帝遇到蠻不講理的后宅婦人,也是無計可施。
劉奎只覺可笑又可氣,表便顯得十分稽,
Advertisement
“是是是,可見姑娘也是有勇有謀,不人窩囊氣。”
裴鉞正愁沒地兒發火,眼刀子扔過去,“是你喚的?”
劉奎連忙了自己一個響亮的掌,“奴婢失言。”
裴鉞換好裳,張開手臂任由劉奎給他系帶,
“你說,朕總不能遣兩名暗衛去將人給打一頓?”
這事做倒是做得出來,就是有失面。
劉奎憋著笑,不接話,恭敬地迎著皇帝去殿歇著。
裴鉞剛上了塌,忽然想起個法子,
“你明日清晨,以朕的名義下一封手書,申斥太常寺卿舒茂風,家風不嚴,后宅不寧,他為家主疏于管教縱容婦人為惡。”
“奴婢遵旨。”劉奎上前替他掖被,
裴鉞剛躺下去又折起,
“朕記得那舒家二房也有個兒子?”
自從曉得舒筠真實份后,藺洵便將舒家的事給查了個底朝天,劉奎記在心里隨時預備皇帝垂詢,故而立即答道,
“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舒謙,正在國子監教,小兒子舒讓,十分紈绔。”
裴鉞臉一沉,“難怪如此猖狂,自己有兩個兒子便覺了不起,欺負三房。”
“可不是,”劉奎見他沒有睡的意思,干脆又給他奉了一杯茶,“舒三夫人當年出嫁舒司業,頗有些嫁妝,三老爺夫婦原先打著招婿的主意,以奴婢瞧,那楊氏怕是擔心好旁落,一心想吞了三房的家產,方才可勁兒折騰。”
裴鉞聽著來氣,抿了一口水擱在一旁,吩咐道,“你看著辦。”
“誒....”劉奎心里有數了。
裴鉞闔眼的時候,還在眉心,“朕得替想個一勞永逸的法子。”
劉奎掩了掩,暗自嘀咕道,“陛下怕不是在養兒吧...”
他嗓音放得極輕,以為皇帝聽不見,卻見裴鉞扭頭過來,眼神銳利盯著他,“你說什麼?”
“沒沒沒,老奴什麼都不敢說....”劉奎忙不迭退下了。
裴鉞回味劉奎最后那句話,盯了暗一會兒,心復雜地闔上眼。
夤夜,風無聲涌,舒家父倆都杵在正房未走,舒瀾風舍不得離開妻子,誰也勸不,最后在蘇氏床榻外安置了一羅漢床,舒瀾風便睡在那里。
舒筠畢竟是未出閣的姑娘,被勸回了房。
三位太醫流值夜,單嬤嬤給安排在正院東面的兩間廂房歇著,待回來室,發現華老太醫留下的那名,已幫蘇氏清理干凈子,那大約十來歲,面相十分稚,語氣卻相當沉穩,
“嬤嬤,您去歇會兒,師傅待,讓我寸步不離舒夫人。”
單嬤嬤眼眶含淚,哽咽著朝施禮,“辛苦姑娘了。”
至于一夜驚四位太醫,留守的劉太醫也很好的給了解釋,
“得虧了藺指揮使,他無意中路過舒家聽說夫人出了事,恰恰前段時日太上皇過問尊夫人病,藺大人不敢大意,遂稟報了圣上,圣上念著太上皇掛懷舒家,囑咐我等務必救回夫人。”
舒瀾風連著對皇宮的方向,磕了好幾個頭,老淚縱橫道,
“謝太上皇隆恩,謝陛下隆恩。”
即便藺洵有意瞞蹤跡,多多還是被長房窺見了苗頭。
大老爺舒茂風夜里回來,聽門房稟報錦衛上了門,唬得失聲摔碎了茶盞。
要知道錦衛非大案不輕易出,二弟賦閑在家,三弟一介小小司業,哪怕是捅破天也出不了什麼大事,錦衛上門只可能是因為他。
“因什麼事?”
門房的管事面含懼,“瞧著像是三夫人病危,帶了人過去,指揮使沒多久便離開了,留了一名錦衛,小的不敢怠慢,將人引倒座房歇著,也悄悄遞了銀子過去,不過人家沒接。”
沒接可不是好事。
舒茂風脊背開始發涼,在書房踱了好一會兒步,六神無主,別看他在家里威風,到了外頭,這三品太常寺卿在權貴遍地的京城實在不夠看,平日也是點頭哈腰,極起腰板,這還是跟淮王府結了親,方才有幾分面。
待回了房詢問大夫人,方知道家里出了事,老太太伙同二房算計三房的婚事,大夫人方氏一臉不屑,
“這就是你們一家子干出的好事。”
舒茂風如鯁在。
先是他兒搶了舒筠一回親,如今二房又要搶第二回。
著實是欺人太甚。
只是這些事都是關起門來的宅家務,怎麼會驚錦衛?
舒茂風一夜戰戰兢兢做了不噩夢,直到次日上朝,人剛踏進衙門,便得了司禮監一道申斥,那小公公人站在廊廡下,嗓子又尖又細,
“太常寺卿舒茂風,治家不寧,縱容婦人為惡,朕深惡之,責爾停職半月,回家整肅。”
大老爺膝蓋一,就這麼跌在臺階下。
清晨正是人來人往之時,這事很快在署區傳開了。
回家整肅事小,停職半月事大,這半月必定是底下兩名卿代他理政,等他回來,誰知是何景,這廂丟臉丟大發了,以后升遷更是別想。
他剛剛借著兒東風,攀上淮王府,轉背被皇帝當眾申斥,別說他抬不起頭來,就是兒以后在王府也要被人笑話。
舒茂風恨死家里糊涂的老母,他憤地擰著行囊回了府,怒氣沖沖直奔后宅,彼時老太太正與二夫人在暖閣里說話,聽得蘇氏昨夜在鬼門關走一遭,頗有幾分幸災樂禍,不想外頭傳來婆子驚呼聲,接著一道寒風裹進來,大老爺沉著臉皮笑不笑踏。
他先看了一眼自己老母,再瞅著二夫人那副明樣,氣得頭昏眼花,
他將丫鬟沒來得及收好的錦杌往前一踢,大馬金刀坐在二人面前。
老夫人見他如此神,心里有些發怵,“你這是作甚?”
舒茂風口猶如油鍋似的,冷笑道,“我的好親娘,您可真是讓兒子長臉。”
老夫人云里霧里,卻也聽出話里的諷刺,老臉掛不住,“有話好好說,別怪氣。”
“好,那我問個清楚,昨個兒母親與二弟妹做了什麼?心里沒數?”
老夫人嚨一哽,心里自然有些發虛,只是面上卻不顯,皺著眉斥他,
“宅一點家務事,哪里到你一個大老爺們心。”
“呵呵呵。”大老爺譏諷地笑了幾聲,眼眶發紅怒道,“是,您也知道是一點宅家務事,可現在,咱家這點家務事弄得滿朝皆知,陛下今晨令司禮監的公公站在署區門口,當眾申斥兒子,說兒子治家不寧,縱容婦人為惡。”
“讓兒子停職半月,回府整肅。”說到最后,大老爺氣出哭腔,滿朝文武還從未有人過這等恥辱。
皇帝這一招看似只是申訴,實則是斷了大老爺仕途,更影響長房和二房幾個爺科考,也將是舒家長房與二房子嗣背負一生的罵名。
老太太一呆,手里的杯盞落,上的一瞬間消失得干凈,“怎...怎麼可能...”
大老爺怒而拔,“怎麼不可能?兒子今日了全京城的笑話了!”他氣得在屋子里來回踱步,見二夫人臉上猶有幾分幸災樂禍,氣不打一來,指著,
“你個...你個無知婦人,你還覺得置事外不是?你兒子不在朝讀書麼?你兩個兒子以后難道不科考了?還是你打算帶著他們回你們楊家夾著尾做人?”
二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子,聽了這話臉豁然一變,也跟著站起,叉腰怒道,
“大伯兄可別把火往我上撒,搶舒筠婚事的是你兒,不是我兒,我昨日還被那小蹄子打了一頓,你看我的臉...”
二夫人臉上紅痕遍布,角更是摳出幾塊痂,若非今日要來聽蘇氏笑話,還沒好意思出門,因著被舒筠撕爛了,這會兒說話便扯開了傷口,疼得厲害,連著氣勢也弱了幾分。
大老爺看著二夫人這副胡攪蠻纏的樣子,氣得跺腳,“哎,都怪二弟過于懦弱,方縱容了你這悍婦,來人,將二老爺請去我書房,我要他休妻!”
休妻不過是嚇唬楊氏的話,楊氏卻當了真,眼珠子幾乎瞪出來,氣得往大老爺后一撲,
“你敢!”
大老爺被這架勢唬了一跳,他原先覺得大夫人方氏不夠溫,子傲慢,如今瞧了二夫人楊氏這潑婦樣,方覺妻子已經算完了,他怒得甩開,
“放肆!”
楊氏那點力氣哪比得過高大的男人,被大老爺這麼一甩,人往后撞在博古架上,窸窸窣窣的件全部倒下來,恰恰砸了一,楊氏嗚呼痛哭,疼得倒涼氣,開始在屋子撒潑打滾。
大老爺走了老遠還聽得的哭鬧,方覺皇帝申斥的沒錯,這個家著實太不像樣,是該要整肅一番了。
他一面虎虎生風往書房去,一面嚴詞厲吩咐管家,
“鎖門,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許出府!”
二老爺子,哪里敢休妻,自然是央求兄長開恩,大老爺也曉得休妻不大可能,畢竟楊氏還生了幾個孩子,得為孩子將來著想,只是決不能這麼輕饒了楊氏,非要楊家來人將楊氏接回去,想嚇唬楊氏一番。
楊氏起先還鬧,后來見大老爺真格的,沒了半分氣勢,可憐兮兮哭著求,只道自己以后本本分分做人不再作妖。
大夫人在這時了面,“你是什麼德我能不知?我告訴你,想留在舒家也可,其一,中饋出來,第二,去城外尼姑庵修行一年。”
大老爺這回堅定支持妻子,要麼休妻,要麼去尼姑庵,兩相其害取其輕,二老爺選擇了后者。大老爺曉得朝中史如今都盯著他,也不含糊,干脆利落著人將楊氏卷起塞馬車,連夜給送走了。
至于老太太,大老爺則讓在佛堂吃齋念佛,不許再管府上的事,老太太作威作福多年,愣是被氣出個好歹,泱泱昏了過去。
三房這邊誰也沒摻和長房和二房的事,舒瀾風告了幾日假,舒筠一心一意照料母親。
有了太醫心調理,蘇氏病一日好過一日,如同死過一次,心里越發看開了,不再催促舒筠的婚事。
這當中,陳文舟聽聞蘇氏病重,攜禮上門探,他不能去后宅,便在書房給舒瀾風請安,幾番問婚事,見舒瀾風心不佳,便忍不言,待小廝送他出門時,卻見一俏生生的姑娘立在竹林石徑口子上。
這僅僅是陳文舟第二次見舒筠,可那日相見,模樣便刻在他腦海里,揮之不去,他克制著緒,隔著數步距離,朝拱手,
“舒姑娘安。”
舒筠面帶愧回了一禮,開門見山道,“冒昧攔公子大駕,實在有事相告,先前聞公子求親,舒筠倍慚愧,今日不防告訴公子,我心中有人,此生非他不嫁,怕是得辜負公子一片誠心。”
陳文舟一呆,一貫沉靜的面容瞬間閃過諸多復雜的緒,只是他與舒筠到底陌生,哪敢多問,人家姑娘如此斬釘截鐵,可見是主意已定,他心中自然是難的,卻也不敢輕易表出,只憾地嘆了嘆氣,朝再拱手,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187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496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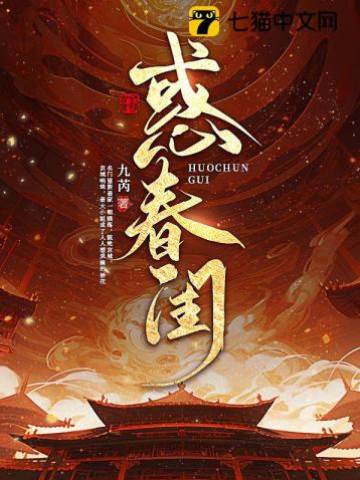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