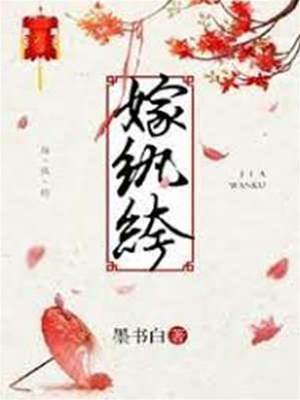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長寧將軍》 第 58 章 第 58 章
姜含元便如此,被畔的男子帶回到了寢閣。
他命庭中的值夜宮人全部散去,閉了門,走到的面前,抬手,為解起他方才為披的氅。他微笑著,用幾分帶著責備似的寵口吻,低聲抱怨:“不小的人了,怎像個小娃娃似的,半夜不睡覺,出去跑。外頭風大雨急,你沒瞧見?”
他解了氅,又取來帕巾,為細心地拭著飄沾在面龐和脖頸的雨水。
姜含元定立不。
“為何如此行事?”
盯著面前這張若無其事帶著笑意的臉,問道。
他抬眸,看了一眼,沒回答,那手仍繼續替臉,揚手,一把推開。
“我聽到了你和劉向說的話!為什麼這麼對待無生?”
“一個僧人而已,他何罪之有?”
他和那一雙閃爍著怒氣的眼眸對視片刻,臉上笑容慢慢地消失。
“他不是沙門比丘嗎?”他淡淡地哼了一聲,也擲了手中巾帕。
“據說年紀輕輕,便悟大道,是位得道高僧?待在石頭里做什麼?遣他去個該去之地,做和尚該做的事,豈不更好?”
姜含元怒極:“說得好聽!隨后監視,看管起來,奪他自由,他生不如死,是不是?你的這一套,你當我不知?這就是你所謂的他該去的地方?何況,他已經快要死在你送他的這條路上了!”
他也未否認。他雙閉,目落在的臉上,似在端詳審閱著。
片刻后,他漠然地道:“他既是出家之人,當知一切諸報,皆從業起。若真死了,也是他命。”
姜含元的雙手已是控制不住,在微微發抖了。看著面前這個冷酷得如同陌生人的男子,幾乎無法相信,就在片刻之前的今夜,還曾和他耳鬢廝磨親無間。為他所,為了即將到來的分離而暗自糾結,無比惆悵,甚至,竟生平第一次對的將來景愿生出了搖。開始考慮,是否可以真的將的余生和這個男子系在一起。
Advertisement
此刻再看他,看面前這張悉又突然陌生無比的臉,忽然想起母親,想起皇城里的那個至今仍然高高在上或許永遠都將如此的大長公主,想起他也并不只是束慎徽。
被他對展出來的迷,忘記了,他也是一個天家之人。視人命為草芥的那種殘忍,本就是流淌在他們那所謂高貴的脈里的與生俱來的共。而他,只會比別人更加殘忍。這一點,在當初獨自來到京城探他之時,便已親眼見到。
只是昏了頭腦,忘記了而已。
本已雙手握,得拳,最后,又慢慢地松了下來。
“那麼,他到底犯了何罪,哪里冒犯到你,你要對他施加如此的懲罰?”
極力地控制著緒,再次發問。
想不通。真的想不通。
他的雙依舊閉。就在以為他或許不會回答的時候,忽然聽他問道:“年初在你離開云落城長安的前一夜,你都做了什麼?”
姜含元起先沒有明白他這發問的意思,定定地看著他的眼睛。這雙眼眸看似平淡,眸里卻仿佛著幾分看不懂的莫測之。更知道,他既然問出了如此一句話,那便絕不可能真的會如他語氣聽起來的那般平靜。
繼續看他,突然間,猶如醍醐灌頂。
“你何意?你不會是以為我與無生有茍且之事?”
他不說話,只看著。
姜含元后背如有芒刺,面龐因那施加在上的誤解而迅速漲熱。立刻說道:“你誤會了!前夜,我確實是在他那里過夜的。但我發誓,絕沒有你以為的那種事!他是我的朋友!我承認,我當時因為即將到來的婚事,心有些。他是一個智慧的人,他的開解和誦經,能我得到心中的平靜。所以每當我去云落,我就會去找他。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什麼事都沒有!就和以前一樣,我和他說了幾句心事,他誦經給我聽,我睡了過去。醒來后,天沒亮,我便走了。這就是經過!也是這幾年,我和他的全部的關系!”
Advertisement
他依然沉默。以為已經解釋清楚了。但他那著的眼神,非但看不出半分的緩和,不知為何,竟還覺得仿佛多了幾分沉。
的心跳得厲害,“你這麼瞧我作甚?你不信嗎?你若執意誤會,以你想象加我上,斷定我是放之人,辱我便罷,我認,但他不是!他和世人不同。他通佛法,智慧高遠,他是為渡人而生的。他的心簡純,更無半分私。他居于崖山的這幾年,日夜苦修,潛心譯經。他為城民看病,解除痛苦。他絕不是你以為的那種人!”
說完,見他目爍,竟嗤笑了一聲,仿佛說的話是什麼笑話似的。
“兕兕,我的兕兕,”他了兩聲的名,用一種聽起來很是古怪的語調。
“原來你的心里,也有如此高看之人?他竟了圣人?只有他開解誦經,你才能安心?可惜了——”
姜含元一把攥住他的臂,打斷了他的嘲諷。
“我只將他視為友人!你要我如何,你才肯信?你到底將他發去了哪里?他已經病得快要死了。你相信我,你放過他吧。若真有錯,那也是我的錯。是我將他帶到云落,是我找他說話,要他誦經給我聽的。他何其無辜!”
束慎徽視線從攥住自己的手上,落到那張充滿了焦急和擔憂的臉上。
他看了片刻,慢慢地道:“兕兕,我可以信你對我說的話。但那個和尚,我告訴你,他絕不無辜。”
“倘若他真如你所言,毫無私心,他西行回來被你所救,傷好之后,他就應當接護國寺當初對他的邀約,去往我大魏國都長安。彼,才是最適合他宣法的地方。惟在長安,他的聲音才能傳播到更多更遠的地方。就連譯經,也只有在集天下人力力于一的長安,他才能得到更多的助手和便利!莫和我講他不知曉!他是西域高僧法的關門弟子。法來中土后,選擇的落腳之,便是當日的晉國國都。是在那里,法才能大量譯經,宣講法理,普度眾生。如今這個法的得意弟子,他若真如你所言,是一心向法之人,他會不知如今哪里才是他最該去的地方?他卻偏偏舍了,停在那種荒野石,一停就是數年。他不是為你,為了誰?你竟和我說,他沒有半分的私心?”
他冷笑了一聲,“也就只有你,天真無知!才會被他蒙蔽!”
“你如今是大魏的攝政王妃。我告訴你,就算他的上沒有任何別的罪由,是憑這一條,也是足夠了!名為出家,六不凈!我豈能容他再留你旁欺瞞你,玷污你的名聲?”
他頓了一頓,語氣再次轉為冷淡。
“就這樣吧,這是我能做到的對他的最好安排。他若真若你所言,高僧渡人,天下何不能渡,只能在那個云落城里?”
他竟然將無生論斷如此一個不堪之人,姜含元聽得頭皮發麻,片刻前那勉強才下去的憤怒再次涌上了心頭,再也遏制不住。
“束慎徽!”怒聲,直接喊他名字,“你完全是在以己度人!你到底將他發到哪里去了!他就快要死了!”
他卻立著,冷眼看,一言不發。
姜含元咬牙,雙手再次握拳,指節咯咯作響。
他瞥一眼,“怎的,直呼我名也就罷了,你還要和我手不?”說完,用下指了指殿閣西的方向,“我的佩劍就在那里,你去拿。”
姜含元閉了閉目,呼吸了口氣,猝然轉,朝外走去。
“站住!”
后又傳來他的喝聲。
“你去哪里?再找劉向?我告訴你,莫說劉向沒這個膽,就算有,他和你說了,你若敢去,我立刻要了那無生的命!”
伴著后的話音,一道閃電掠過窗外,跟著,雷聲在后山的山頭炸裂,震得窗欞簌簌抖,暴雨如注,疾疾打在窗面之上。
姜含元停步,立了片刻,慢慢地轉頭,看著的枕邊之人。
他的眼中再看不到半分的往昔溫。此刻這雙眼睛里,只剩下了冷漠的睥視。
姜含元知道,他說的是真的。
聽著殿閣之上那轟轟在頂的鎮萬的天雷之聲,看著面前這個手握世間生殺之權的人,心中的怒氣,慢慢地,化作了一片冰冷。
怔立良久,回了,走到他的面前,在他吃驚的注目之中,雙膝緩緩落地,朝他跪了下去,叩首到地。
叩畢,直起,依然跪著,抬起了眼。
“殿下,倘若你真不能放過,我懇求你,吩咐一聲,你的人盡量勿要苛待他,好好為他治病,留他的命。他不該就這樣死去。他只是我的友人,從前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看著站在面前的這男子的一雙眼睛,一字一句,說道。
“你生殺予奪,人命在你眼中猶如螻蟻。我不一樣。我本是個不祥之人,我的母親因我喪生,我不愿我這唯一的友人如今也因我獲罪,就這樣死去。”
“我姜含元,借著今夜天雷發誓,我不會再去找無生。我也發誓,我之余生,毋論長短,也毋論往后在何方,做過了攝政王妃,即便將來不復,寧可孤獨終老,我也絕不會做任何會令這頭銜蒙之事!”
“我是軍人,倘我有違誓言,我他日戰死沙場,首異,有如——”
從地上霍然起,走到殿閣西的案前,握住他擱于劍座上的佩劍,一把出,另手攥住了自己的長發,揮劍就從齊肩削去。
揮劍的速度,迅若窗外閃電,待束慎徽追上,那劍已到發。他來不及再從手中奪劍,劈手強行握住了劍鋒,這才堪堪止住劍勢。
的幾長發被劍刃斷,緩緩飄落。接著,有殷紅的,從握著劍的指間迅速滲出,滴落在肩上。
姜含元吃了一驚,迅速抬眼,對上了他一雙正皺著的眉眼。知他掌心已被劍刃割破了,一時顧不得別的,收目,邁步便要奔出去人送來傷藥,卻聽后一道聲音說道:“死不了!”
停步,回頭,只見他鏘的一聲,擲了劍,從上的白絹中上撕下一角,三兩下纏裹住正在流的手掌,隨即盯著,沉沉地看了許久,忽然,冷冷地道:“你知不知道,你可以為了他,向我卑微又決絕至此地步的那個人,他到底是什麼人?”
百-度-搜-醋-=溜=-兒-=文=-學,最快追,更新最快
又換域名了,原因是被攻擊了。舊地址馬上關閉,搶先請到c>l>e>w>x>c點卡目(去掉>),一定要收藏到收藏夾。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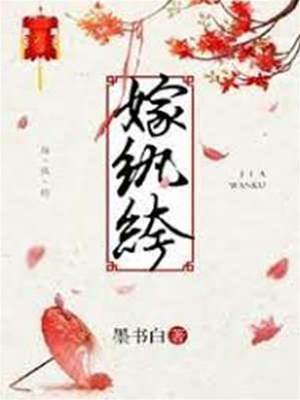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689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407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