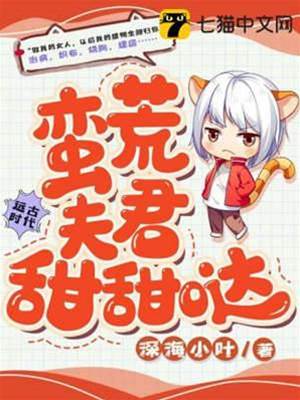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表妹慫且甜》 第48章
第48章 第四十八章
徐靜書心中砰砰砰跳得跟什麼似的, 兩耳嚶嚶嗡嗡好半晌,才漸漸鎮定下來。
看來這回是沒得躲了。也罷,有些事不明不白僵著終究不好。
「那, 那就借、借一步再說話, 」目視前方,極力維持表面鎮定,「你先把手放開。」
這願意談談的態度總算讓趙澈鬆了一口氣。他毫不猶豫地聲笑應:「借一步可以, 放開就別想了。」
他拍拍前頭的趙渭, 傾在他耳畔叮囑:「留心你弟弟妹妹,你二姐不要領你們走遠。待會兒咱們在前頭第三個街口頭就是。」
趙渭回頭,疑地看了兄長與表姐一眼。當他目不經意掃到這兩人牽在一起的手時, 忍無可忍地在心中翻了八回大白眼。
不過他素來不是多事的孩子,通常都是看破不說破的。
「好的, 大哥放心。」
說完,趙渭將旁的趙蕊牽住, 另一手搭住趙淙的肩頭,又扭頭回去,繼續專心而虔誠地繼等待他那「有青龍紋的大糖刀」了。
嘖,的破事, 哪有大糖刀有趣?
趙澈之所以隻叮囑給趙渭, 是因這幾個小的裡也就趙渭武藝還算不錯。大家一起出來的, 當趙澈不在近前時, 安全的事宜自需趙渭多擔待些。不過趙澈也不至於這麼心大, 哪會真將幾個弟弟妹妹放生在人湧的坊市裡。
他往後某淡淡使了個眼, 立時便有人不聲地靠攏過來。
糖畫攤子前那幾個沒心沒肺的傢伙見又圍了人過來,只是稍稍看了人家兩眼,約莫是確認對方並無古怪惡意,便只當也是來夜集遊樂的閒人,竟愈發起勁地與那幾人也攀談起來。
Advertisement
****
此時四衢坊的主街與幾條大巷全是人山人海,但側旁有些小巷瞧著倒是冷清。
難得下定決心要談談的徐靜書氣勢洶洶走在前,趙澈不肯鬆開的手,也不同他爭,就那麼拖著他走進了糖畫攤子對面的那條小巷。
因今夜不設宵,小巷裡雖都是關門抵戶的,但有些人家門口燈籠還亮著。
影織斑駁,在喧鬧夜之外隔出些許溫靜謐。
兩人在一戶人家的後門站定,那裡正好有堵約莫半臂寬的突出牆柱,堪堪可遮去外頭主街上的人來人往,避免被不相干的好奇目窺視打擾。
牆柱角落裡倒扣著個半人高的廢棄大竹筐,就著些微亮都能看出那竹筐周圍的積灰,顯然此平常就有人來。
是個「借一步說話」的好地方。
「來,咱們就先談談,你這些日子究竟為什麼躲我?」趙澈開門見山,目灼灼攫著的臉。
這麼幾年來,他似乎還是頭回用這樣近乎強的語氣同徐靜書說話。
事乍然超出以往經驗,這先才還有幾分氣勢的徐靜書立刻慫退了半步,直到腳後跟到那個廢棄大竹筐的邊沿,這才不得不停下步子穩住形。
「沒……」徐靜書弱弱吐出這個字後,忽然覺得不對,立刻又直了腰,虛張聲勢道,「那不躲!是理當該有的避諱!」
躲了將近十日,雖盡力摒棄心中雜念去認真讀書,可每到夜深人靜躲在被窩裡時,有些事就偏要鑽進腦子裡,不想都不行。
有時會覺得自己或許是自作多。畢竟趙澈素來是個盡責的兄長,對弟弟妹妹們都很護。他對的諸多溫以待,大約也是為兄長的習慣吧?若不是他的表妹,他會理才怪了。
Advertisement
可又總是會忍不住想起他似乎意有所指地輕啄那隻玉兔雪花糕的畫面;想起他幫顧灶火時那一臉甘之如飴的笑,溫縱容地說「我選擇束手就擒」的神;想起他置氣般大口吞下「青玉鑲」時彆扭神;想起夏夜裡他在瑤華樓對自己眨眼,將眼中而浩瀚的璀璨星辰亮給看的場景。
甚至時常想起自己加冠那夜,他笑意繾綣地「送」一捧好月華的模樣。
這些畫面在腦中替浮沉,就讓又覺得自己或許並非自作多。那樣的趙澈只有見過,這事很篤定。
每個夜裡,心煩意地輾轉反側時,眼前都會有兩個小人兒在爭吵。
一個總是板著臉兇大喊:徐靜書,你實在是想多了!
另一個又紅著臉振聲抬杠:並沒有想多!他分明就是歡喜你的呀!
這倆小人兒每夜在腦中喋喋不休,卻始終吵不出個勝負,這讓很。原本想得明明白白,隻拿他當兄長對待,可每個夜晚只要這倆小人兒在腦海中爭吵,的心就忍不住跟著左搖右擺。
彆扭搖擺這樣,本沒有自以為的拿得起、放得下,哪裡敢去見他?
無論再怎麼說服自己隻安分做他的小表妹,至在面對自己時,不得不承認,喜他,是以一個小姑娘對一個好兒郎的心。這件毋庸置疑,無法自欺。
若他不是將來可以擁有三個伴的信王世子,那個紅臉的小人兒的話或許就能讓有一點點勇氣,站在他面前紅著臉問一句「你是不是也喜歡我」。
若是,請再給我一點時間,等我變更好的人,就來牽你的手。
「將來可以擁有三個伴」這件事,當真是心中繞不過去的檻。在腦中將《皇律》、《民律》一條條細細回想個遍,依舊尋不到繞過這道檻的破解之法。
若他當真也屬意於,那他或許會因的不安與不能接而給出承諾,溫且誠摯地告訴,不會再有別人。
可這樣的承諾並不能真真使安心到義無反顧。因為記得阿蕎說過,人心易變。
將來的事,沒有真正到那一天之前,誰說了都不算。
仔細想想,世間萬事,有幾樁不是循著這個道理的?
當年在出生時,的爹娘一定也曾真心實意說過要護此生安穩。可後來父親病逝,母親改嫁,最初那些承諾就都不作數了。
而母親一開始改嫁繼父時,也曾真心實意承諾,是為了母兩能吃飽飯才做出這個抉擇,永遠都不會丟下不管。可當一對弟弟妹妹出生後,繼父養不了這麼多人了,母親便將送到姑母這裡。
相信,許多人在做出承諾的當時,都是真心的。可世事無常,大家都有可能走到不由己的境地。
自小種種經歷都在告訴,以後的事誰也不知道,到了不得已時,從前的承諾只能揭過不提,任誰再難過不甘,都無能無力。
親之間的承諾尚且有不得已時,何況男之?
只能頹喪地夾起兔子尾,躲趙澈遠遠的,努力在心中挖出一個很深很深的,藏起所有悸心事。
天地很大,此生漫長,除了風花雪月,還有許多事需要費盡心力去爭取。不能太過耽溺於愫,應該要埋頭往前,向著更寬更遠的前路不停步。
道理都很明白的,可只要他一出現在目之所及的地方,的目就總是不控地往他跑去。
他的每個眼神、每個作、每句話,不管有心或無意,都在招惹、打擾,都在不餘力地撥著極力想要掩埋起來的。
這時才明白,原來真真喜歡一個人時,即便堵上自己的,捂住自己的耳朵,甚至遮住眼睛,全是徒勞。
喜歡了就是喜歡了,不管怎麼努力告訴自己要清醒理智,最終都是藏不住、收不回的。
因為腦子會想,心會跳。
這種懸在半空起起伏伏的覺,真是既甜且惱,又酸楚,又歡悅。還磨人!
眼見他此刻明擺著要將窗戶紙捅破的架勢,徐靜書索也豁出去了。
「既過了年禮,那我、我也是大人了!男、男有別,你、你是我表哥,又不是我表姐,我當然、當然就不能再、再像小時候那樣沒遮沒攔往你跟前湊的,那、那不對!阿蕎也、也不會沒事就、就往含院跑,小五兒還那麼小都不會,我、我怎麼可以不像話!當然該躲!」
趙澈盯著看半晌,忽地笑了:「你也是夠不容易的,磕磕還能出這麼一大段廢話。」
「怎麼就是廢話了?我在跟你講道理!」他的話讓徐靜書惱得想咬人。
「你那也道理?」趙澈笑眼裡閃過一危險的芒,「你說這麼多,意思就是你在我這兒,同阿蕎是一樣的?同小五兒是一樣的?嗯?」
「那當然是……」
「徐靜書,想清楚再說話啊。」趙澈哼笑一聲,「友好」地提醒。
徐靜書被他完全不同以往的氣勢制,慌張低下頭,訕訕清了清嗓子,弱聲弱氣:「們是你的妹妹,我是你的表妹,那當然是……差不太多的。」
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又覺自己方才「借一步說話」的提議很蠢。有點想跑路了。
哪知腳尖才微微一,就被趙澈看穿了企圖。他長臂一展抵在牆上,堵住的去路。
「我告訴你,差得可多了。」
****
趙澈瞪著眼前低垂的小腦袋,憋了將近十日的惱火、疑與委屈齊齊湧上心頭。
從那天在含院古古怪怪藏起眼裡的小星星後,這傢伙就乾脆俐落地躲起來了。
將近十日,他不管白日裡再忙再累,夜後都沒法輕易合眼眠,為這事簡直都要抓心撓肝、摳破牆皮了,卻還是想不個中緣由。
偏躲得徹底,本不給他任何發問的機會,這會兒居然還「兔膽包天」,大言不慚地說和趙蕎、趙蕊對他來說是一樣的?!
真是再好脾氣也要被得「惡向膽邊生」了。
「能一樣嗎?!我時不時拎著那倆妹妹一訓就是半個時辰起,幾時這樣待過你了?!」
「我會允許那倆妹妹從我這裡虎口奪食?!我會對那倆妹妹事事毫無瞞,生怕們事後得知要難過失落而鬧彆扭不理人嗎?!」
「我會在那倆妹妹面前不就面紅耳熱、心跳得像韁瘋馬、彆扭稚到自己事後想想都覺嫌棄的地步嗎?!」
趙澈長這麼大,還真是頭一回這樣氣急敗壞地向人……深刻地剖析自我。
總之,結論就是,一樣個圈圈叉叉啊!分明打從最開始,他對「表妹」與「妹妹們」,就非常、非常地不一樣!
趙澈強行按捺在耳邊咆哮的衝,從牙中出冷森森的笑音:「旁的不說,單隻『你親我』這件事,若是倆敢這麼做,我就敢親手打斷倆的小狗,再將們種到土裡生發芽!」
趙澈看似溫和,待人卻從來都有清楚界限與分寸。對幾個妹妹,他何曾真的縱容退讓過?
徐靜書的小兔兒至今安好,甚至還一直以為自己功地瞞天過海,這足以證明,他縱,從來就沒什麼底線。
只有對心儀的姑娘,才會接二連三地忍氣吞聲啊!
哪裡一樣?!
「什麼、親?」徐靜書猛地抬頭,烏潤明眸裡盛滿蓋彌彰的驚恐,「沒、沒有的事!你、你是我表哥,是、是兄長,是家、家人,我、我怎麼、怎麼可能做這、這麼荒唐的事呢?哈。哈。哈。」
很好,親了還死不認帳,每次提到這件事,就只會「哈、哈、哈」。
「春日裡王府櫻桃宴,在半山亭裡,敢說不是你親的我?」趙澈微微瞇起了眼,笑得有點兇。
「不是我!我沒親!你瞎說!」徐靜書臉紅得像被刷了層新漆,梗著脖子跳腳否認。
「呵。你還倒打一耙,變我瞎說了?」
趙澈怒極反笑,倏地抬手住的下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那負隅頑抗的甜上一啄。
他看著面前「待若木兔」的紅臉小姑娘,良久後,才嗓音輕啞地開口淺笑:「表妹不必狡辯了。當初的口,與此刻分明是一樣的。」
主街上不知什麼人點了煙花。明亮火球接連呼嘯破空,在穹頂之下炸出漫天絢爛花海。
徐靜書懵懵地著面前的人好半晌,像被掀了底牌突然輸個的僥倖賭徒,面漸漸蒼白。
的頭慢慢垂下去,雙手捂臉,形微晃,絕而無助地不住慄。
趙澈慌了,忙不迭趨近,手足無措好一會兒,才展臂將輕輕環住。
綿綿踹了他一腳,接著又騰出一手,揮拳砸在他肩頭。
他不如山,一一生。
最後,將淚漣漣的臉在他的肩頭,出雙手環住了他的脖頸,如即將溺斃之人在絕中攀住了水面唯一的浮木。
煙花連綿不絕炸響的巨大聲浪混著人們雀躍的歡呼,排山倒海般洶湧而來,在這個霎時蓋過了周遭所有靜。
可對趙澈來說,徐靜書那哀傷噎的淺細嗓,才是天地間唯一清晰的聲音。
「你怎麼可以這樣?為什麼非要揭穿?我不要做三個人裡的一個啊……」
所以,「三個人」,就是古古怪怪藏起眼裡小星星的緣故?趙澈輕輕拍著的後背,心疼又狼狽地在耳旁虛心求教——
「請問,究竟是哪『三個人』?」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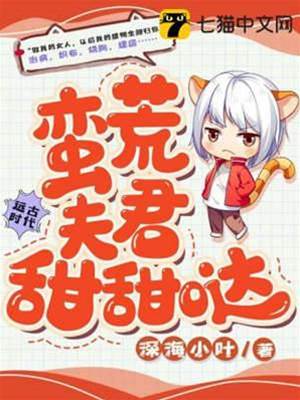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320 -
完結154 章

二小姐進京了
沐羨之穿成了沈相爺家多病,從小養在山上道觀里的二小姐。彼時沈相夫妻剛去世,面對龐大的產業,親戚們虎視眈眈。性格軟弱的長姐被欺負得臥病在床,半死不活。要面子好強的三妹被退了婚…
52.8萬字8 23817 -
完結571 章

滿門炮灰讀我心后,全家造反了
喬嬌嬌上輩子功德太滿,老閻王許她帶著記憶投胎,還附加一個功德商城金手指。喬嬌嬌喜滋滋準備迎接新的人生,結果發現她不是投胎而是穿書了!穿成了古早言情里三歲早夭,戲份少到只有一句話的路人甲。而她全家滿門忠臣皆是炮灰,全部不得好死!喬家全家:“.......”喬家全家:“什麼!這不能忍,誰也不能動他們的嬌嬌!圣上任由次子把持朝綱,殘害忠良,那他們就輔佐仁德太子,反了!”最后,喬嬌嬌看著爹娘恩愛,看著大哥 ...
105.3萬字8.18 17771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5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