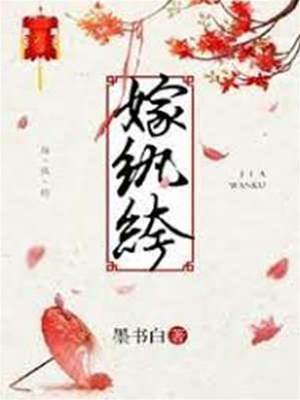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替身竟是本王自己(雙替身)》 第 27 章 二十七
回常安坊的路上,天空中又飄起了雪片。
到得山池院時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桓煊挑起車帷往外,見到門口那兩盞風燈,一時竟生出旅人歸家之。
說來也奇怪,無論王府還是蓬萊宮,都從未讓他生出過這種覺,他想了想,大抵是因為這里有個無依無靠,全心依賴他的人吧。
馬車駛到清涵院門前停下,桓煊降車,忽然聞到遠飄來淡淡的食香氣,混雜在風雪中撲面而來,冷風也帶了塵世的煙火氣。
他頓住腳步,朝那沒于楓林里的小院子了一眼,那星星點點的燈也似比別暖一些。
“又在折騰什麼?”桓煊問迎上前來的高嬤嬤,狀似不經意。
高嬤嬤答道:“昨日王府送了南邊來的鵪鶉,鹿娘子在烤鵪鶉,又弄了些古樓子。”
頓了頓:“殿下從城外回來,還未用膳吧?老奴人去傳膳……”
桓煊猶豫了一下道:“他們送到棠梨院去,我去那里用膳。”
高嬤嬤一愣,隨即明白些什麼,覷著桓煊臉道:“那些是鄉野鄙人的烹調之法,恐怕不合殿下脾胃。”
桓煊并未反駁,“嗯”了一聲,卻徑直沿著楓林中的小徑向那暖融融的小院走去。
走到門口,便已聽見庭中的歡聲笑語,那獵戶略帶沙啞的聲音特別引人注意。
他推門進去,只見那獵戶和幾個青婢坐在廊下說笑,腳下燃著炭盆,面前擺著風爐、鐵架,竹簽串著的鵪鶉滋滋冒油,旁邊一個鐵爐子上烘著古樓子,一旁小竹案上擺著酒壺酒杯和料碗。
他風塵仆仆在外奔波一日,的小日子倒是過得自在,他這麼想著,心里莫名涌出一酸意,角的笑容淡了去,看起來又是那副高高在上、難以取悅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幾人見齊王殿下降臨,俱都起行禮,春條和小桐等一干婢連忙退到一旁。
桓煊淡淡地看了隨隨一眼,微微頷首便算打了招呼。
這時,高邁和侍膳的侍也提著食盒到了。
桓煊便對幾個婢道:“你們退下吧。”
小青們都忍不住流出失,他們眼看著就要吃上鹿娘子的烤鵪鶉和古樓子了,誰想齊王殿下突然駕到,快到的東西吃不,別提多難了。
尤其是鹿娘子做的古樓子,那可真是一絕,連西市上白家胡餅鋪的都比不上。
但主人有令,他們也只能眼地看著到的味飛了。
小桐年紀最小,更藏不住事,幾乎要哭出來了。
隨隨看在眼里,對桓煊道:“殿下,這些鵪鶉烤得老了,餅也有些焦了,民重新烤過吧?”
桓煊知道是替那些下人著想,心下甚覺無謂,但因著心好,并未反對,點點頭:“這些便賞他們吧。”
婢們個個面驚喜,上前謝恩。
隨隨沖他們眼。
桓煊看在眼里,只是一哂。
待婢們退至遠,桓煊抖了抖狐裘上的風雪,解下遞給隨隨放在一旁,掃了一眼鐵架上的鵪鶉,明知故問道:“這是何?”
隨隨答道:“回稟殿下,是南邊送來的鵪鶉。”
頓了頓,又指那鐵爐子上烘得焦黃香脆,撒了胡麻的面餅:“這是民做的古樓子。”
桓煊“嗯”了一聲,走到方才坐的小榻邊,不見外地坐了下來,了眼皮:“什麼餡的?”
“羊餡。”隨隨答。
桓煊眉頭一皺,挑了挑下頜:“孤不吃羊。”
他用眼梢瞟了一眼,卻見那獵戶只是眨著一雙水盈盈的眼睛,目中微有困,全然不明白他的暗示。
Advertisement
他只能指了指鐵架子:“你的鵪鶉快烤焦了。”
隨隨這時方才明白過來他是想吃,不啞然失笑,想吃便說想吃,還要人猜他心思,這人還真別扭。
看著火候差不多,拿起只烤鵪鶉,往上灑了許鹽花:“殿下要嘗嘗麼?”
桓煊這才矜持地點點頭:“好。”一副紆尊降貴的模樣。
隨隨知他子如此,并不放在心上,將鵪鶉放在銀盤中,連著竹簽子一起呈上前去:“殿下請。”
桓煊拿起來看了看:“未加調料?”
隨隨道:“鵪鶉是活宰的,新鮮的雀兒只撒鹽就很鮮了,加了調料反而蓋住味道。”
說完這話兩人都是微微一怔,依稀曾在哪里說過、聽過,但一時都想不起來。
就在這時,鐵爐上傳來焦香味,隨隨低低地驚呼一聲,連忙起跑過去,將古樓子取下來放在盤中,用小胡刀切數片,刀鋒劃開香脆面皮,空氣中充斥著餡的鮮咸香味。
桓煊不喜食羊,嫌它腥膻,平日王府的庖人做古樓子,用的都是豚或做餡料。可這獵戶治的羊卻聞不出腥膻,他不由好奇道:“這羊里加了什麼?”
隨隨目微微一:“是胡人治羊的法子。”
桓煊點點頭,家鄉那一帶胡漢雜,從胡人那里學到些奇怪的法子也屬正常。
他沒再多問,垂下眼皮,抿了一口酒。
他的睫很長,但不翹,微微垂眼的時候幾乎將眸全都遮住,讓人猜不到他心思。
隨隨問他道:“殿下可要嘗嘗看?”
桓煊本來不品嘗,他的憎一向很分明,開始討厭一樣東西,便討厭到底,即便是沒有膻味的羊,他也興致缺缺。
他們兄弟三個,他和長兄隨了母親,不了這些腥膻之,他長兄當年去西北兩年,回來說起還苦不堪言。
但他不經意間抬眼,對上子的眼睛,琥珀的眸子在燈火映照下閃著奇異的,滿是希冀,似乎手里捧著的不是古樓子,而是切下的一片心。
桓煊便是鐵石心腸也不住這樣的眼神,何況還是與自己有過之親的子。
他接過來咬了一小口,餡熬得爛,脂油在齒間化開,非但沒有一般羊的腥膻,還有一不知什麼香料的清芬,食之齒頰留香,他眼中不由閃過一抹訝異。
他只是不想看眼里的芒暗下去,本打算咬一口淺嘗輒止,卻不知不覺又咬了一口,一口接一口,將整塊都吃了下去。
隨隨彎起眉眼,一臉欣悅:“殿下可喜歡?”
桓煊才說自己不喜歡羊,臉上有些掛不住,淡淡地“嗯”了一聲:“不錯。”
頓了頓又道:“上回……”
他想起上回送來的湯和醉松蕈,卻忽然想起自己非但不領,還將的吃食倒了,便不再說下去。
高邁知道主人心思,便接過話頭:“鹿娘子真是蘭心蕙質,連烹調都這般出。對了……”
他頓了頓:“上回那醉蕈子不常見,是怎麼做的?”
桓煊冷冷地乜了他一眼,高邁卻仍舊笑嘻嘻地著隨隨。
隨隨道:“那是松蕈,后園山坡上松林里摘的。”
桓煊不發話,高邁繼續道:“殿下上回倒是用得好,來年秋日鹿娘子再做些可好?”
隨隨眼神微微閃,笑道:“這種蕈子不常能找到,這個秋天氣候暖和又多雨,不知來年還長不長。”
高邁道:“來年不長還有下一年,鹿娘子在殿下邊,總有機會的。”
隨隨微垂眼睫,淺淺地一笑,卻沒有回答。
來年秋天多半已離開,若非必要,謊話能說一句便說一句吧。
桓煊面無表地瞟了一眼,見垂眸,以為是赧,角微不可察地了。
用了一只烤鵪鶉和一塊古樓子,桓煊便有些飽了,他一夜未眠,胃口不比平日,清涵院廚房送來的肴饌都便宜了隨隨。
桓煊用帕子揩凈了手,讓侍煮了茗茶,一邊飲茶一邊看隨隨用膳,見吃得香,忍不住重新拿起玉箸,吃了兩塊金銀夾花平截,又用了一小碗棗粥。
用罷晚膳,夜已微闌,風雪又大起來。
桓煊道:“上回給你的棋譜記了?”
隨隨點點頭:“記住了。”本就善弈,那譜又簡單,打一回便記住了,不費什麼事。
桓煊便人收了茶床,擺好棋枰。
“看看你這幾日有沒有進益,”桓煊道,“這回授你八子。”
一邊說,一邊將八顆黑子擺在星位上。
兩人都是靜思寡言之人,一時只聞棋子敲在棋枰上發出的清脆聲響。
至中盤,桓煊有些詫異,這子的棋竟然出乎意料的好。
畢竟學棋日短,局部的攻守有所欠缺,但難得有大局觀,棋路雖生,但每落一子,總有呼應。背的譜,用起來也不拘泥,倒是時常走出意想不到的一著。
他們上回對弈是數日前,同樣授九子,他已能覺到的棋力有明顯提升。
他起眼皮,看了看隨隨,子拈子沉的模樣給添了幾分幽靜嫻雅。
“你的棋很不錯。”他一向吝于夸贊,能從他口中聽到一個“不錯”,實非易事。
隨隨抬頭淺淺一笑:“多謝殿下夸獎。”
棋難以言喻,但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阮月微當初狠下苦功,記下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棋譜,但與他的差距越拉越遠,便是天生不擅布局,總盯著一隅,且拘泥于棋譜,因此下了許多苦功,棋藝仍然難稱頂尖。
他的母親倒是擅弈,長兄還在世時,他母親尚未對他避而不見,他去宮中請安,母子偶爾也會對弈上一局。他們母子相,分稀薄,相對而坐時常沒話說,手談倒是避免了尷尬。這也是他母親難得夸贊他的時候。
“兄弟三人中,棋藝倒是你最好,”他母親曾道,“你長兄恬淡,不喜征伐,不在意勝負,棋風也溫和緩,你二兄失之躁進,攻殺兇狠,卻了大局觀,倒是你,布局殺伐兩相宜,厚勢而銳意,假以時日,恐怕我也不是你敵手。”
“觀棋如觀人。”他母親道。
而自己的棋風剛強執拗,一如的為人。
桓煊回過神來,了眉心:“勝負已分,這局棋便到此為止吧。”
隨隨依言收起棋子。
桓煊靜靜注視著,這子屢次讓他刮目相看,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你的騎不錯,從棋路中也可看出,有些排兵布陣的天分,”他忽然道,“若是在軍中,倒是個可造之才。”
隨隨心頭一凜,難道他察覺出什麼了?
自問已將棋力藏得很好,即便是桓煊這樣的高手,當也看不出善弈。
穩了穩心神,微赧:“殿下說笑,子怎麼能從軍。”
桓煊卻道:“并非說笑,大雍是有一支軍的。”
不過并不隸屬于朝廷,而是在河朔,這支軍隊是蕭泠在接掌三鎮兵權之后用了數年時間建立的,軍中子多是戰中失去父兄、丈夫的孤貧之人。
當時蕭泠組建這支軍隊,無疑是驚世駭俗之舉,便是在河朔軍中也多有反對的聲音,但在后來的戰事中,這支軍驍勇善戰,完全不遜于男子,其堅韌不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反對的聲音便漸漸銷聲匿跡了。
在戰死沙場前,的軍隊和幕府中不乏子將領和幕僚,親衛中也多有子。
桓煊瞥了眼對面的子,想起今日馬上的風姿,不知怎的又想起桓明珪那廝的“明珠蒙塵”。
他將這念頭從腦海中掃出去,了額角,想這些無謂的事做什麼,左右是不可能再去別了。
隨隨聽他提到軍,眼皮便是一跳,靜待了片刻,他卻沒有繼續說下去的意思,又不似在試探,按捺下心中不安,把棋笥收好。
桓煊道:“這棋枰棋笥便送與你吧。”
隨隨微怔,不說這些墨玉和羊脂白玉的棋子,便是這張紫檀嵌螺鈿的棋枰,也是用之,他不是奢靡無度的人,怎麼隨隨便便就拿來賞人,不過橫豎也不可能將這些東西帶走,便坦然地收了下來。
桓煊侍收放好,便舉步去了臥房。
外頭風大雪,他自然就留在了棠梨院,兩人洗漱沐浴更,上床就寢。
桓煊沒什麼睡意,卻難得心緒平靜,許是一夜沒睡又鞍馬勞頓了一天,此時他沒什麼別的心思,只是從背后摟著,聽著悠長的呼吸聲起起伏伏。
宮中的事,長兄的事,小時候的事,走馬燈似地在他腦海中閃過,不知過了多久,終于安心地闔上眼睛。
……
東宮正院書齋前,斜風將雪片吹落到廊廡上,漸漸積起厚厚一層。
阮月微穿著繡鞋踩在雪上,意侵羅,但毫也顧不上。
太子自那日梅花宴起便以政務繁忙為由,時常宿在蓬萊宮,即便偶爾回東宮,也多在前院歇宿。
雖然他很召別人侍寢,但阮月微心中依舊忐忑。
今日聽說他一回東宮便進了書房,不敢打擾,按兵不半日,到人定時分也不見太子那邊的消息,這才終于按捺不住,帶著親手熬的參湯來了前院。
太子代皇帝理政,前院書房有很多朝奏文書,本來阮月微是不該踏足的,但侍從們都知道太子對太子妃如珍寶,平日隨意出,沒人敢攔著。
侍打起簾櫳,阮月微從疏竹手里接過食盒和一卷書軸,一個人走進房中,讓婢等在廊下。
太子見了,并不如往日那般溫脈脈,只是抬起眼道:“你怎麼來了?”
阮月微有些委屈,不過面上不顯,溫道:“妾聽聞殿下政事繁忙,也不知有沒有好好用晚膳,所以熬了些參湯送來。”
太子道:“有心了。”
頓了頓又道:“讓下人送來便是,何必冒雪前來。”
阮月微怔了怔道:“妾也想看看殿下。”
太子面稍霽,皺的眉頭舒展了些,站起走到跟前,捧起雙手:“你看,手這樣涼,你子骨弱,寒怎麼辦?”
阮月微見他又恢復了往常的態度,心下稍安,又道:“上回梅花宴上,賓客們作了許多詩,妾這幾日閑來無事,人將詩抄寫卷,又加了批注,請殿下過目……”
太子雅好章句,平日總是用詩文投石問路,一向屢試不爽。
然而這回太子卻興致寥寥,只是道:“先放著吧,孤眼下還有別的事。”
阮月微掃了一眼書案,上面干干凈凈,并無奏疏,方才進屋時,太子也只是坐著無所事事罷了。
心下越發委屈,咬了咬,輕聲道:“殿下,妾可是做錯了什麼事?”
太子安地握了握的手:“你別多想,前些時日朝中事多,讓你冷落了。”
阮月微覷了一眼太子,見他神疲憊,小心翼翼道:“可是朝中出了什麼事?”
太子道:“無事,前朝的事與你不相干,你安安心心的,若是寂寞便召閨中的姊妹、朋友過來陪你消遣,孤有空便來陪你。”
阮月微道:“是妾僭越了,妾只是想替殿下分憂。”
由太后教養長大,一開始便是沖著太子妃之位去的,習詩書,涉獵經史,自問眼界學問不遜于進士翰林。
太子仍道:“你子骨不好,不能多思慮,這些事便別費心了。”
阮月微只得道:“參湯快放涼了。”
伺候太子飲了參湯,阮月微又道:“妾替殿下研墨吧。”
太子搖搖頭道:“不必了,時候不早,你早些回去就寢吧,這些事下人做便是。”
阮月微無可奈何,只得告退。
太子著的背影,眼中的溫漸漸淡去,仿佛兩口冰冷的古井。
……
幾場雪一下,轉眼便是歲除,桓煊要宮,一大早便換上錦袍,披著狐裘出了門。
作者有話要說:下一更在18日中午12點
存稿沒了,以后更新時間還是每天中午12點,有多發多
謝在2021031013:27:262021031123:50:56期間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營養的小天使哦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舟18個;nullland2個;丁丁、sweetie、風雪夜歸人1個;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棋罷指猶涼、經濟小吃10瓶;板燒堡6瓶;小咪子5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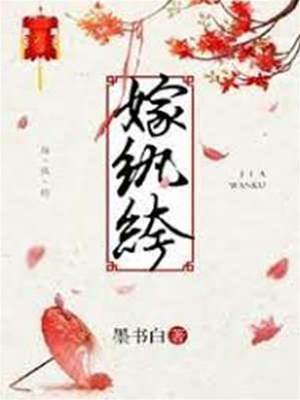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389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398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0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