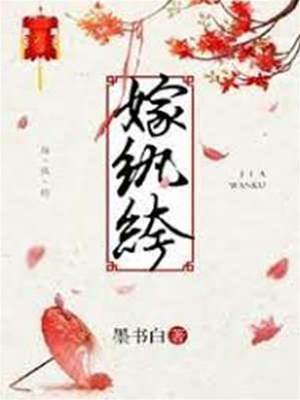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逐鸞》 第117章 番外2:插翅難飛(1)
除夕宮宴,闔宮結綵。
登基三年的皇帝在甘殿設宴宴請文武百,宴會還未開始,殿已有過半賓客,並還在有人不斷進殿。
「靈武公主到——」
隨著一聲長長的傳唱,著紅的萬俟丹蓼昂頭走殿中。的三個哥哥雖說也有爵,但排場怎麼也比不過為公主的妹妹。
萬俟家主如今已為武國公,此番他蒙獲聖恩,千里迢迢從鳴月塔趕來覲見皇帝,雖走在自己兒後,可卻一臉得意地著周遭艷羨的目。
萬俟三兄弟看著父親的模樣,不得不在心中嘆一聲,姜還是老的辣。
早知今日,就是他們也聲義父,也有何不可?
武國公落座之後,立馬就有不想要攀附關係的員上前寒暄。武國公常年鎮守鳴月塔,鮮京際群臣,他對這新鮮的吹捧,看上去也用不已。
這萬俟一家,頗皇帝重用,同皇后的弟弟荔象升一般,都是武將一派里舉足輕重的人。
正當眾人圍繞在靈武公主和萬俟氏父子邊熱聊之時,殿外的太監再次傳唱。
「咸寧公主,駙馬到——」
「太傅到——」
隨著魯涵和魯萱的先後殿,殿多人神一振。
這朝廷上的香餑餑,一個接一個的,讓他們都不知道先去拍誰的馬屁好了。
自皇帝登基以來,皇上諒魯涵年歲已大,將其召回京都,封為三師之一。雖說這太傅一職並無實權,但到底是個正一品的職,走哪兒都得人仰。
不過說來也怪,這魯涵似乎也沒甚大功,帝后卻格外敬重,連帶著這咸寧公主,雖然弱,不像是阿諛諂之人,但宮中也什麼好事,皇后也第一個想到咸寧。
去年,皇后親自為咸寧公主指婚,駙馬乃是皇后的堂兄荔鳴珂。
Advertisement
荔鳴珂為人正直,儀錶堂堂,還一直潔自好,房中未有眷。再加上還是國戚。這門親事,不知艷羨了多京都貴。
兩人婚後,琴瑟和鳴。
此次赴宴也是,荔鳴珂小心翼翼地攙扶著懷有七月孕的妻子,鞍前馬後地為服務。
有員想要上前套近乎,荔鳴珂也是短短數語便終結了聊天,目和注意力始終在妻子上。
過了不久,最後一位昌平公主到了。
苑隨著父親安國公的腳步走大殿,當了三年公主,還是有些力不從心。
從政治意義的角度來說,這位昌平公主比起前兩位公主,明顯遜了許多。眾人的焦點大多還是放在的親生父親安國公上。
為前朝重臣,帶著四十萬將士接彼時還是太子監國的皇帝的招安——可是為當今皇上的資歷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位安國公的呼籲下,朝廷招倖存的前朝皇族,封爵授,令他們可以恢復真名,安居樂業。
從前層出不窮的復國運,在此之後便漸漸平息了。
新帝登基三年,百姓各居其位,百各司其職,大燕已有國泰民安之相。
如今國家缺的便是一個好消息了,可礙於皇帝那喜怒無常,捉不的格,沒人敢去這霉頭,所有人都盯著宮裏,卻不敢言語。
「帝後到——」
眾人神一凜,紛紛放下手中的事,向著門外叩拜行禮。
幾位公主也接連跪下行禮。
從傾瀉而的月中,帝后二人並肩走出。甘殿眾人跪拜行禮,高聲問安。
謝蘭胥在寬闊的龍椅上坐下,穿鈿釵襢的荔知一如既往,與他同坐一椅。殿諸人已經習以為常,私底下甚至有人稱為「二聖」。
眼前這位皇后,在新帝微末之時便不離不棄,一路與之出謀劃策,生死與共。可謂是有勇有謀,有有義。封后后,也是民如子,尤其注重天下學子的教育,封后第一年,皇帝便在皇后的勸諫下,建立了國第一所子學。
Advertisement
子學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便是皇親國戚,不是皇帝所收義,便是皇后的親妹妹。
即便是為了攀龍附,也有好些富貴人家將自己的兒送學。
如此一來,京中子讀書蔚然風,爭相以考學為榮。
今年初,皇帝在皇后的諫言下,對子放開科舉限制,現在子不僅可以在後宮為,也可在前朝任職。燕國子,無不以當今皇後為明星。
同皇后的德行與遠見相比,出上的瑕疵便沒有多人關注了。
「眾卿請起。」皇帝淡淡道。
朦朧的月混在亮如白晝的燈火中,為皇帝的面容蒙上一層淺淡的白影。
皎潔,蒼白,不可捉。
百習慣了皇帝喜怒難辨的模樣,不敢有毫造次,規規矩矩地落座。
「今日是除夕宮宴,大家盡興宴飲便可。」皇后笑道。
皇后安定而平穩的聲音讓大家鬆了口氣,殿氣氛這才融洽起來。
百爭相向龍椅上的帝后二人敬酒祝賀。
酒過三巡,皇帝已出厭倦神。
謝蘭胥握住荔知的手。
「還要加班至多久?」他哀怨地看著。
荔知笑了笑,反握了握他的手,說:「想走了?那便夾一筷魚喂我。」
夾一筷魚罷了,謝蘭胥想也不想照辦,不想魚剛至荔知邊,就險些嘔吐出來。
荔知已經轉過去,謝蘭胥還怔在原地,殿的百已經比他更快地意識到了什麼,拿著酒盞的放下了酒盞,正在說話的也閉上了,眾人不約而同屏息凝神,閉上了一致豎耳傾聽——
「皇上,還不太醫?」荔知用一張綉有曇花的絹帕捂著,提醒道。
謝蘭胥這才回過神來:「太醫呢?!」
傳召太醫的時候,謝蘭胥不可思議地看著,臉上倦一掃而空,他似乎想到了什麼,但又不敢確認,直至太醫院院使匆匆趕來,把脈后一臉喜地跪地行禮:
「恭喜皇上,賀喜皇上,皇後娘娘已有兩月孕——」
一石驚起千層浪。
謝蘭胥猛然起,而殿眾人旋即跟著太醫一起跪下祝賀。
「兩月?你……你為何現在才告訴我?」
謝蘭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彎著腰把手放在荔知肩上,手足無措地看著。
此時的他倒不像個喜怒不定的帝王,只是個最符合年紀的愣頭青。
「月份淺,容易弄錯,我也是昨日才確定的。」荔知笑道。
謝蘭胥抿了抿,似有千言萬語一起堵在了嚨里,反倒讓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半晌后,他忽然彎腰,一把抱起了荔知,大步走出了甘殿。
留在殿中的員面面相覷,但很快,他們便相互恭祝了起來。這皇後有孕,對社稷後繼無人的憂慮便能放上一放了,至於忽然離席的皇帝和皇后——哎,大家都習慣了皇帝旁若無人的偏,也無所謂了。
謝蘭胥抱著荔知上了龍輦,又將荔知一路抱至未央宮中。
荔知哭笑不得:「現在還不放我下來?」
謝蘭胥頗有主見,堅持走至大床邊,才將小心翼翼放下。
「我聽人說,越是月份淺的時候,越要小心。」謝蘭胥說,目定定地停在還看不出變化的肚子上。
他像是還在夢中,半信半疑地了平坦的肚子:
「這裏面……已經有我們的孩子了嗎?」
「是啊,」荔知笑道,「阿鯉從現在起,便可為我們的孩子想一個名字了。」
「也不知是男是……如何取名?」謝蘭胥遲疑道。
「那便各取一個。」荔知說。
謝蘭胥興不已,立即冥思苦想起來。
但高興了不過片刻,他又變得憂心忡忡,蹲在床邊,將攔腰抱住。
他沉下臉來,帶著對自己的遷怒:「只恨我不能替你苦。」
荔知他的頭頂,笑道:
「你有這份心,便讓我心滿意足。」
謝蘭胥抱了一會,又問喝不喝水,困不睏倦,荔知都搖了搖頭。
「我想去曇園看看,說不定,能上曇花開放。」
荔知剛懷有孕,一方面謝蘭胥對有求必應,另一方面則生怕磕著著,因此去往曇園的一路,謝蘭胥都格外小心,恨不得將荔知放在口裏含著過去。
到了曇園,謝蘭胥扶著荔知走下龍輦。
曇園去年才建,園中只有曇花一種,種植曇花的暖房四季如夏,以保證曇花常年開放。
或是曇花也知除夕之喜,荔知走曇園,迎接的便是妖冶而聖潔的曇花。
縷縷的白花瓣,簇擁著花蕊,盛放著只在夜晚展的香氣。一株株曇花層層疊疊,遠看像是皚皚雪景,其中最大的那株王曇,在百上千曇花之中,就像是佇立在鳴月塔大地上的仙乃月神山,巍然醒目。
「世人雖牡丹,我卻獨曇花。」荔知笑道,「因為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它從始至終都堅持在自己的時間盛開。」
謝蘭胥對花並無研究,但他一樣偏曇花,因為偏之人曇,他也便跟著曇。
皇宮之中,紫薇樹盡數拔除,取而代之的是堅貞的松竹和只在剎那之間盛放的曇花。
「能得你喜的,便是最好的。」謝蘭胥看著。
忽然,暖房外響起了高善的聲音。
「啟稟皇上,中郎將荔鳴珂求見。」
謝蘭胥皺了皺眉,剛想讓荔鳴珂進來,荔知說道:
「中郎將想必有事和皇上相商,此地狹小,不便議事。皇上還是移步接見吧。」
謝蘭胥挑了挑眉:「你不與我同去?」
「曇花開放,轉瞬即逝。」荔知說,「更何況,我已知道他所求何事了。皇上一人去足以。」
謝蘭胥這才推門走出暖房。
門外侍立著許多宮人,謝蘭胥不放心獨自一人在暖房觀賞曇花的荔知,停下腳步對領頭道:
「你在門外小心謹慎,隨時聽候皇后吩咐。」
謹慎應是。
謝蘭胥這才在高善的陪同下,走到不遠的荔鳴珂面前。
荔鳴珂行禮問安,不太習慣與皇帝單獨相。他略微拘謹地道明了來意。
「你想將次子,過繼到魯涵膝下?」謝蘭胥有些訝異。
「此事一開始是公主的想法,後來得到皇后的肯定,公主才將此事告知下,請求下日後若有次子,將其過繼給魯家承嗣。」荔鳴珂板板正正地說道,「下覺得無甚不可,但因為公主份高貴,所以此事還需皇上同意才行。」
謝蘭胥聽完只覺浪費了和荔知獨的時間。
「你們二人的孩子,不必和朕代。既然皇後有意如此,那便如此。」謝蘭胥說。
荔鳴珂鬆了口氣,再次行了一禮。
謝蘭胥不去管他,轉再次走向暖房。
推門而后,暖風迎面而來。
百丈大的暖房中,曇花如雪山堆砌。幽香四溢在寂靜的空氣之中。
一張絹帕落在地上。
暖房空無一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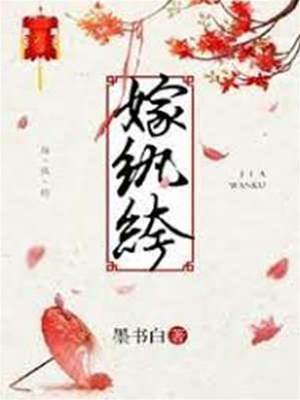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9516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606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1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