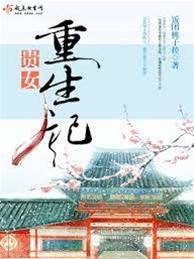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昭昭春日》 [昭昭春日] - 第44節
他停了停,看向眼前擔憂地著他的,低聲道:“抱歉。”
李羨魚輕輕一愣。
輕垂下眼,細細想了想臨淵方才說過的話。
良久,輕輕啟,像是落定了決心。“若是一定要去,那,你帶我一起去吧。”
臨淵握著麵的長指收,驀地抬眼看向。
李羨魚也抬起眼來,眸清澈地與他對視。
“你方才不是說,這是一個權貴樂的地方嗎?”著他,順著這個道理,得出個答案來:“我是大玥的公主,應當也算是權貴吧。”
李羨魚著他,輕聲重複:“若是一定要去,那你便帶我一同去吧。
說得這般認真,且從他的話中找到了自己的道理。以致於臨淵一時竟不知如何作答,隻握住手中的紅寶石麵,薄抿,深看向。
秋日金的日照進殿來。
李羨魚坐在長案另一側,雪烏發,眼裏流轉著星河一般的。
秀眉輕展,對他嫣然而笑,天真又誠摯。
“我會努力保護好你。”
作者有話說:
今天還算是準時吧~
記在小本本上:今天小甜餅準時更新啦。
第38章
說得這樣認真,令臨淵握著紅寶石麵的長指驟然收。
他立時拒絕:“不行。
他道:“公主絕不能去。”
李羨魚沒想到臨淵會拒絕得這般果斷,輕愣了愣,又問他:“為什麽呀?”
問:“難道公主不算是權貴嗎?”
自然是算。
臨淵皺眉,不知該如何與解釋。
他看了手中的紅寶石麵一眼,尋出個理由。
“紅寶石麵隻有一張。”
李羨魚也看向那張紅寶石麵,略想了想,重新站起來:“你等我一會。”
起走到鏡臺前,將妝奩打開,從中尋出一些黃金與紅寶石的首飾來。
Advertisement
將這些首飾遞向臨淵,杏眸微彎:“這些首飾都是我不喜歡的。你把它們融了,應當便能夠打一張一模一樣的紅寶石麵了。”
臨淵垂眼看向。
的掌心裏捧著許多首飾。
從耳璫到手串再到簪子不一而足。皆是黃金亦或是紅寶石製,在日下影流離,寶盈目。
這些首飾,足夠打一張紅寶石麵。
但,他仍不能答應。
明月夜中守備森嚴,暗線無數,一步行差踏錯,便是生死之遙。
而他本就是自明月夜中來。
早已經習慣了其中的殺戮,習慣了在刀鋒劍影下行走,習慣了每日裏生死一線地去與人搏命。
但李羨魚不同。
眼前的這樣的幹淨而好,像是養在玉瓶裏的一株芍藥,花瓣,花枝纖細,瓶是清澈的水,瓶外是澄明的,與明月夜中的腥殺戮像是隔著千山萬水般遠。
他本也無意讓李羨魚見到其中汙穢。
更無意,令以涉險。
於是,他將紅寶石麵收起,淡垂羽睫。
“唯有這件事不行。”
他拒絕得這般明確,像是沒有毫回寰的餘地。
李羨魚捧著首飾,偏首向他,卻仍舊是放不下心來。
可是,紅寶石麵在臨淵手裏。
去明月夜的路,也並不知曉。
若臨淵執意不帶去的話,便也拿不出什麽好的辦法。
除非臨淵自己願意改口。
於是李羨魚認真想了想,便先將首飾放下,重新往長案後坐落。
“臨淵,那我們現在能繼續玩藏貓嗎?”莞爾,像是已經將方才的事忘到腦後:“我還想學聽聲辨位。”
比起帶去明月夜,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要求。
於是臨淵頷首,毫不遲疑地站起來:“好。”
話音落,他已展開形,回到梁上。
Advertisement
他將紅寶石麵放下,拿了那枚藏貓用的金鈴回來,重新立在李羨魚前。
他問:“公主現在便玩麽?”
李羨魚起走近了些,低頭將金鈴幫他係在手腕上:“現在便玩,但是——這次藏貓也是要有些彩頭的。”
“若是你被我抓到了,便要答應我一件事。”
臨淵皺眉,察覺到的意圖,立時便要將手收回:“公主還是想去明月夜。”
李羨魚見自己被識破,耳緣略微一紅,輕輕手握住他的袖緣,小聲勸道:“隻是個彩頭,有什麽關係。”
羽睫輕眨,語聲裏有些心虛:“反正,反正,你的手那樣好,又不會讓我抓到。”
臨淵抿看向。
李羨魚說的並不錯。
隻要他不想,即便是不蒙上眼,李羨魚也絕不可能近他的。
但是由李羨魚主說出來,反倒令人覺得其中有異。
他垂眼,手去解係好的金鈴:“臣不與公主賭這件事。”
李羨魚一愣。
稍頃,低下頭,抿鬆開他的袖子。
背對著臨淵往長案後坐落,隻抬眼看著外頭茂的凰樹,怏怏不樂的模樣。
臨淵頓住作,看向。
“公主?”
李羨魚仍舊不回轉過來,隻是悶悶地道:“你不帶我去明月夜,不陪我一起過中秋,連藏貓都不陪我玩。”
抱怨得這樣有理有據,每一句話都似是無可辯駁。
臨淵默了默,終於還是走上前來。
他將解下的金鈴遞給:“公主若是真想玩藏貓,便玩吧。”
李羨魚半轉過臉來,惴惴試探:“真的嗎?你願意陪我玩了?”
臨淵低應了聲。
李羨魚略忖了忖,得寸進尺道:“可是,這樣不公平。你有武藝在,我原本便捉不住你,更勿論是蒙著眼睛。”
臨淵握著金鈴的長指一頓,垂眼看向:“公主想如何?”
李羨魚輕眨了眨眼,像是怕他反悔,便先將金鈴接過來,係回他的手腕上,這才將自己心裏的想法說出來:“應當是你蒙上眼睛,然後我來捉你,這樣才公平。”
臨淵眸淡淡。
這樣並不公平。
但即便是這樣,他也確信,李羨魚並捉不到他。
於是他頷首。
正當李羨魚杏眸微亮,心緒略微雀躍時,卻又聽臨淵淡聲:“既有彩頭,那輸家,自然也當有相應的賭注。”
他道:“若是公主輸了,往後便不能再提想去明月夜之事。”
李羨魚一時怔住。
原本想的是,先從藏貓玩起,然後再打雙陸,葉子牌,鬥百草。
這麽多遊戲,總能贏下一樣的。
但是臨淵這句話,卻像是將的退路都堵死。
李羨魚遲疑起來。
試著與他商量:“能不能換個賭注?”
臨淵垂眼:“不能。”
他道:“若是公主不敢對賭,這場藏貓,也可不設彩頭。”
李羨魚愈發遲疑。
能看出,臨淵並不想帶去明月夜。
能答應對賭,已十分不易,若是就此放棄,往後,恐怕便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心裏天人戰一陣。
最終,卻還是僥幸占了上風。
想,即便是臨淵會聽聲辨位,但是他畢竟是蒙著眼睛。
隻要自己不發出聲響,過去捉他,足足一刻鍾的時辰,應當不至於捉不住的。
於是輕眨了眨眼,答應下來:“那便這樣說好了,若是我贏了,你去明月夜的時候,一定要帶我同去。不能抵賴。”
臨淵應聲:“好。”
他隨意取過塊黑布蒙住自己的眼睛:“從現在起?”
李羨魚忙站起來:“你先等等。”
說著,便將自己上可能會發出聲響的環佩與步搖盡數取下,放到長案上,這才對臨淵道:“可以了,便從現在起,以一刻鍾的時辰為限。”
臨淵頷首,卻並不閃躲,隻立在原地。
李羨魚躡足過去,像是往日裏在花叢中撲蝶那般小心翼翼。
的作極輕,上的所有配飾皆已卸下,發上也隻戴著一支不會發出聲響的玉簪。
但不知道的是,年能聽見更為細微的聲音。
的底繡鞋輕盈落在宮磚上的聲音,行走間料攃的聲音,甚至是披帛被秋風拂的,極輕微的聲響。
一聲接著一聲,聽得極其清楚。
因而,在李羨魚即將到他的那一刻,臨淵閃避過。
李羨魚探出的指尖握了個空,甚至都沒到他的袖緣。
李羨魚輕愣了愣,又試著往他的方向接近。
可一連數次,皆是如此。
每次都是眼看著就要捉到了,便又被他閃避過,重新退到三步之外。
李羨魚鼓起腮來,忍不住問道:“臨淵,你是不是看了?”
臨淵道:“不曾。”
李羨魚仔細瞧了瞧他,也覺得他不像是看的模樣,便唯有重新開始努力。
可更聲一點一滴地過去,眼見便要到一刻鍾的時辰,卻仍舊是連臨淵的角都不到。
眼見著便要輸下這局。
李羨魚有些慌了神。
倉促間,倏然想起上回玩藏貓時,自己捉到臨淵的法子來。
可是,上回那件事分明便是意外。
若是故技重施,便是刻意去騙臨淵了。
想,騙人始終不對。
但是、但是,這似乎也比再讓臨淵孤赴險好些。
李羨魚遲疑了一陣,又抬眼去看立在不遠,卻始終捉不到的年。
他小臂上的刀傷還未愈合,仍舊纏著白布。
令想起,中秋夜,正與說著話的年,倏然聲息全無地倒在懷中的模樣。
心跳似也緩緩慢了一拍。
而在紊的心緒中,遠的更聲,也將將行至尾聲。
李羨魚終於橫下心來。
垂下眼,踩上了自己的裾。
子一傾,隨即摔倒在地上。
李羨魚手捂著自己的足踝,語聲因心虛而分外得輕:“臨淵,我,我的足踝扭到了。”
語聲未落,年已展開形,飛掠過來。
他在跟前半跪下`,單手扯下蒙眼的黑布,劍眉皺,低頭去看的足踝:“讓我看看。”
他的話音方落,李羨魚便鬆開了捂著自己足踝的素手。
輕輕抬起指尖,握住了他的手腕。
臨淵作略微一頓,立時抬眼看向。
李羨魚坐倒在地上,臉頰緋紅,似是也在為自己做的事而心虛。
低聲道:“臨淵,我捉到你了。”
臨淵抬起眉梢,薄抿:“公主騙臣。”
李羨魚雙頰更燙。
也覺得自己這樣不彩極了。
分明不是個喜歡耍賴的人,之前與小宮娥們玩藏貓,打葉子牌的時候,輸了便是輸了,彩
猜你喜歡
-
完結353 章

良陳美錦
未到四十她便百病纏身, 死的時候兒子正在娶親. 錦朝覺得這一生再無眷戀, 誰知醒來正當年少, 風華正茂. 當年我癡心不改; 如今我冷硬如刀.
95.5萬字8.31 171086 -
完結588 章

邪醫妖妃名動天下
二十二世紀的神棍女異師云嬋,一朝穿越,竟嫁了個權傾朝野的異姓王爺。可打遍天下無敵手,克天克地克空氣的她,一面對那位爺就立馬變弱雞,只能任其欺凌索取,各種耍流氓。某天,她好不容易找到機會逃出去,結果竟因為呼吸困難不得不回到他身邊。這不科學!某偏執王爺笑的一臉妖孽:“認命吧嬋兒,乖乖留在本王身邊不好嗎?”“……”云嬋想不明白,卻也毫無辦法。直到很久,塵封的記憶被解開,她才知道,原來他是她前世欠下的債。
121.3萬字8 56142 -
完結384 章

錦鯉農妻
陳卿是傅凜被逼無奈傾家蕩產買來的媳婦,對此他心里特別難受,連累倆只小包子一塊吃苦,但敢怒不好意思言;直到有一天陳卿惹毛了他,傅凜拉臉,用盡畢生所學冷冷道:“前不凸后不翹,干干癟癟四季豆,你未免也太自信,誰會喜歡你?”【叮!系統提示,恭喜您獲得來自傅凜50000點好感幣,等級提升。】陳卿:“……”懶癌少女×忠犬直男萌寶助攻,1V1,好軟好甜真香現場。
66.2萬字8 22638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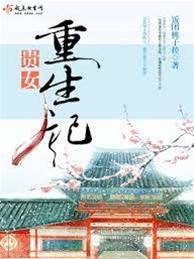
貴女重生記
大晉貴女剛重生就被人嫌棄,丟了親事,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將未婚夫賣了個好價錢!被穿越女害得活不過十八歲?你且看姐佛擋殺佛,鬼擋殺鬼,將這王朝翻個天!小王爺:小娘你適合我,我就喜歡你這種能殺敵,會早死的短命妻!
62.1萬字8 12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