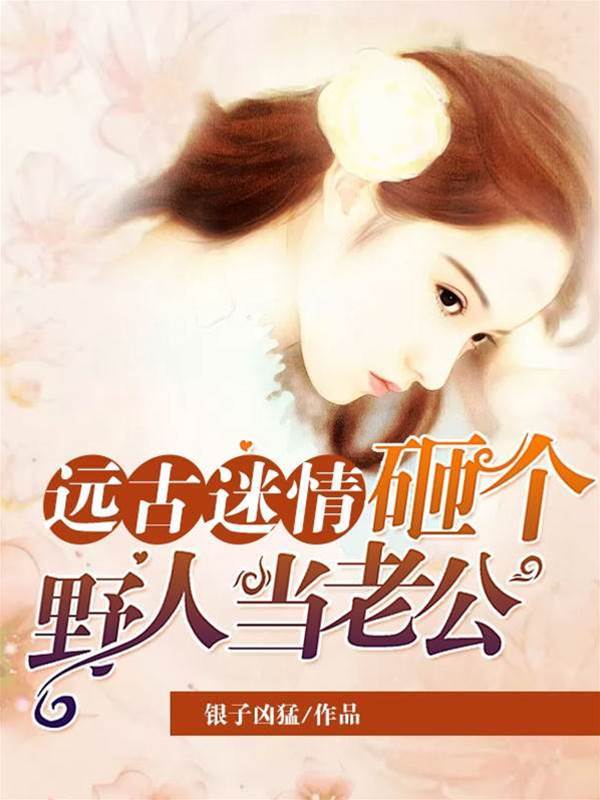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辭春闕》 第246章 不可一世的陸相曾跪過滿殿神佛
晏青扶與他稍稍頷首算作打了招呼。
陸行愣神過后,眼中閃過幾分驚喜。
“你……你怎麼過來了。”
“今日蘭姨遞了帖子,我便過來看看。”
依舊著陸夫人蘭姨,某一瞬間,總讓陸行以為這是還做青相的時候,用與當時如出一轍的模樣站在他面前,疏離冷淡地說話。
可如今又與當時不一樣。
陸行恍惚了片刻,目及頭上的珠翠,又回過神。
只神明顯看的要比剛府的時候要高興些。
陸夫人下去張羅著午膳,這偌大的前廳便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屋一時安靜,晏青扶是話的人,陸行倒也習慣,隨意找了個話與聊著。
“最近我在朝中也不曾見過沈世子,倒不知當時江岸城的事……理的如何?”
陸行自然仍不知道背后的人是皇帝,還以為他們如同當時一樣,要去江岸城查城主。
晏青扶目掃了一眼屋,也未瞞陸行。
“江岸城之事主使另有他人。”
“他人?你們這麼快就查清了嗎?”
陸行稍有驚訝,隨即問。
“嗯,當時……”
一句話匆匆未說完,門邊傳來一陣腳步聲,頓時晏青扶就止住了話。
陸行亦正了神回頭看去。
是陸府的丫鬟來著兩人去用午膳。
幾人便一同在涼亭里用過午膳,二人尋了個安靜的地方又說起此事。
“前些天皇宮有封折子,是要拿你衛軍統領一職,換去刑部理事,這你可知道?”
陸行眼中神凝了凝,點頭。
Advertisement
“知道。”
此事后來亦從八王府遞了信出來給他,何況陸府百年世家,對朝中風向最為敏,他當然知道,這位新帝,不甚喜歡陸家,甚至是討厭。
“或者說他討厭的不是你陸家的權,而是陸家的權不能為他所用。”
晏青扶看他心中所想,輕聲點明了扼要。
陸行稍稍沉默下來。
陸家祖祖輩輩都在大昭做,亦出過不丞相,雖然如他這般年輕的丞相有,可陸家手中權勢一向不。
雖為帝王忌諱是常有的事,可陸家本本分分,一心為著大昭,為大昭的帝王。
如今局勢明下,朝中大權與上京城真正的掌權者從不是龍椅上坐的那位帝王,帝王年輕難堪大任,若要真正掌權理事還需一段時日,陸家此時聽的就必不是容瑾的話。
哪知因此,會惹了帝王不喜。
陸行稍稍攏了袖,將心頭的想法下,又說。
“此事雖后來被容祁了下去,但你想說,皇上存了這個心思,日后也必然會對陸家下手。”
晏青扶與陸行說話向來不用廢話,能坐上丞相位置的人都不是簡單角,何況他自小生在陸家,對朝中政事耳濡目染,比旁人更通。
是以稍稍頷首,此話略一點出,算作給陸家的提醒。
“那你們……打算如何做?”
陸行若有所思地問。
他不傻,相反,他清楚晏青扶既然肯與他說這些,就證明如今皇帝已并非全然在王府掌控之中了。
換言之,年輕的帝王,已在背地里發展了自己的勢力,要和王府抗衡了。
Advertisement
不然這封折子,就不會遞到容祁桌案上。
晏青扶也不會今天和他晦地說起這些。
挲著手腕上的白玉鐲子,思忖著說。
“江岸城背后主使,是今上。”
短短一句話傳遞出的信息卻足夠讓人震驚,陸行幾乎是以為自己聽錯了話。
可偏頭看去,晏青扶靜靜地坐在那,神平靜。
新帝容許,甚至攛掇惠安公主奪位?
這是聽了就覺得荒謬的一件事。
陸行下意識地覺得此話有假,甚至難得出了驚訝的表。
“長孫府和江家,如今也聽命于皇帝。”
仿若不覺陸行訝然的表,繼續說道。
“他為何……”
陸行尤為疑容瑾背地里的這些作,可話說到一半,他又沉默下來。
能是為何,無非權之一字才能讓人鋌而走險。
他才幾日不曾關注這些,朝中竟然已經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平和的表面之下撕開是暗流涌,能平穩坐在一個位置上穩如泰山的人,又怎會全然依靠他人?
“如今西域虞為仍在大昭,遍尋找不到蹤跡,若說當時是皇上攛掇幫扶惠安公主,那與西域聯系的人……”
“也是他。”
晏青扶頷首承認他的猜測。
“簡直荒謬。”
陸行眉眼掠過幾分幾不可見的怒意。
大昭與西域勢如水火,可容瑾作為皇帝,為了一己之私,竟然和西域勾結。
如此之人怎堪大任。
“如今皇上已約有了作,我今日說這些,是想讓你多個準備。”
莫要輕易讓陸府挨了皇帝的算計。
陸行自然明白話中未盡之意,冷靜下來之后問。
“那你們呢,打算下一步如何?”
如此想著,陸行竟忍不住苦笑一聲。
曾幾何時,他提及晏青扶時已總下意識地帶了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陪在側,籌謀算計與行事都在一,但這個人卻不是他。
繞在袖的手稍稍晃了一下,他聽見晏青扶說。
“還未下決定。”
此時貿然行事必定是不妥的,他們還不清楚皇帝手中有沒有其他底牌,得試探清楚之后再有作。
陸行頷首,只說。
“若有什麼需要我的,只管傳信去相府。”
晏青扶自是點頭。
“不過在書房里,還放著之前皇上要我查過的一份名單,你不妨帶回去,興許有用。”
當時皇帝遞給他一份朝廷員的名單讓他一一查過,他依稀記得里面便有長孫家和江家。
既然晏青扶說這兩家如今都已經為皇帝所用,那麼陸行猜想剩下的人里,多半也有皇帝的人。
他三言兩語解釋罷,晏青扶點頭應聲。
“也好。”
“只是名單在相府的書房,是我改日著人送去,還是你今日跟我去一趟相府?”
既然來了,折騰一趟自然是好的,晏青扶沒多猶豫,便說。
“我去相府。”
晏青扶辭別了陸夫人,順著長街與陸行一路到了相府。
已有半
年多沒來過陸相府,此時一見竟覺得有些陌生,跟在陸行后慢慢走著。
越過廊前,目一掠,看見堂下種著的花草……
記得之前相府并未種過照水梅。
晏青扶以為自己記憶出了差錯,便開口問陸行。
“相府之前……也種過梅樹嗎?”
陸行步子頓住,順著的視線看到院中的照水梅。
繼而搖頭。
“沒有。”
他稍稍沉默片刻,說。
“是后來……覺得好看。”
也是后來青相府沒了人,他某次去那里,想起從前種在后院的那些梅樹。
盡然種的不多,但能種在后院里,想必也是極喜歡的。
他鬼使神差一般,從別也移了幾棵種過來。
生怕晏青扶再問下去他不知道如何回話,陸行別扭地轉移話題。
“書房到了。”
二人一同走進去,陸行順著桌案翻找著東西,可找了近半刻鐘的時候,也沒找到那份名單。
他蹙眉回想了片刻,朝晏青扶說。
“也許是在另一個書房里,你且在這等一等。”
晏青扶點頭,陸行大步走了出去。
桌案上被他翻找的凌,晏青扶無所事事地順著窗欞往外看,九月的風太大,順著吹進來將桌案上的紙張卷的飛起。
晏青扶走過去將窗子關上,回頭一看,桌案前被風卷起了一紙信封。
信封未放好,里面那封信約出來,沒有窺探旁人東西的喜好,折了信剛要放回去,目一掠,在信的背后看到了兩個字。
青扶。
?
晏青扶眉眼一怔,心中像是有什麼應一般,折開了手中的東西。
是一封信。
是陸行寫給,“去世”的的信。
“青扶,今日京城下了一場雪。
春三月的日子下雪,在上京一向罕見,可今日是你離開的第三個月。
我看著這場雪,想起你當時被先太子算計,一個人留在京城去世的那一日,是不是也這樣大的一場雪。
真是對不住,在你曾最無助,可能唯一也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我卻沒在上京。
細想想,從你初登相位,到如今兩年,我們同臺共事,相卻寥寥無幾。
于你看來,興許我只是和旁人都沒什麼差別的同僚,可對我來說,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樣。
每次在相府論及的公事,其實都是我百般心思想與你多呆些時候。
還有阿娘,亦很喜歡你,總熱地扯著你去陸府,每每我回去,也總向我過問你。
我對說,我喜歡上了一個人。
這喜歡不能輕易說出口,但若是可能,興許過了兩年,會有個和兒子一樣在朝中理事,聰明厲害的兒媳。
只是兒子比不得厲害,還盼著以后別為了這個人嫌棄兒子。
但太憾了,這些話告知還不過兩個月,便再沒有了實現的可能。
回來之后,我總想著你那時疼不疼,沒有人陪在邊會不會也很孤寂,我想若是可能,也許當時,我寧愿替你飲下那杯毒酒的人是我,或者百里揚鞭回了京城,替你先將太子殺了。
今日京城的雪很大,我又去了郊外看你。
春三月的雪還涼,墓碑前我替你掃過,也開始想你在那邊,會不會也很冷。
或者已經投胎轉世,換了新的人生吧。
做丞相太苦太累,雖你做的很好,但我仍在佛前求過,盼你來世投個尋常人家,得庇佑安安穩穩。”
云臺寺高,石階冷,但向來不信神佛不可一世的陸丞相,曾在寒雪覆滿白的春三月,悄無聲息地跪過滿殿神佛。
此一世未免太苦,愿來世許富貴尋常人家,折我半世命數,庇安穩。
信在此時戛然而止,怔怔地看過,著沉穩有力的字跡,仿佛窺見當時寫信之人的認真。
落款的最后一句,是被寫過又劃掉六個字,濃重的黑墨沾染了最后那點地方,便窺不見是什麼話。
時間落在今年春三月,轉世回來的那一日,他曾在陸府的屋,著墨一點點寫過這封,原本再不會被人看到的信。
后極輕的腳步聲臨近,沒顧心頭的復雜,下意識將信復了原位放回去。
陸行轉角踏進屋的剎那,見神如常地站在桌案邊,用和以往一模一樣的語氣出聲。
“找到了嗎?”
陸行目掠過桌案,似乎覺得有哪不對勁。
可桌案走前就被他翻的凌,此時也看不出什麼。
他揮掉心頭的想法,將手中的東西遞過去。
當時應當是他查過,順手放在了另一個書房。
晏青扶接了過去,聽見他說。
“信上的人都是皇上讓我查過的,你回去可仔細看看,再讓容祁想一想,這其中可有人有什麼怪異之。”
晏青扶點頭,又道。
“有勞。”
陸行啞然失笑。
“何須客氣,好歹你我也算同朝共事,就算只為大昭,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帝王心思太狠,剛愎自用又與外敵勾結,不管如何聰明,都不適合做皇帝了。
陸府就算只為大昭,也該尋個更好的人做皇帝。
這句話說完,屋一時又安靜下來。
晏青扶了手中的書信,斂下眼說。
“時候不早,我先回去了。”
陸行眼神一黯,但很快也點頭說。
“好。”
他目及凌桌案上,支在桌沿出的一點信角,眼神一頓,稍稍往前走了兩步將信封推進去。
晏青扶只恍若不覺他的作,抬步走出書房。
陸行跟在后很快出來。
“我送送你。”
說是送,其實也就是跟著到了大門外,早有馬車侯著,陸行看著坐上去,馬車從門口離開,往長街另一邊去。
他站在門邊看了許久,直到那點黑影漸漸消失不見,才轉頭回了書房。
書房里從來沒有下人收拾,一向是他親力親為。
陸行將凌的桌面收拾罷,看向被他放在桌邊的那封信。
原本是在硯臺下的,他翻找東西時竟順手拿了出來。
鬼使神差般,他將信封拆開,又將那張薄薄的紙拿出來。
上面的字已是午夜夢回他反復看過無數遍的,如今眉眼認真地又看過,他忽然合了信,引過一旁的燭臺,明黃的火跳躍,靜靜地將東西燃盡。
如今這東西于他,已是再無無用。
猜你喜歡
-
完結158 章
歡天喜帝
泱泱亂世下,一場王與王之間的征戰與愛。他是東喜帝,她是西歡王。他叫她妖精,她稱他妖孽。他是她的眼中釘,她是他的肉中刺。他心狠手辣霸氣橫溢,她算無遺策豔光四射。相鬥十年,相見一面,相知一場,相愛一瞬。是他拱手山河博卿歡,還是她棄國舍地討君喜?世間本有情,但求歡來但尋喜。
43.2萬字8 8887 -
完結407 章

重生后成了皇帝的嬌軟白月光
(重生1V1)論如何從身份低微的丫鬟,獨得帝王寵愛,甚至於讓其解散後宮,成為東宮皇后,自此獨佔帝王幾十年,盛寵不衰。於瀾:“給陛下生個孩子就成,若是不行,那就在生一個。”反正她是已經躺贏了,長公主是她生的,太子是她生的,二皇子也是她生的,等以後兒子繼位她就是太后了。至於孩子爹。“對了,孩子爹呢?”慶淵帝:“……”這是才想起他。朕不要面子的嗎? ————於瀾身份低微,從沒有過攀龍附鳳的心,她的想法就是能吃飽穿暖,然後攢夠銀子贖身回家。可,她被人打死了,一屍兩命那種,雖然那個孩子父親是誰她也不知道。好在上天又給了她一次重來的機會。既然身份低微,就只能落得上輩子的下場,那她是否能換個活法。於瀾瞄上了帝都來的那位大人,矜貴俊美,就是冷冰冰的不愛說話。聽說他權利很大,於瀾想著跟了他也算是有了靠山。直到她終於坐在了那位大人腿上,被他圈在懷裡時。看著那跪了一地高呼萬歲的人,眼前一黑暈了。她只是想找個靠山而已,可也沒想著要去靠這天底下最硬的那座山……完結文《權臣大佬和我領了個證》《向隔壁許先生撒個嬌》
59.5萬字8 278080 -
完結1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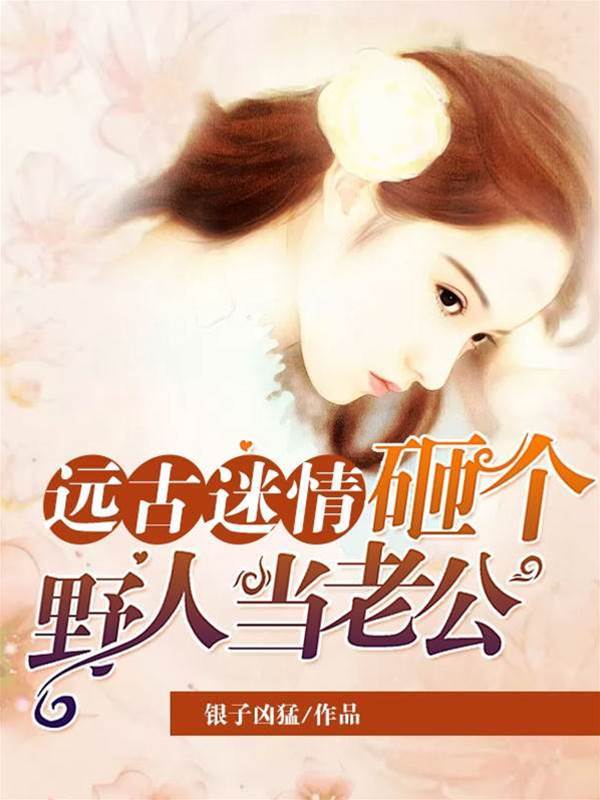
遠古迷情:砸個野人當老公
穿越到原始深林,被野人撿了 野人很好,包吃包喝包住,然而作為代價,她要陪吃陪喝陪睡! 于是見面的第一天,野人就毫不客氣的撕了她的衣服,分開她的雙腿 作為報復,她將野人收集的皮毛割成一塊塊,將他抓來的兔子地鼠放生,生火差點燒了整個山洞 然而野人只是摸摸她的小腦袋,眼神溫柔,似乎在說,寶貝,別鬧了!
41.9萬字8 13079 -
完結889 章
嫁給渣男死對頭
前世,沈鸞那寒門出身的渣男夫君給她喂過兩碗藥,一碗將她送上了權傾天下的當朝大都督秦戈的床,一碗在她有孕時親手灌下,將她送上了西天,一尸兩命。兩眼一睜,她竟回到了待字閨中的十五歲,祖母疼,兄長愛,還有個有錢任性的豪橫繼母拼命往她身上堆銀子。沈鸞表示歲月雖靜好,但前世仇怨她也是不敢忘的!她要折辱過她的那些人,血債血償!
167.1萬字8.18 77599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8 90347 -
連載573 章
侯府雙嫁
葉家心狠,為了朝政權謀,將家中兩位庶女,嫁與衰敗侯府劣跡斑斑的兩個兒子。葉秋漓與妹妹同日嫁入侯府。沉穩溫柔的她,被許給狠戾陰鷙高冷漠然的庶長子;嫵媚冷艷的妹妹,被許給體弱多病心思詭譎的嫡次子;肅昌侯府深宅大院,盤根錯節,利益糾葛,人心叵測,好在妹妹與她同心同德,比誰都明白身為庶女的不易,她們連枝同氣,花開并蒂,在舉步維艱勾心斗角的侯府,殺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最后,連帶著不待見她們二人的夫君,目光也變得黏膩炙熱。陸清旭“漓兒,今夜,我們努努力,再要個囡囡吧。”陸清衍“寒霜,晚上稍稍輕些,你夫君我總歸是羸弱之身。”
100萬字8 30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